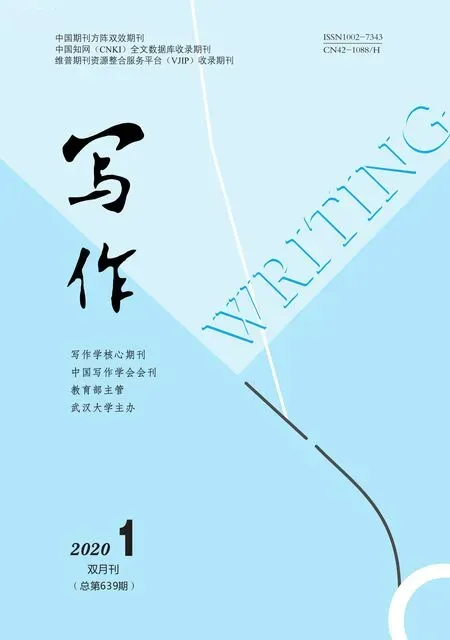科幻創作題材創新的五條路徑
劉 洋
2012年,英國評論家保羅·金凱德在《洛杉磯時報》上發表一篇書評,對2011年的幾本科幻年選中的作品發表了略顯刺耳的批評,他認為當前“科幻作為一種文體已經到了近乎枯竭的狀態”。隨后,“枯竭說”引發了美國科幻評論界的一場大討論。喬納森·麥卡蒙特發表了一篇長評,其中說道:“我認為科幻小說已經失去了對世界的興趣,與時代脫節,導致了一種既缺乏相關性又缺乏生命力的自戀又內向的文學的出現。”事實上,類似的批評在很早就出現了。在1954年出版的一本美國科幻選集的前言里,編者就發出了這樣的感慨:“今天的許多雜志都離讀者太遠了。它們已經失去了驚奇感和熱情,這正是很多以前的作品吸引讀者的原因。它們并沒有像真正的科幻小說那樣,在作品里把現實的科學理論和那些激動人心的科技進展結合起來。”①Lester del Rey,Cecile Matschat and Carl Carmer Philadelphia.The Year After Tomorrow-An Anthology of Science Fiction Stories.Winston,1954,pp.6-7.在中國,近來也有越來越多的關于科幻小說“內卷化”的批評,認為現在的作者大多只是在前人開辟的疆域中修修補補,失去了創新的勇氣和能力。這些批評或許過激,但的確反映了當前科幻創作中的一種趨勢,作為創作者來說,應該要有所警醒。今天的科幻小說早已突破了黃金時代那種單一的風格,在新浪潮運動之后,很多作品在文學性上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追根究底,科幻小說這一文類,其最核心和最根本的吸引力,還是來自于題材和設定所帶來的驚奇感。所以,如何在題材上有所突破,做出一個具有創新性的設定,對于今天的科幻創作者來說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在當今創意寫作課程逐漸興起與科幻文學、科幻影視趨熱的時代背景下,科幻創作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創意寫作方向,也越來越多地引起了人們的重視。早在1991年,吳巖就在北京師范大學開設科幻文學類課程,后來逐漸分化出科幻創作的方向,這是我國最早在高校開設的科幻創作課程。發展至今,已經有多所高校開設了科幻創作課程,例如賈立元在清華大學開設的“科幻文學創作”、蘇湛在中國科學院大學開設的“科幻文學與影視創作”等。筆者在南方科技大學也開設有“科幻創作”課程。在科幻創作的教學過程中,如何引導初學者跳脫出一般科幻創作的俗套,啟發他們的創意和想象力,同樣是一個值得我們認真探討的問題。
對于初涉科幻的作者來說,第一步當然還是要大量的閱讀,從各種經典的文本中汲取營養,同時也讓自己對前人開拓的領域有個大致的了解。這樣,在自己寫作的時候,才能對題材的新穎性有一個合理的評估。其次,他們還應該對當今科學的前沿領域有所了解。當然不必像科學家那樣深入,但至少應該大致掌握其研究脈絡和相關機理。當你對某個領域產生特別的興趣,決定以此切入,創作一篇科幻作品時,你就應該對它進行更深入地了解。其實,以當今科學如此迅猛的發展速度而言,想要尋找新的創意點并不困難,很多時候科學家已經進行的課題甚至已經超越了科幻作家的想象。作為范例,也為了幫助初學者找到突破的方向,下面我將在五個具體的方向介紹題材創新的開拓方式,并提出一些創作時需要注意的問題。
一、假想科學
一種常見的誤解認為科幻小說一定要基于現有的科學理論來做設定,其實不然。科幻小說的“科學性”不同于學術論文的“科學性”,它更強調的是推想過程的邏輯自洽,而不強求其理論基礎嚴格符合當今科學的認知。其原因有兩個,其一是為了故事構建的需要。我們必須強調,科幻小說的首要目標是構建一個具有驚奇感的故事,為了這一需要,當作者不得不引入一些超越科學認知、有時候甚至略微違反科學認知的設定時,他們是應當得到允許的。劉慈欣的《球狀閃電》基于“宏電子”這一完全沒有科學依據的設定,并不影響它成為一部偉大的科幻小說,因為在這一設定的基礎上進行的一系列推演,包括電子的量子特性在宏觀下的展現等,都完全符合現代科學的邏輯。正是在這一系列設定的基礎上,作品才成功地為讀者呈現了一個詭異怪誕、極富驚奇感和吸引力的世界。
另一個引入假想科學的理由是:科學理論本身是在不斷變化的,一些目前還不成立的虛構的理論,并不意味著今后不會發展成真正的科學。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阿西莫夫在基地系列里虛構的一個科學理論“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該理論認為,雖然人類個體的所作所為很難預估,但作為一個整體,人類大眾的種種行為——包括人類未來的歷史——則可以通過純粹的統計手段來預測,惟一的前提條件是“人類集團本身不了解心理史學,以便其反應是真正隨機的”①原文為“the human conglomerate be itself unaware of psychohistoric analysis in order that its reactions be truly random”。。基地系列的主線情節就是基于這個科學理論而衍生出來的。顯然其靈感來源是熱力學與統計物理,在那里,盡管每一個微觀粒子的速度和軌跡都無法預測,但表征其整體的物理參量如溫度、壓強、體積等,卻是可以預測與計算的。在阿西莫夫寫出該作的20世紀中葉,心理史學當然只是他的設想,但隨著近年來一門稱為“社會物理學”的學科的迅速發展,它已經越來越接近阿西莫夫所設想的那個虛構的學科了。雖然現在的社會物理學還沒有發展到小說里心理史學的程度,但我們完全可以期待其未來成為一個真正完備和成熟的理論體系。
引入假想科學作為設定基礎的時候要注意避免與當今的科學結論直接沖突,那樣容易使作品陷入“偽科學”的漩渦之中。當然,我們必須要明確,科幻小說中的假想科學與一般認為的偽科學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為了故事構建的需要而引入,作者和讀者都明確地知道這一點,并不會認為它是真實的科學理論,而后者通常會竭力模糊其與真實科學的界限,其宣傳者本身往往聲稱它們就是真正的科學理論。“宏電子”產生的背景是人們目前對球狀閃電的起源并沒有一個確切的理論解釋,而且對電子、夸克這類基本粒子,人們對它們的了解同樣極度缺乏。“心理史學”同樣如此,它并不違反任何已知的科學定律,相反是超前于現有的科學理論。其他常見的科幻設定,如時間旅行、曲率驅動、瞬間傳輸等,雖然并沒有現有科學支撐,但至少并不被科學定律所禁止,從而為假想科學留下了理論上的空間。
通過引入一個假想的科學理論來建構一個虛擬世界,是極具原創性的設定方法,可以開發出極有新意的題材。具體設定的時候一定要注意豐富假想理論的細節,將其與現有的科學規律融合在一起,盡量減少其假想的色彩,避免其成為一座沒有支撐的空中樓閣。
二、異構世界
想要從一個虛構的科學理論出發推導一切的想法往往是極為困難的,大部分時候我們并不這么做。想要達到與其類似的顛覆性的奇觀效果,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途徑,比如設想一個處于某種極端環境下的異世界,或者其他與現實截然不同的世界。這些世界的物理法則和我們并沒有區別,但故事通常并不發生在我們熟悉的地球或類地球環境里,那里的眾多事物和智慧生物的日常行為也往往與人類截然不同。
一種常見的異世界設定是讓故事發生在地球之外的其他星球。有時候我們會借助那些確實存在的星球,比如火星、金星、月球、冥王星等來構建自己的故事,這時作者應該做好充分的準備,讓自己對這些星球各方面的狀況了如指掌,特別是它們與地球相比有哪些異樣之處,因為這些異常點往往才是讀者更感興趣的地方,作者應該圍繞這些異常之處來展開故事。在克拉克的《月海沉船》里,故事始終圍繞著月塵的特殊物理性質來展開,比如它們的流動性、導熱性、電磁屏蔽等,讓整個故事顯得真實可信的同時又不斷產生新的驚奇點。金·斯坦利·羅賓遜的火星三部曲則圍繞火星的實際狀況設想了眾多對其進行環境改造的方案,以這種巨大的變革為背景引發了激烈的沖突。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肯·沃特的《地下之上》,該小說發生在木衛二那被冰殼覆蓋的液態海洋中,那里產生的智慧生命具有與正常視角相反的上下方向認知:因為生存在海洋里,身上長有氣囊的他們同時受到指向星球外部的浮力與指向內部的重力,由于前者大于后者,綜合起來的等效重力便成了指向外部的方向,于是它們把這個方向認定為“下”,而把指向星球內部的方向認定為“上”。這種誤解帶來一系列有趣的故事,比如他們想要突破星球的束縛,向外進發,卻搞錯了方向,一直向著星球內部挖掘,發現一直無法突破到海洋外部。他們還總結出了一些錯誤的引力定律,比如高度越“低”引力越大——擬合的數據甚至顯示到某個高度重力會無窮大——事實上只是因為越靠近冰層,液體的壓力越小,其身上的氣囊就越大,從而使其所受的浮力增大了而已。
另一些作品則完全發生在一些虛構的星球之上,或者目前人類尚不明了的遙遠星球上。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不受已知星球的各種特征的約束,在一個更為自由的維度下,根據故事的需要來建構所需的環境,它們往往比既有的、人類較為熟悉的太陽系內的星球環境更加怪異,從而讓作品具有更強烈的沖擊性。弗蘭克·赫伯特的《沙丘》虛構了一個被沙漠覆蓋的干旱星球,卻出產能使人產生超感能力的香料;與之類似的是電影《阿凡達》中的星球,它富含奇妙的常溫超導物質,因此引來了人類的大舉入侵;羅伯特·福沃德的《龍蛋》描寫了一個生活在中子星上的種族——奇拉族(Cheela),他們的新陳代謝是基于核反應而不是化學反應,同時因為其星球表面的重力遠超地球,他們和人類的時間流速也相差甚遠。寫作這類發生在虛構星球上的小說時,我們可以先從一系列基本要素開始進行設定,比如這顆星球的半徑是多少(涉及到重力的大小),主要組成元素是什么(磚石星球?),星球表面的環境怎么樣(是否有固體表面、土壤、大氣、液態水),它的自轉和公轉情況如何(涉及到不同緯度的重力差異、是否有四季及磁場等),它所圍繞的恒星是什么狀態(是否已經變為紅巨星,或者有三顆恒星?),距離恒星的距離是多少(涉及星球表面的溫度),等等。切記設定一定要服務于故事的需要,在一開始就要明確自己想寫一個什么樣的種族或什么樣的奇觀,以此來指導自己對星球的設計。斯蒂芬·吉列特在《世界建構》(World Building)一書中提出了很多操作性的建議,大家有興趣可以參考。
除了外星球,故事還可以發生在其他的奇異世界,例如賽博朋克作品常發生在意識電子化之后的虛擬空間中,另一些作品把場景設置于人或其他生物的體內、二維的平面宇宙、中空的地球內、環繞恒星的戴森環上、原子等微觀粒子內部,乃至整個宇宙之外的超空間中。可以說,科幻小說的故事可以發生在任何世界里,不管它們有多么詭異或不合常理。特德·姜的《巴比倫塔》設定了一個在空間上具有周期性邊界的世界,人們造了一座極高無比的塔,穿過了天頂,最后發現又回到了地面。格雷格·伊根的《邊境守衛》(Border Guards)構想了一個具有三維環面拓撲結構的虛擬世界。瑪麗亞·斯奈德(Maria V.Snyder)的立方體之戰系列則發生在一個被稱為“里面”(inside)的世界,那是一個全封閉的立方體,按照階層分割為不同的生活區域。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雖然上文我們看到了很多五花八門的異構世界,但這些精巧的設定本身并不直接決定其好壞。評價一個世界的結構設計是否優秀,除了看其創新性、自洽性和驚奇感之外,還應該觀察其是否容易衍生出各種戲劇沖突。設計一個完美、和諧、人人幸福的烏托邦世界,在大部分的時候是沒有意義的。
三、技術奇觀
科幻小說中總是充斥著各種虛構的科技發明,很多科幻小說中常常會出現一個發明家或科學家的形象,通過其口向讀者闡釋某種新奇技術,并由此帶動故事的發展。有的時候,這些發明會帶來好的結果,科幻作家對科技的進步持積極肯定的態度,例如在劉慈欣《圓圓的肥皂泡》《帶上她的眼睛》《地火》《地球大炮》等小說里,超級表面活性劑等作者設想的技術都帶有很明顯的技術樂觀主義的傾向,故事的主要矛盾在革命性的技術創造中得以解決,是這類作品的典型特征。但大部分時候,科幻小說中的技術創新帶來的更多是不好的結果,或者雖然它給人類帶來很多好處,但作品重點關注的卻是它的負面效應,例如其導致的操縱失控、倫理失序、人類異化、審美缺失等。對技術的警惕和反思日益成為現代科幻作品的主流,這固然和當今世界科技發展的狀態與科技倫理思潮的興起有關,但一個更根本性的原因不容忽視,那就是一個關注科技陰暗面的作品,比起那些科技樂觀主義的作品,往往更容易構造一個復雜曲折又有深度的精彩故事。
在科幻作品里,構造一個新奇的、震撼人心的技術奇觀,是一種常見的題材創新方式。但那些新奇技術其實也并非是作家憑空想象出來的,它們通常也帶有現實科技的影子。一般而言,科幻作品中的技術奇觀,從其創生途徑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宏大化。其基本思路就是通過放大現有的工程尺度,來塑造那些宏偉壯麗的奇觀。凡爾納的《從地球到月球》描寫了一個900英尺長的巨型大炮,這是對大炮這一現有技術的夸張放大。大炮這種技術本身并不新奇,但尺寸上的放大卻帶來了視野上的另類驚奇感,后來在劉慈欣的《地球大炮》里更是將炮筒貫穿了整個地球,可謂將這一思路用到了極致。這種對宏大奇觀的描寫在硬科幻小說中常常出現,隨口就可以說出無數這樣的例子:《天堂的噴泉》里出現的太空電梯、《與拉瑪相會》中的巨型太空站、《星球大戰》里的死星堡壘、《環形世界》里的戴森環、《流浪地球》里的行星發動機……宏大不僅是技術極端發達的表現,而且也給讀者帶來了新的審美體驗。但要注意的是,不要為了宏大而宏大,或者一味地進行大尺寸空間下的描寫,任何宏大之物都需要從細節上進行呈現。
第二類是重構。在一個新的環境中,重新構建那些我們熟悉的技術,也是一類常見的技術奇觀的創建方式。在這類小說里,我們會看到很多略顯奇怪的機械或技術,它們源于現實,但又在某些地方偏離了現實。蒸汽朋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那里,一切機械的動力來源都是蒸汽機,包括大型飛艇、機器人及計算機。那些龐大、笨重而又結構繁復的機械噴吐著灼熱的蒸汽,在冷硬中卻又呈現出另類的美感。另一種常見的重構方式是將機械生物化,例如《無賴殖場》里的生物火箭、《海伯利安》里的樹艦、《三體》里的人列計算機等。這也是我比較喜歡的一種重構方式,我在《說書人》里寫過用細菌發電的直流發電機,在《流光之翼》里設想了一種利用蝴蝶構建的量子計算機。這類設定將鮮活的生物和冰冷的機械結合在一起,常常能產生令人意想不到的驚奇效果。
第三類是異化。具體來說,科幻小說中的異化通常又分為人的異化和技術的異化兩種,兩者都是某種特定的技術發展到極限或失控之后,所涌現的脫離原來預期的產物。很多情況下故事中都會出現某種形式的災難,其技術設定的奇觀場景在這些悲劇性的災難爆發過程中得到集中地展現。
人的異化通常與那些應用于人體的生物、醫學等方面的技術有關,《弗蘭肯斯坦》里面目猙獰的人造人、《羚羊與秧雞》里基因編輯培育出的“秧雞人”、《寄生前夜》里由線粒體幻化出的異形人,都是其典型的例子。國內作家也創作過大量這類題材的作品,最典型的就是王晉康的“新人類四部曲”《類人》《豹人》《癌人》《海豚人》,每一部都描寫了通過某種基因技術制造出的新人類,以及技術失控下產生的悲劇。另外,劉慈欣《微紀元》里的微型小人、何夕《盤古》里的巨嬰、劉宇昆“未來三部曲”里意識上傳后的數字人,也都是讓人印象深刻的異化設定。
與技術帶來的人的異化不同,一些作品重點關注的是技術本身的異化,其通常涉及的是這樣幾個方面的技術:1.人工智能,如杰克·威廉森的《束手》,描寫了一個智能機器人接管一切,人類受到機器無微不至地照料,什么都不用做,卻也什么都不能做的可怕場景;2.互聯網/物聯網,如尼爾·斯蒂芬森的《雪崩》,虛構了一種可以同時在網絡和現實生活中傳播的電腦病毒;3.高能物理,如劉慈欣的《朝聞道》,設想高能加速器的實驗會導致真空衰敗,甚至毀滅宇宙;4.納米技術,如麥克·克萊頓在《納米獵殺》呈現的場景:一個納米集群失控后逃出實驗室,不斷進化、復制,并開始獵殺沙漠中的動物乃至人類。還有一類小說并不關注某種單一技術對世界造成的影響,而是著眼于科技與工業發展對全球生態的影響,這就是目前在西方興起的所謂“氣候小說”(Cli-Fi),其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對技術異化下的一種奇觀展示。
我們可以看到,在科幻小說里設想一種技術奇觀作為核心設定,具有眾多的途徑和選擇對象。建議初學者從自己熟悉的領域入手,盡量大膽地進行推想,然后再用文字細致地勾勒出腦海中那些宏偉而奇絕的圖景。
四、奇異生物
在作品里引入現實中不存在的生物并非奇幻小說的專利,在科幻小說里我們也常常這樣做。這些奇異生物要么沒有智慧,僅憑生物本能做出反應,在小說里通常作為人類探索、研究、斗爭的目標;要么具有智慧,甚至處于人類遙不可及的文明等級——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外星人,小說主要通過人類與其交流交往的過程建構故事和沖突。后一類題材在各種科幻小說中較為常見,這里不再過多闡述。我們重點討論前一類奇異生物的設定和呈現技巧。
我們一開始就要明確自己設定這些生物的目的以及小說的寫作方向。如果你要創造的是一個或眾多“怪獸”,那么其故事可以非常好萊塢化,展示其侵入人類生活空間、與人類斗爭的過程,類似電影《哥斯拉》《迷霧》《漢江怪物》《長城》等;也可以反之,描寫人類無意中進入怪物的領地,突出探索和冒險的元素,如電影《黑暗侵襲》《被時間遺忘的土地》《九層妖塔》等。這種題材的生物設定簡單粗暴,通常是通過模仿、放大或拼接現實中的生物來塑造怪物的形象,并且讓它們具有某種超出普通生物的能力或特征,使其能夠對人類造成威脅。設定的時候,除了強調其非凡的攻擊能力之外,還要注意為其留下一個致命的弱點,以便故事的主人公能夠消滅它們或者從危險之地脫身。
另一些科幻作品中的奇異生物則顯得更為神秘,與人類的互動關系也不是簡單的獵殺和被獵殺。在故事中,常常通過探索或研究的行為來呈現其異常特征。寫作這類題材,我們在設定時需要更加大膽、細致,既要突破一般的思維局限,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新鮮物種,給讀者帶來驚奇的閱讀體驗,同時也要注重其邏輯的合理性,對其奇異特性的由來、所處的環境、生存所需的物質條件、基本的結構特征、生殖發育的過程等方面統合起來考慮,讓其奇異之處得到更多基礎設定的支撐,以增強其合理性和真實性。以石黑達昌的《冬至草》為例,其中描寫了一種奇異的植物,它具有近乎透明的葉片,生長在含鈾的土壤中,帶有放射性。故事以一位研究員對冬至草的追蹤和探究為主線,借助前人的研究筆記為線索,逐漸描摹出這種植物的各方面特性,并最終揭示出背后隱藏的真相。文中對冬至草的很多細節描寫值得我們注意:“從莖生出的羽毛一樣的葉片嬌嫩欲滴……給人一種強烈的透明感”,“根系竟然十分發達,相互纏繞、延綿不斷”,“距離墓地越近,冬至草的生長就越密集,而且白色的純度也更高”,“給它加熱,想讓它早點干燥,可是它突然間就會燒起來”,“該植物有夜間發光的記錄”。這些細節描寫都不是孤立的,它們相互支撐印證,構成了一個嚴密的邏輯鏈條,為我們建構了一個真實可信的生物體系。
需要指出的一點是,以奇異生物為核心設定的小說,尤其需要以寫實的手法來創作。只有在這樣的虛實交織之下,設定和現實的界限才會盡可能地模糊,從而給讀者更強烈的震撼感。
五、社會結構
科幻小說常被人寄望于可以對科技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予以預測,甚至給出一些可能的解決方案,因此科幻作品通常會涉及到社會的整體結構在某種科技或極端事件下的調整、震蕩與劇變。一部分作品更關注科技本身帶來的驚奇感,對其在社會結構上帶來的影響常常輕描淡寫地帶過,或者采用其他的寫作技巧以避免讓作品在這方面復雜化。而另一部分作品則截然不同,它們的重心恰恰就是對社會結構的設定與描摹。在這些作品里,社會的運行規則常常與我們現實生活迥然不同,從而形成了種種奇特的社會結構。正是這些奇特的社會規則和社會結構,給這類作品帶來了獨特的閱讀趣味,它們才是作品的核心設定。而與之相匹配的技術手段,不管它們看上去多么精巧或酷炫,本質上其實并不重要,因為它們往往是為了迎合與匹配那些社會結構而刻意地設計出來的。
這種題材的科幻小說常被歸類為“烏托邦”或“反烏托邦”,在歐美的科幻小說里有許多這樣的經典作品,如《1984》《美麗新世界》等。近年來性別、種族等題材在歐美科幻小說中逐漸流行,也隨之涌現出了一批聚焦女權主義的烏托邦和反烏托邦作品,如厄休拉·勒奎恩的《黑暗的左手》,內奧米·奧爾德曼的《權力》等。在這些作品里,男女的性別及其社會地位之間的關聯被消除或者顛倒了,從而帶來了新的社會結構。在中國,致力于建構新奇社會結構的科幻作品相對較少,但也絕非空白。劉維佳的《高塔下的小鎮》描寫了一個在激光大炮保護下的田園牧歌式的小鎮。大炮可以阻擋所有外來者進入,讓小鎮居民生活在零壓力的安逸狀態之下,然而這其中也隱藏著進化的危機。王晉康的《蟻生》借助一種從螞蟻中提取到的激素,建立了一個人人利他的烏托邦農場,最終卻因與外部社會的格格不入而走向幻滅。劉慈欣在《超新星紀元》里創造了一個由孩子統治的世界——因為一場超新星爆發,所有13歲以上的人類都相繼死去。在之后的新世界里,所有大人們留下的法則和規律都被推翻,甚至連戰爭都淪為了一場游戲。我們注意到,在這些作品中,促成社會結構改變的因素,往往只是輕描淡寫地幾筆帶過,因為它們并非作品的重心所在。《高塔下的小鎮》并沒有詳細說明激光大炮的建造和工作原理,《蟻生》里也對所謂的“蟻素”語焉不詳,至于《超新星紀元》里讓所有大人死去的宇宙輻射,其實也完全可以改為其他的致命因素——比如一種只對大人們有效的流行病毒——而對故事的核心毫無影響。
如果說大部分科幻小說的設定是對某種科學技術的思想實驗,那么以社會結構為核心設定的科幻小說就是一場社會實驗。只要構思精巧,它們往往可以呈現出比普通科幻小說更有吸引力的一面,同時在思想性和文學性上也容易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因此,在社會結構的設定上發揮自己的創意,也是一種極有意義的題材創新方向。
綜上所述,本文從“假想科學”“異構世界”“技術奇觀”“奇異生物”和“社會結構”五個方向介紹了科幻創作的創新路徑,并提出了寫作時需要注意的一些問題。在科幻產業正逐漸興起和完善的中國,我們的科幻創作者們應該更加積極地開拓這一文類的題材,以更加富有驚奇感的場景、設定和故事吸引讀者,讓科幻走出小圈子的自娛自樂,被更多的讀者接受和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