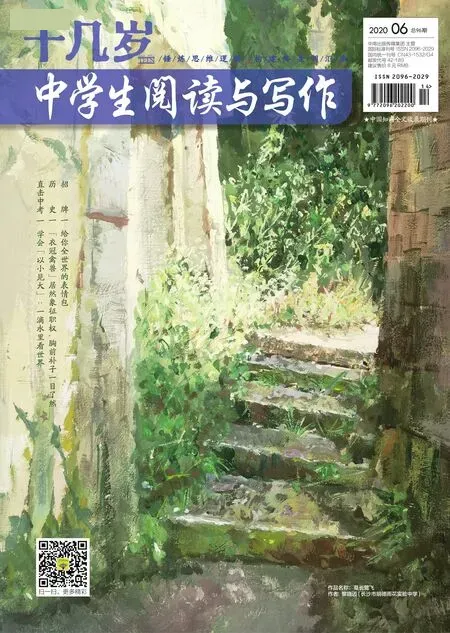“貼”著人物:不是靠近,而是走進
文/沈念(湖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手機微信里下載了表情包后,與朋友聊天時為了快捷回復,常常發去不同的表情,一下就表達了當時的情緒。
談論某部經典文學作品,我們會迅速聯想起其中某個活靈活現的人物,刻骨銘心的是人物的命運,說過的一句話一個動作,也可能是在某情境下的一個表情。如魯迅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瑪絲洛娃,布爾加科夫的沃蘭德、瑪格麗特等。因為他們,我們體悟著廣袤世界里的形色人生,為之欣喜、哭泣、歡慶或悲傷。我們閱讀中的情緒往往就與人物的表情緊密地關聯在一起。
人物描寫是一個綜合性的話題,語言、動作、神態表情、心理活動、外貌等等,各有千秋。人的表情可以理解為面部、語言聲調或身體姿態上的思想感情。如何寫好人物的表情,有句行話:“貼著人物寫”,這也成了寫作中一個亙古不變的命題和探索不盡的奧妙。好的作家在寫人物時,就像一條嗅覺敏銳的獵犬,會跟著、盯著人物奔跑,也驅逐著人物。而寫好表情,也就是“跟著、盯著和驅逐”之中,恰如其分地表達出來。
魯迅在名篇《故鄉》中,寫到閏土時:紫色圓臉變作灰黃,眼睛腫得通紅,頭戴破氈帽,身著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著,手又粗又笨而且開裂。這是一個鄉下農民飽經風霜和時間打磨的模樣。兩個兒時玩伴終究再次見面,免不了要寫到閏土的表情。魯迅是這樣寫的:“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凄涼的神情;動著嘴唇,卻沒有作聲。”
歡喜和凄涼,兩個看似平常的表達表情的詞語,卻道出了時隔多年再次相見的陌生性和距離感。因為“我”是老爺,而曾經強勢的少年閏土只是“我”家的一個佃戶、奴仆。于是,魯迅接著寫道:“他的態度終于恭敬起來,分明的叫到:老爺!……”
那個工于心計的裹腳女人楊二嫂出場時著墨不多,僅“圓規”二字就惟妙惟肖。面對“我”的忘卻,她“很不平,顯出鄙夷的神色……’”
顯然,魯迅是走進人物內心深處的。人的異化、奴役,那個黑洞里所存在的,他不去濃墨重彩,卻只是以一個表情、一聲稱謂、一聲冷笑,人就活了。那個鄉村冬天的寒凜,那個時代的冷漠,人人知道但不肯述說的東西,潑墨般地在大地之上向我們展開。
我有個曾獲第四屆張天翼兒童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島上離歌》,寫了一個第一次走出大山的少年成長的故事。他冬天隨著父親來到洞庭湖上的一個無名小島砍割蘆葦。我的筆墨圍繞著這個天性好奇、調皮又有些內向的少年展開。少年誤闖蘆葦蕩迷失方向,終于辨清來時的腳印,如釋重負地跑出來,像是心中藏著一個秘密。我是這樣寫他的表情:“力波無端地笑起來,小臉白里透紅,像樹上自然成熟、綻裂的石榴。”
我以比喻的方式來寫一個孩子緊張感化解之后的慶幸和放松。而在寫父親參與追捕毒鳥人遇難后,我這樣寫到:“力波咬著牙,蹲在沼澤岸邊,眼睛無聲滴落。”“他張開嘴,但沒有人能聽到他的聲音,盡管他明明是有話要說出來的。”
父親的遇難是緊張、悲痛的,但少年在經歷這些苦難后學會了成長,我以結合動作和心理感受的方式書寫少年孤寂的情緒,他的表情就多了隱忍,也就是貼著人物,并走進人物內心深處去窺探去發掘的。
寫人物離不開對生活的細密觀察和對生命的敏銳體悟。越深刻,越真切,你所能表達出的情緒就越與眾不同。如美國作家納博科夫說一個真正的作家:“會仿制一個睡覺的人,并急不可待地用手去搔他的肋骨逗他笑。”若此般言說真能做到,那就是紋絲不動卻六路八方皆在心中的武林高手,也才可能漸漸渡游至“下筆如有神”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