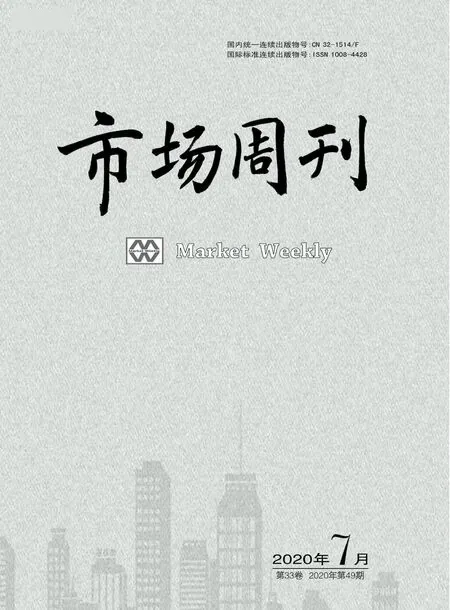電商平臺“二選一”行為的反壟斷分析
代傳花
(華僑大學法學院,福建 泉州362021)
一、 電商平臺中各主體間法律關系的定性分析
互聯網經濟的發展模式因其雙邊性特征而與傳統經濟存在天壤之別。 平臺經濟打破傳統商家向消費者“一對一”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的模式,電商平臺通過提供免費的平臺服務以聚集廣大用戶資源,并以此用戶資源為資源媒介吸引投資以獲得收益。 因此,界清平臺不同主體間的法律關系,是對電商平臺“二選一”行為進行反壟斷分析的首要步驟。
《電子商務法》針對電子商務領域的特殊問題確立了獨立的規制標準,例如第35 條專門針對電子商務經營者濫用相對優勢地位進行了獨立規制,使得對電商平臺實施“二選一”行為的規制取得了合法依據。 在立法者看來,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相較于平臺內經營者享有“天然的優勢”,而與其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無關。 據此將電子商務平臺與平臺內經營者簽訂的“二選一”協議解釋為第35 條中的不合理交易規則,應屬于合理性解釋。 因此,在分析電商平臺“二選一”行為時,就電商平臺與平臺內經營者之間的關系而言,在適用反壟斷規制出現舉證困難而難以認定電商平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時,《電子商務法》確立的濫用市場優勢地位可以發揮獨立的規制作用。
電商平臺為取得優勢而不顧消費者合法權益,時常強迫其合作商在該平臺與其他經營者之間做出不兼容選擇的行為。 “3Q 大戰”中最大的爭議焦點就在于不兼容行為能否納入限定交易的規制范圍,是否應包含“多去一”的不兼容行為。 該類不兼容行為雖針對特定對象,但具有很大的強迫性,超級電商平臺利用其市場支配力實質性實施限定交易。
電商平臺的行為表面上沒有違反《反壟斷法》中限定交易的規定,但其不兼容行為在本質上損害了鼓勵市場交易的立法目的,極大地沖擊了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
二、 電商平臺“二選一”行為的反壟斷分析
(一)《電子商務法》對相對優勢地位的規制
互聯網巨頭依靠網絡的擴散性及用戶鎖定效應,利用其競爭優勢地位進行不正當競爭,嚴重破壞市場競爭秩序。 然而,目前司法實踐中迫于我國《反壟斷法》缺乏對濫用優勢地位的有效規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將優勢地位行為約同于市場支配地位,進而套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規定對其進行規制,結果往往造成其在法律適用上無法認定的困境。 因此,在對電商平臺“二選一”行為進行反壟斷分析時,區分相對優勢地位與市場支配地位的界限,科學設立相對優勢地位的認定標準并設置相應的法律責任具有緊迫的必要性。
首先,電商平臺實施的“二選一”行為具有破壞市場競爭的危害性。 司法實踐中濫用相對優勢地位案件的被告多為互聯網巨頭,如BAT,此類企業在財力、技術、資源等方面明顯具有市場優勢地位。 而弱勢企業若喪失與網絡巨頭交易的機會則會損失巨量經濟利益甚至走向消亡。 因而掌握互聯網話語權的網絡巨頭利用其優勢地位從事“二選一”等限制交易的行為,在損害弱勢企業發展的同時,進一步強化了其優勢地位,形成“強者愈強,弱者消亡”的局面。 其次,巨頭電商平臺利用弱勢企業對其的依賴性而實施“二選一”,使得無力競爭的對手“暫時”接受不公平交易規則,而后通過另一邊市場的二次交易行為將其損害轉移給終端的消費者,致使消費者承擔最終的不公平交易的代價,即通過抬高價格、降低服務質量等形式以補充其損失的經濟利益。
(二)《反壟斷法》規制電商平臺“二選一”行為的邏輯
1.相關市場的認定邏輯
對電商平臺“二選一”行為是否構成壟斷行為的邏輯起點是對相關市場的認定。 從產品替代分析法到SSNIP 分析法的轉變,是世界各國界定相關市場實踐中破解壟斷行為的思路。
而在大數據產業中,基于商品、服務的雙邊市場,網絡的擴散性及外部性等特性,在界定平臺經濟中的相關市場時,采取綜合標準方案,將雙邊市場概念納入其中是應對互聯網經濟特性的應有之義。 其一,基于大數據產業的網絡外部性及用戶鎖定效應,電商平臺用戶對商品、服務的價格敏感度下降,而基于轉換成本、習慣等因素的考慮,面對產品的小幅度漲價,并不會直接導致平臺經營者的用戶量減少。 故在對SSNIP 分析法進行改進時,可以適當提高漲價的幅度范圍,并綜合考慮產品的性能、競爭者數量等因素。 其二,基于電商平臺的雙邊市場特性,具有支配力的電商平臺通過對一邊的市場支配輻射另一邊市場的競爭格局。 而法院在實踐中對互聯網反壟斷案件中的相關市場的界定進行模糊性處理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現行《反壟斷法》中尚未引進雙邊市場概念,致使缺失明確的法律指引司法實踐。 故在對電商平臺經營者進行反壟斷分析時應適應互聯網經濟競爭模式特性,引入雙邊市場概念以指引司法實踐。 此外,我國學者在理論上嘗試為互聯網界定相關市場提供其他解決思路,如盈利模式測試法。
2.市場支配地位的認定
對電商市場支配地位的認定是對其進行反壟斷規制的關鍵點。 市場結構方案是實踐中各國認定市場支配地位的最核心要素,而我國《反壟斷法》在對市場支配地位進行認定時,采取綜合要素標準與市場份額推定結合,技術條件、財力和其他經營者的依賴程度等構成該標準的核心要素。 我國對市場支配地位的考量標準看似明確而具體,然而在反壟斷司法實踐中,原告難以對市場支配地位進行舉證成為反壟斷司法適用的一大困境。 以“3Q”大戰為例,2010 年QQ 的市場占有率已經達79.1%,依照其在即時通信的市場份額應能推定QQ 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然而,最高人民法院終審中卻否定了QQ 的市場支配地位。 可見,網絡經濟中相關市場邊界的模糊化和不確定性,使得市場份額在認定市場支配地位的構成要素中的地位下降。
市場份額在電子商務中對于認定市場支配地位的參考價值明顯下降,因此,在認定互聯網平臺的市場支配地位時,應采取綜合標準方案,弱化市場份額的單一認定標準。 在保留市場份額判斷要素的基礎之上,對市場份額進行計算時應淡化價格分析,重視對瀏覽量、點擊量、銷售量等數據的綜合分析。 同時,應考量電商平臺的網絡效應和動態的市場進入壁壘,綜合衡量影響市場支配地位的相關因素。
3.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認定
反競爭效果因其直接顯明濫用支配力的危害性而成為各國反壟斷實踐認定濫用支配力的依據,即主要考量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企業實施的行為是否排除或限制了市場競爭、損害了消費者權益等結果要素。 我國《反壟斷法》針對電商平臺“二選一”行為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具體法律規制,主要體現在我國《反壟斷法》第17 條的限定交易條款。 根據該款的立法目的,凡經營者實施利用其支配力干預交易相對人、競爭對手的交易自由而無正當理由的行為,應認定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電商平臺“二選一”行為能否認定為限制交易,是對其進行反壟斷規制的前提依據。 我國《反壟斷法》第17 條對限定交易進行規制的目的在于禁止具有市場支配力的壟斷企業通過不正當手段損害交易相對人的正當權益,側重于損害結果層面的分析,而電商平臺“二選一”表面上給予商戶在指定之外的選項里享有自主選擇權,實則在后果上產生排除、限制市場競爭的效果,構成反向限制交易。 具體而言,在電商平臺實施“二選一”的行為中,以“東貓大戰”案件為例,能否在認定“二選一”行為的實施者天貓在相關市場具備支配地位的前提下,進一步認定其“二選一”行為構成限制交易? 就此必須結合互聯網行業競爭的特點,綜合市場行為及競爭效果、產品性質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 從《反壟斷法》的條文規定來看,具備“市場支配的地位”這一主體身份的主體凡實施壟斷價格、虧本銷售、拒絕交易等行為,即受到第17 條的規制,而無須另行考慮該行為是否實際引起反競爭后果。 而從現有的判決來看,是否應將涉嫌的行為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結果納入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構成要件存在爭議。
電商平臺實施“二選一”行為雖然與限定交易有相似之處,且都在效果上限定了交易相對人的選擇權,但其并非屬于第17 條嚴格意義上的濫用行為,對于其他未列明的非典型濫用行為而言,“二選一”行為的定性因不能直接依法條得出結論。 故法院在對“二選一”行為進行認定時,應當從損害后果上對其是否實際造成了“排除、限制競爭的結果”進行深度評價。 從法律目的解釋出發,《反壟斷法》列舉的幾種典型濫用行為,在內涵上囊括了“產生排除、限制競爭的結果”的應有之義。
三、 電商平臺“二選一”行為法律規制的可行性探析
(一)《電子商務法》與《反壟斷法》的補充與銜接
在司法實踐中,基于互聯網平臺的專業性、雙邊性、用戶鎖定效應及免費模式等特性導致原告因舉證責任過重而導致敗訴。 而《電子商務法》第35 條基于對平臺經營者優勢地位的直接的獨立規制,使得原告舉證難的困境迎刃而解,不僅保護經營者訴諸權利救濟的新鮮路徑,更在制度層面激發了對不正當競爭的預防機制。 《電子商務法》承繼《反壟斷法》對限定交易的規制,并進一步在網絡經濟背景下對其不足進行彌補,當難以對電商平臺的市場支配地位認定時,執法及司法機構不會因《反壟斷法》過高的適用門檻而難以對限制交易進行追責。
在司法及執法實踐中,在對電商平臺實施的“二選一”行為進行法律規制時,應重點把握《反壟斷法》這一對壟斷行為進行規制的主線作用,對經過法院論證能夠認定為“壟斷行為”的法律事實,依法進行反壟斷規制。 此外,在無法進行壟斷認定時,正視《電子商務法》的補充作用,通過法律規制上的銜接,增加對電商平臺“二選一”行為規制的合力,使得二者在維護互聯網經濟環境上相得益彰。
(二)將“二選一”行為納入公益訴訟制度
運用反壟斷公益訴訟制度對電商平臺“二選一”行為進行規制,不僅符合反壟斷的立法精神,在實踐上亦具有操作的可行性。 首先,反壟斷公益訴訟維護市場秩序及消費者群體的初衷與反壟斷法的宗旨一致。 電商平臺實施的“二選一”行為損害的消費權既涉及民事權,亦損害公權性質的社會性權利,即涉及社會公共利益。 其次,基于壟斷行為致害的復雜型,平臺經營者實施的壟斷行為造成的損失,不僅包括直接的經濟損失,也包括間接的非經濟損失。 同時,壟斷違法行為造成的損失具有發散性特征,而受壟斷行為沖擊的消費者力量微弱,且存在訴訟動力不足、舉證難度大的現實難題。 因此,引入反壟斷民事公益訴訟制度,不僅回應了反壟斷司法實踐的要求,也更利于保護消費者權益及社會公共利益。
就反壟斷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而言,各級檢察院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理應具有提起該訴訟的主體資格,而其他社會組織如消費者協會是否具備訴訟主體資格雖不明確,但基于保護公共利益及訴訟效率考慮,應根據《民事訴訟法》中民事公益訴訟的精神內涵賦予其訴訟主體資格。 即便反壟斷民事公益訴訟會耗費高昂的訴訟成本,但其在維護市場競爭秩序方面的作用是私人訴訟無法比擬的。 同時,反壟斷訴訟的私人救濟作為一種基本的民事權利,不應以公益訴訟的實施而喪失其存在的私權救濟途徑,反壟斷公益訴訟勝訴后,受損害私人主體仍可就其受到的損失單獨提起民事訴訟。
(三)建立懲罰性壟斷損害賠償規制
相較于普通的民事損害而言,壟斷行為對其他經營者及消費者的損害具有難以比擬的擴散性。 故應加大對壟斷行為的經濟懲處力度,增加其違法成本,在對受害者進行經濟補償的同時,增強反壟斷司法的實施效果。 一方面要適當擴大壟斷行為的賠償范圍,就反壟斷行為的經濟賠償范圍而言,除直接損失外,受害者遭受的可期待利益應當包含在賠償范圍之內。 對因客觀情況而無法確定損失的,可允許法院運用自由裁量權綜合考慮原告受損情形、被訴壟斷行為情節因素確定賠償損失。 同時,將懲罰性經濟補償定為三倍是合理的,此外,就行政壟斷行為而言,其行為實質上屬于國家機關及公職人員實施的違法行為,故將相對人的損失納入國家賠償范圍具有合理性。
四、 結語
為了保持競爭優勢,電商平臺實施的“二選一”行為屬于不正當商業手段,在直接損害競爭者利益的同時,更在宏觀意義上破壞了正常的市場競爭秩序。 而司法實踐中法院在認定相關市場及支配地位的最大困境在于其行為的隱蔽性,作為應對的對策,在對電商平臺“二選一”行為進行反壟斷規制時,務必將平臺內各主體法律關系的剖析放在首位,借鑒先前的司法實踐,結合電子商務的特性改進相關市場及市場支配地位的認定思路和方式,根據具體情形將市場支配地位與相對優勢地位進行區分,規制損害市場競爭秩序的行為,重視發揮《電子商務法》的補充規制作用。 此外,提取公益訴訟制度的有益因素,將涉及公共利益的反壟斷案件結合公益訴訟制度。 同時,為進一步提高反壟斷規制的震懾力,加大壟斷實施者的違法成本以及健全反壟斷損害賠償規則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