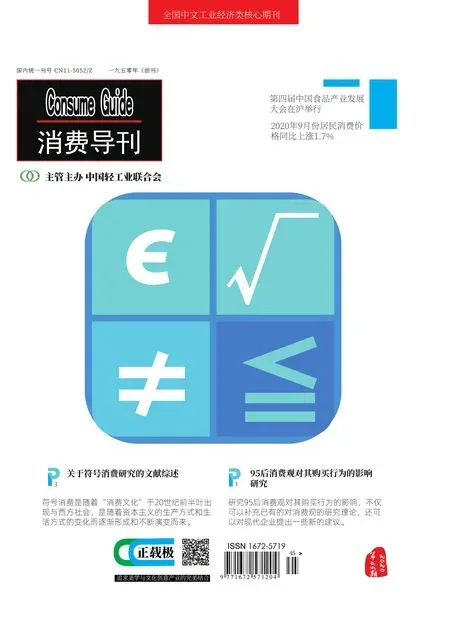關于符號消費研究的文獻綜述
石彩文 上海師范大學
讓·波德里亞認為,在現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的生產,從實質上來說,已經不僅僅是對使用價值的生產,而是對符號價值的生產。消費也更多的關注的是這個符號的附加值。消費作為馴化人的社會機制把人由生產者變為消費者,這一機制的關鍵在于消費社會中的人們消費物時,物的功能和價值發生了轉換——由使用價值轉換成符號價值[1]。這說明在商品內部占主導地位的不是商品本身的使用價值,而是商品的符號價值,這些帶有差異性的符號價值也會為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帶來差異化心理的滿足。物品的豐盛使它的使用價值不再局限于生存,更多的是為消費主體帶來的心理上的滿足。因此在整個的消費過程中,物品的符號價值超越物品的使用價值,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
與符號消費相關的關鍵詞組合起來也很容易解釋我們的消費社會的現狀,在我們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關系的不斷優化,使得物的生產更加豐富,符號化的商品開始主導人們的消費觀念。人們對物的使用和消費所不斷形成的炫耀性消費和夸示消費觀念沖擊著我們的意識形態。
一、符號消費觀的演變
“消費文化”出現于20世紀前半葉的西方社會,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而逐漸形成和不斷演變而來。它的出現將人類的文化消費作為一種獨立的表現形式從物化消費中脫離出來,并賦予了它特定的內涵和社會形態[2]。這個時候的“消費文化”已經逐漸的從物當中抽離出來,并且有了自己特有的含義和價值。作為消費文化理論的核心概念“符號消費”最早由法國社會學家讓·波德里亞提出,他早在1970年的著作《消費社會》中提出,他認為人們通過消費不同的物品來界定自己的身份,并且與其他人的身份相區別。從讓·波德里亞的觀念可以看出,人們真正消費的不是商品的使用價值,而是商品的符號價值。這種以符號化、物化來衡量人們的消費標準的消費觀念隨著工業革命向世界各地擴散。
19世紀后的美國消費主義,主要是以“上流社會炫耀性”消費為其主要特征的,即購買商品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獲得直接的物質滿足與享受,而更是為了獲得心理上的一種滿足[3]。在這樣一個夸示性的消費時代,商品所持有的某種含義已經成了人們身份的一種象征。消費者或者消費者群體會以某些特殊產品和服務的價值為基礎,形成他們的自我意識和身份認同[4]。所以,他們所進行的消費是為了展示自己的社會地位,也是為了展示自己的社會聲譽、社會名望。發展到現在的符號消費與原來人們的消費心理相比沒有多大的變化,對符號消費的理解可以從兩個層面來進行:第一個層面是商品的符號化。商品的符號化是商品價值的發生和發展,正是因為商品的價值存在并且符合使用價值等消費者對商品的一系列要求,才會在商品價值的不斷發展過程中形成商品的符號化。第二個層面是符號意義的商品化。符號意義的商品化發生在商品的符號價值的確立的時候。這個時候,商品所包含的符號價值已經遠遠高于商品僅有的使用價值了,人們對商品的認可也不再是商品的使用性,而是由于符號為商品或品牌增加了某種文化或者精神上的附加值,商品或品牌的符號所包含的意義成為了人們的社會地位、消費品味等的一種象征。
二、符號消費的研究延伸
關于符合消費的延伸主要集中于讓·波德里亞提出的消費社會、符號價值、消費文化、消費主義、身份認同等幾個方面,還包括意識形態、符號學等。符號消費的形成也是在人們的意識形態中不斷成形的,最初以物為出發點,再到物被人賦予了某種文化或者精神上的附加值的時候,人們消費的注意力也就隨之轉向了這種附加值上面。這也是人們在消費社會中確認自我歸屬和身份的內在需求。因此,卡西爾把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在消費社會的語境中,傳統的信仰的禮制制度遭到破壞,人們失去了穩定的統一自身存在和表達自我之意義和價值的原有參照符號系統[5]。
圖1是筆者在中國知網的高級檢索中選擇的所有文獻的發表年度趨勢,從圖中可以看出關于符號消費的文獻發表在2012年和2016年呈現接近60篇的趨勢,并且在2006年的研究數量上升幅度大。單從中國知網的文獻年度發表情況來看,我國關于符號研究的趨勢和熱度是逐年上升的。

圖1 符號消費研究的論文年度發表趨勢
圖2是我國關于符號研究的主題分布,其中最為主要的依然是符號消費,其研究數量在總的研究主題中占35.4%,其他依次是符號消費、消費者、讓·波德里亞、生產關系、消費社會符號化、消費文化等。從這些研究主題的分布可以看出,我國關于符號消費的研究可以大致分為三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是從讓·波德里亞提出的消費社會出發,從他的文獻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來分析符號消費;第二個方向是從消費本身出發,延展到消費社會、消費文化等人們的消費日常的各個方面;第三個方向是從符號學的角度出發,來研究符號在消費中的作用,符號對人的消費心理產生的作用以及符號消費對人產生的符號化現象。當然,這些研究的大前提背景是資本主義的消費社會,以及研究的主要對象還是人和物的關系。關于我國的符號消費的研究主題的客觀呈現也是以符號消費為中心點,分以上三個層次來深化研究的。

圖2 符號消費研究的主題分布

圖3 符號消費研究Citespace網絡分析
圖3是與符號消費相關的研究體系,無論這個研究體系怎么發展,都是基于物——商品所持有的特殊意義而形成的人們對于符號消費的反思的研究體系。這個研究體系的形成也為我們的研究找到了方向。從上圖我們也不難出,符號消費的本質是一種文化消費,是一種把消費和文化體驗相掛鉤,標榜消費者個人或者群體身份認同和社會地位的一種消費方式。
(一)符號消費中的大學生消費觀
關于大學生消費觀這方面的研究也是當下比較熱的一個話題,大學生作為一個不可忽視并且消費潛力巨大的一個消費群體,在他們的消費觀念中也出現了“符號化”、“超前化”的新興消費觀。關于大學生“符號消費”的表現主要有以下幾點:(1)關注價格、質量、實用性的同時也注重外觀、品牌和流行性;(2)消費傾向“符號化”,追求商品或消費品的符號價值;(3)消費傾向“超前化”,追求暫時性的物質享樂[6]。這些消費表現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大學生的消費心理和消費習慣,追求差異化的這種心理也不僅僅在大學生這個消費群體中有體現,同樣在其他的消費群體中也有。我們所處的媒介環境是大眾媒介環境,也正是在大眾媒介環境 的“勸導和馴化”之下,我們逐漸的失去了自己本身對物的理解的自由星和對商品所持有的其他文化或精神的自由型,從而變成了被大眾媒介所支配的單向度的人。
(二)符號消費中的身份認同
我們人類發展的過程本就是一個不斷多自我的身份進行認同的過程。從認同的歷史變遷來看,它不是純粹生物性的,而是社會性、精神性認同所發生的階段性變化[7]。消費社會對人的身份認同的構建是以商品為出發點的,但是最終的歸屬點卻是人的商品符號所附加的文化或精神的認同。這樣一個認同過程,也說明了人們自我的身份認同是社會性的和精神性的,而且從社會性的身份認同到精神性的身份認同也在人在自我身份認同過程中不斷深化的一個過程。現代社會的消費階段已經是一種大規模的消費了,發達的市場經濟和充裕的商品,在很大程度上讓人們的消費產生了很大的認同,而且這種認同感越來越一致。這就體現在人們通過消費來展現他們的身份,地位或者個性等,并且獲得他人的認同,這種方式都是通過消費來獲得和實現的。盡管具有文化象征意義的符號消費不是唯一人們產生認同的方式,但是這種具有文化象征意義的符號消費在很大程度上對認同感的構建有很大的作用。“人們通過向別人傳達信息來定位自己,而這種信息的傳達是通過他們加工和展示的物質產品和所進行的活動方式實現的。人們對自己進行熟練的包裝,由此創造并維持自己的‘自我身份’。物質商品的不斷豐富給這一過程提供了支柱。在一個物質產品不斷豐富的世界,個人的身份成為一個對個人形象進行選擇的問題,而以往任何時候都不曾如此。人們也越來越不得不對他們的身份做出一定的選擇。”[8]
(三)符號消費中的意識形態變化
20世紀50年代以后,晚期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早期的由商品生產占主導地位的社會轉變為由符號消費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社會的意識形態也由早期的機器主導轉變為符號為主導。英國思想家伊格爾頓曾言:“在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符號與經濟的聯系被切斷;現在,這兩個領域卻被不適當的重新結合起來,因為經濟領域已經深深地滲透到符號領域。”就拿當前的“古物”收藏和“藝術品拍賣”等,都是一種對物的非功能性價值的定義,也說明符號或者商品所攜帶的經濟性是存在的,而且還是普遍存在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在商品審美化地同時,又特別重視商品審美時尚化的建構。之所以追求商品生產的時尚化,也是為了加快商品消費的速率和激發人們的消費欲望,以及自己被承認的愿望[9]。提高商品的時尚化也是我們現在的品牌所追求的目標,越來越多的人在消費的過程中有自己的消費理念和消費習慣,并且在尋求差異化的心理催化的情況下所形成的意識。這種器物加文化的相互結合也讓人們深信消費這樣的產品可以帶來某種社會價值的體現或者自我認同的歸屬感。
(四)符號消費中的異化
符號消費中的異化表現為三個方面:一、商品生產和消費中人的異化。馬克思在對“異化勞動”理論進行論述時曾明確指出:“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產品,作為異己的東西,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獨立力量,是同勞動對立的。”[10]這說明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人通過在勞動生產過程中生產的勞動產品是異己的,而且是不依賴與生產者的,因此物通過控制人來對人進行異化。二、符號消費中的人的異化具有間接性的特征。消費中的人的異化使得人和人、人和物之間的關系都隱藏在符號的背后,但是這種異化也是更加強烈的。三、符號化的人的生存狀態。符號化的商品所具有的文化意向超越了商品的使用價值[11]。人在大眾媒介的勸導和馴化之下,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對物的選擇的自由性和消費習慣的自主性,從而變成了單向度的人。
三、符號消費的作者互引現狀
一些學者關于符號消費的研究,都是以讓·波德里亞的《消費社會》為出發點,從意識形態領域去研究人們的消費行為和消費文化,也有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研究人們的消費心理。圖4是關于符號消費的作者互引現狀,從圖中可以看出,除了讓·波德里亞之外,還有邁克·費瑟斯通,他的著作有《理論、文化和社會》、《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等,他的主要研究的興趣和內容是消費文化、全球化等。他認為,大眾的文化消費是具有破壞性和主動性的,并且大眾文化的生產和消費者所產生的消費從本質上來說是一個控制和抵制的過程。而且人們的消費意識中盡管存在著一定的被商品所異化的因素,但是被消費社會完全的控制是不可能的,因為消費并不是完全被操縱的文化工業的產物。另外被引用的次數多的人是羅剛、王中忱,他們主編的文獻是《消費文化讀本》,該書中提出:憑借時尚總是具有等級性的這樣一個事實,社會較高階層的時尚會把他們自己和較低階層的區別開來[12]。這也說明在消費社會中所謂的“時尚”是可以構建階級的,而且這種階級也是可以被打破的。

圖4 符號消費論文的作者互引現狀
四、總結
關于符號消費的研究,研究者的關注點也更多的是在“符號”和“消費”這兩個方面,無論是在意識形態方面還是在人們的身份認同方面都是對符號消費研究一個再研究和再思考。這也是人們在消費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問題,就是商品的這種符號化的生產作用讓商品的流通擴展產生了社會的自主文化形成,從而產生了一種獨有的商品邏輯。這種形成的商品邏輯也讓消費者的關注度更加集中在商品的符號所持有的附加值和為消費者賦予的社會地位,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也是加劇了消費者的差異化心理和攀比心理。因此,我們需要做的是保持理性并且用審視的目光去進行消費,而不是符號消費中的異化使得不斷實現著的異化變成了我們消費者的內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