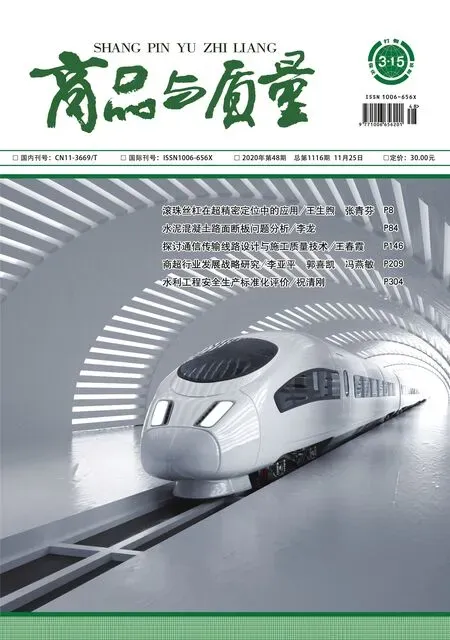企業參股發電項目融資結構簡析
胡磊
揭陽前詹風電有限公司 廣東揭陽 522000
1 股權合作方的選擇
項目股權合作方的選擇可以決定項目融資乃至整個項目的成敗,股權合作方要實現優勢互補、目標互補。在本項目上,雖然合作雙方磨合起來爭執不斷,但從客觀上講,雙方實現了很強的互補,不可分割[1]。A集團是孟加拉國知名私營企業,主要產業涉及銀行、房地產、鋼鐵、水泥,但對電力行業了解有限,沒有大型電力項目投資經驗,而且始終想葆有項目絕對控股權,必然無法吸引中國大型國有電力投資方參與投資,而沒有行業資深企業的參與,A集團既無法通過IPP項目(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的招標資格預審,拿不到開發權,更不可能獲得銀行貸款。此外,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之后,歐美、日韓金融機構逐漸退出對煤電項目的支持,只有中資金融機構、東南亞金融機構仍在支持煤電,融資來源相對較少,作為大型煤電項目,只能優先考慮中資金融機構,因此不得不選擇有較強資金實力、愿意參股投資的中資國有電力施工企業作為股權合作方。
2 顧問的選定
海外綠地電力項目涉及交易協議眾多,交易對手包括項目所在國政府機構、跨國投資方、購電方、國際煤炭礦主或貿易商、EPC承包商、運行維護承包商、國際國內金融機構等,項目公司(融資方)必須選擇熟悉國際慣例、行業規則、中資金融機構融資或保險要求、項目所在國電力項目運作模式、業務水平出眾、溝通協調能力優長的國際知名機構作為各類顧問,忽略任何一個方面,都可能出現偏差,影響項目順利推進,其中法律顧問的選擇尤為重要[2]。為了保障自身利益,中國信保和貸款銀團也會分別聘請法律顧問、技術顧問、財模顧問,另行聘請保險顧問,而且往往要求挑選國際知名機構,費用由項目公司(融資方)支付。為了確保雙方顧問實力相當,項目公司也需要聘請綜合能力比較強的顧問。在本項目上,法律顧問M律所參與過多個央企投資或承攬EPC并由中資金融機構保險或融資的項目,其中不乏電力項目,熟悉央企、中資金融機構的運作模式和要求,具備協調能力,并與孟加拉國當地知名律所有緊密合作關系,在項目推進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他顧問也都是同行業世界知名機構,在合同范圍內比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3 關鍵項目合作方的選擇及相關協議的談判
3.1 購電方選擇及《購電協議》的談判
一般而言,為了方便管理或滿足IPP項目公開招標要求,購電方或政府部門會起草統一的《購電協議》模板,孟加拉國的《購電協議》模板由世界銀行協助起草,比較關注投資者利益的保護,基于照付不議(TAKE OR PAY)的原則,按照兩部制電價結算(即容量電價CAPACITY PAYMENT和電量電價ENERGY PAYMENT),容量電價按照電廠在供電計量點供給電網的“可用容量”測量、計量,唯一的支付前提是機組可用、容量充足,與供電方是否調度電廠滿發無關,可以覆蓋投資方的開發費用、還本付息、投資回報、資產折舊、稅負保險和固定運維費用;電量電價按照電廠在供電計量點供給電網的實際上網電量計算、支付,主要包含燃料成本和變動運維費用。《購電協議》約定電費以美元計價,當地貨幣(塔卡)支付,并設定了塔卡兌換美元的機制,內容完備、條款公允[3]。由于IPP投標時《購電協議》模板就已披露,因此購電方不接受投資者對《購電協議》提出過多修改意見,但貸款銀團(含中國信保等ECA機構)及其律師則可以提出意見,以使貸款方利益得到更好的保護。本項目的《購電協議》正式簽訂后,在融資談判過程中,貸款銀團與孟加拉國電力發展局(BPDB)就有關條款舉行多輪談判,持續時間將近兩年。
3.2 《執行協議》的談判
《執行協議》主要約定了孟加拉國政府在本項目上的義務,比如在項目并網前6個月之前建設好廠區外輸電線路,保證購電方按照《購電協議》支付電費并提供擔保,確保外匯兌換,不得征收項目資產等。不是每個國家都有《執行協議》,有些國家會簽署《特許經營協議》約定上述義務,保護投資者利益。《執行協議》或《特許經營協議》的簽約一方是項目公司或投資方,另一方一般是項目所在國政府部門。本項目《執行協議》的簽約方為項目公司和孟加拉國能礦電力部、PGCB。協議正式簽訂后,在融資談判過程中,貸款銀團與孟加拉國能礦部就有關條款舉行多輪談判,持續時間將近兩年[4]。
3.3 煤炭供應商的選擇以及《供煤協議》的談判
燃料是火電廠的能量來源和命脈,安全、充足、及時的燃料供應必須獲得完全保證,貸款銀行和中國信保一般要求在融資關閉前簽署《長期供煤協議》,以規避燃料供應風險[5]。此外,購電方BPDB基于環保要求,在《購電協議》中規定了煤炭的水分、灰分、硫分等成分比例,單純一個礦山、甚至一個國家的煤炭很難達到上述成分比例要求,投資方需要從多個來源采購煤炭,并在煤炭入爐前進行摻配。基于上述原因,項目公司選擇了多家國際知名的煤炭供應商洽談合作,并最終與三家企業簽署了《供煤協議》。
4 結語
本項目是中資企業抱團出海的典范,獲得某副省級城市金融創新獎。中國元素滲透項目的方方面面:參股股東、幾乎全部項目貸款、主要的保險機構、EPC承包商、運行維護的技術力量等,其中EPC合同的中國成分達到了65%,主要設備、材料、施工技術人員都來自中國,極大地帶動“中國制造”、中國技術和中國金融“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