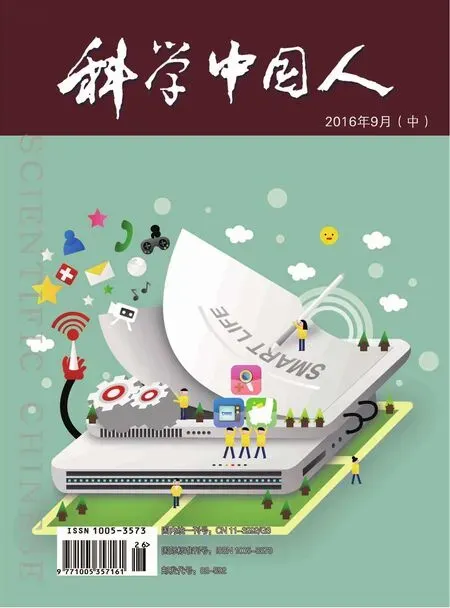新課程下高中語文課程資源開發利用策略探究
任占元
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察右中旗一中
新課程下高中語文課程資源開發利用策略探究
任占元
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察右中旗一中
隨著新課程改革的全面展開,對學生的綜合素質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高中語文作為高中的重點學科,要求高中語文教師要運用各種教學資源,來滿足新課程對學生語文綜合素質的要求。語文課程資源的充分開發與利用,有利于加深學生對基礎知識的理解,提高學生運用語文知識的實踐能力,培養學生的文學素養和審美水平。因此,教師應當充分開發并利用語文課程資源,提高學生的語文學習能力和綜合素質水平。
高中語文;課程資源;開發
新課程改革提出,在課堂教學中,要發揮學生的主體性作用。因此,為提高語文教學質量,高中語文教師要不斷豐富教學形式,使學生能夠充分參與到語文課堂學習中來。充分開發利用高中語文課程資源,有助于發揮學生的主體性作用,增強教學內容與學生實際生活的聯系,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從而使學生能夠充分的運用語文知識。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應當充分運用語文課程資源,充分激發學生學習語文知識的興趣,從而提高高中語文的教學質量。
一、語文課程資源作用和意義
(一)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基礎能力
語文教材是學生學習語文知識的載體和基礎,語文教材不僅能夠使學生充分掌握語文基礎知識,教材中的課文、古詩詞等對于提高學生的文學素養,拓寬學生的語文視野,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教師日常的語文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當不斷更新教學內容和形式,引導學生通過自主學習課文知識的方式,使學生能夠自覺主動地獲取語文知識,提高對課文知識的了解,更加深入的理解并感受課文中所蘊含的思想感情與文化內涵。此外,語文教材資源的充分利用,對于使學生形成正確的學習方法和習慣,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水平也很有幫助[1]。
(二)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
新課程的改革要求,要全面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學生語文實踐能力的提高,離不開語文課程資源的支持。學生語文綜合能力的運用和實踐,需要依托一定的資源與環境,語文課程資源的缺乏,會使學生的語文實踐能力得不到充分的鍛煉與提高。圖書館、博物館、植物園等硬件設施為學生語文知識的學習實踐提供了充足的資源,教師應當引導學生充分運用這些資源,來提高學生的語文實踐能力。此外,學校內組織的各種演講大賽、詩歌朗誦大賽等,對于學生提高語文的實踐能力和運用水平也很有幫助。
(三)有助于提高學生的思維能力
隨著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多媒體教學也被越來越多的使用到語文課堂教學中去。多媒體教學的充分運用,使學生能夠更加直觀的感受到課文中所表達的思想感情,加深對課文知識的理解,進一步培養學生的語文思維能力。例如在學習課文中關于山川湖海等自然風光時,通過在課堂上放映相關的幻燈片、音樂、視頻等,能夠使學生從視覺上、聽覺上直觀感受到這些自然風光,使學生在今后的學習中,再學習相關知識的時候,能夠很容易就聯想到,從而鍛煉了學生的思維能力[2]。
二、高中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途徑
(一)重視對語文教材資源的開發
教材是語文教學中必不可少的基礎資源,要提高語文課程資源的利用水平,首先就要提高教材資源的利用水平。新課程改革要求教師轉變思路,靈活運用教材資源,這就要求教師在教材資源的使用過程中,大膽創新,對教材內容進行深入挖掘,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進行具體教學。這樣就能夠充分將教材知識與學生實際相結合,使教材知識生動形象的展示在學生面前,從而降低學生的學習難度。例如在學習魯迅先生的《少年閏土》時,除了課文知識的學習,還可以引導學生學習紹興當地民俗,聯想當時的社會風俗等,從而使學生能夠全面的了解和掌握課文內容。
(二)多開展語文實踐活動,提高學生的實踐水平
當下高中語文教育,更加注重學生語文實踐能力的培養與提高。教師可以通過舉辦多種多樣的實踐活動,如詩歌朗誦大賽、辯論賽等,提高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與現場表演能力;也可以通過在班級或學校內舉辦黑板報、周報的形式,來鍛煉提高學生的文學水平。這些活動無論是在課上還是課下,都能夠最大化的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與主動性,提高了學生的語文學習能力和水平,從而全面提高了語文綜合素質[3]。
(三)加強和完善多媒體教學
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多媒體教學的廣泛應用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教師應當順應形勢,充分運用多媒體教學,不斷豐富語文教學的內容與形式。多媒體教學的充分運用,能夠使學生獲得更多的學習方式與學習平臺,拓寬語文學習的深度與廣度。以《觸龍說趙太后》為例,通過在課前搜集關于春秋戰國時期的一些歷史知識、視頻資料等等,使學生對于課文中所處的大環境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從而在課文的理解上使學生更加易懂,更好地掌握課文中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從而提高了教學質量和水平。
結語
綜上所述,語文課程資源的充分開發,對于提高學生的語文綜合素質,靈活運用語文知識,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師要提高語文教學質量,就必須充分重視對高中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利用,引導學生從各個方面學習語文課程知識,提高學生學習語文的積極性。只有這樣,才能滿足當下新課程改革對于高中語文的教學要求,從而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
[1]郭鵬忠.高中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J].山東青年,2015,(2):54.
[2]陳芳.高中語文地方課程資源開發與利用[J].作文成功之路(中旬),2013,(11):89.
[3]張維哲.高中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策略[J].讀寫算(教育教學研究),2013,(21):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