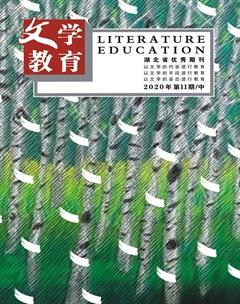淺析《斯萬之戀》的“愛情小樂句”
張逸云
內容摘要:《斯萬之戀》是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第一卷)》中的重要章節。本文以該章多次出現的“小樂句”為主要聚焦點,以斯萬愛情的萌芽、發展和消逝三階段為線索,淺析斯萬愛情的多重含義,初步探討普魯斯特的文學創作美學。
關鍵詞:《斯萬之戀》 小樂句 愛情
作為《追憶似水年華》七卷本中唯一可以單獨成章的故事,《斯萬之戀》較為完整地呈現了斯萬的一段愛情史。其中對于“小樂句”的書寫貫穿始終。但對其重復的描繪并非隨心所欲的反復,而是對斯萬愛情的多次定位與重新闡釋,且斯萬之戀的疑慮、激情、無奈等諸多情感也雜糅其中:愛的小樂句既是初見中愛情萌發的催化劑,又是熱戀中愛情維持的保鮮劑,還是流逝的時光里愛情終結的預警信號。愛情在混淆中可能變得面目全非,客體在時間序列中不可捉摸,一切仿佛轉瞬即逝。只有追憶是與時光抗衡的力量,是對必然性最終的確證。
一.人生若只如初見
“人生若只如初見”?疑問在于,偶然的相遇何以成為此后愛情山盟海誓的確證?憑什么是“這一個”?遇見的偶然性,使愛情的一切都值得懷疑。因此斯萬只能下意識地選擇在奧黛特身上反復尋找愛情的確證。可以說,將相遇的偶然性上升為必然性的動力,并不是主體對客體所產生的愛情本身。斯萬之愛,并非初見剎那萌生之情,而是基于他主觀想象建構的產物。當斯萬頻頻將奧黛特在現實生活中的形象替換成他所愛慕的藝術客體時,奧黛特本人在現實生活中的形象就開始退居其次。對于斯萬而言,重要的并非奧黛特本人的形象真實與否,而是他能在她身上聽到何種聲音(樊特伊奏鳴曲),看到何種形象(壁畫中葉忒羅的女兒西坡拉),聞到何種芳香(菊花),體驗到何種快感(擺弄卡特利蘭花)。自身源源不斷的再生想象累積于奧黛特身上,成為斯萬愛情的初動能。
在愛情確證的過程中,小樂曲的功能不可小覷。在斯萬的愛情埋下種子的瞬間,也許他并未知曉。但這顆種子其實早在他遇見奧黛特的一年前就已被埋下。在某個晚會上,他愛上了一個芬芳的小樂句,它帶著“玫瑰的香味”散發于夜晚潮濕的空氣中,讓斯萬有青春煥發之感。如果說,第一次與小樂句的相遇只是意外,那么此后他對小樂句的苦尋便是突破相遇的“偶然性”,建構“必然性”的主動選擇。當他陪著奧黛特去維爾迪蘭夫婦家,意外地體驗到了與小樂句重逢的欣喜。而正是這原本“無心”的重復,使意外不再被解釋為意外,而指向冥冥之中的注定性。由此,斯萬與小樂句間開始被添加進某種命定的因素,并間接地建構起斯萬與奧黛特之間的情愫,以至于斯萬甚至不由自主地將小樂句當做了他與奧黛特“愛情的國歌”。
斯萬從一開始就混淆了愛情的對象。小樂句作為斯萬愛情的催化劑,并非純粹的客體存在,而是相應地融入于對愛情主體的建構之中。然而,敘述者語調雖多有調侃與反諷,卻并無福樓拜式的冰冷,其字里行間反而不乏諒解式的溫情。實際上,對愛情主客體的混淆遠非只有斯萬一人,日后馬塞爾的遭遇便是最直接的例證。而文本外的讀者在現實中亦有可能扮演著混淆愛情主客體而不自知的角色,這使敘事語言指向了多重調侃的可能。
二.無情不似多情苦
斯萬愛情的“確證”恰似一場疾病的“確診”。真可謂“無情不似多情苦”——斯萬因過于多情而患上嫉妒之病。幸耶?不幸耶?斯萬因嫉妒而體驗到的痛苦固然不幸,但同時不也樂在其中、欲罷不能?小樂句此時已成為“保鮮劑”,其重要功能在于保持愛情的新鮮感。
雖然斯萬愛的只是奧黛特的影子,但他卻時刻追尋著奧黛特的真實形象。“想象發生于非現實的世界,而占有對方的渴望卻動員起我們所有的理智因素在現實世界求馬唐肆,尋覓想象的起源。”①這正是想象的悖論——斯萬企圖解讀出奧黛特一顰一笑背后的秘密,但再三的嘗試卻使奧黛特的過往更加顯得撲朔迷離。顯然,斯萬對此并不罷休,正如當他終于得以透過信封偷看到奧黛特給福什維爾的信時,竟然對自己的“嫉妒”心態感到高興。②可見對奧黛特過往部分的破譯,給斯萬帶來了自得與滿足。但這種滿足感恰恰與嫉妒引發的痛苦相輔相成。換句話說,“揭秘”本是產生痛苦的源泉,本應避之,但斯萬卻從中體驗到了快感。
此時斯萬在愛情中收獲到的趣味,已從對藝術的把玩悄然演變為“考古”的游戲。而斯萬在游戲中則扮演著偵探家的角色,闖關的方式是在歷史的“縫隙”中考證奧黛特的“真實”情史。嫉妒的狂想可能在意識的流動中無限膨脹,亦可能在瞬間萎縮。多層次的體驗如塊莖一般增生,并外化于斯萬對于小樂句的理解中。短暫的自鳴得意、如釋重負的舒心、自虐式的痛苦等情感相互雜糅,但在愛情面前都顯得無足輕重。藝術造詣極深的斯萬,甚至不厭其煩地請奧黛特演奏小樂曲,即便她彈得十分糟糕也沒關系。
對于斯萬的愛情,“有關系”的其實是一種恐懼。一種對愛情未來是否會隨著時間消失殆盡、一張可愛的臉將來是否會在感受中失去魅力的恐懼。正如布魯姆所言:“性嫉妒的面紗實際上掩蓋著對不能永生的恐懼”。③他盼望自己的愛情能以永恒為歸宿,甚至不惜將小樂句比作情感檢驗的香料。④可以說,就算愛情只剩下尸身,小樂句也要充當保鮮劑,盡其所能防止愛情腐爛。因此斯萬不惜沉迷于“考古”的游戲,收藏著奧黛特的一切(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甚至無視自己慣常的審美品味,只為能永久保留熱戀時的新鮮感。
其實,就算奧黛特過去“真實”的一瞬曾被斯萬所確信,這里的真實性仍然值得懷疑。因為這往往只指涉奧黛特想要隱瞞的那一小部分“真實”。再者,哪怕是在現在進行時態中,斯萬的主觀意識也明顯存在著對現實的歪曲。當他與情敵福什維爾一起分享橘子汁時,對奧黛特生活的“妖魔化”想象與眼下平平常常的一幕構成了強烈的內在反差,直指斯萬對愛情的主觀幻想。然而斯萬本人卻無法意識到他試圖“全然地占有某人”的愛情觀所具有的荒誕性。占有欲企圖指向“永遠”,但現實卻不斷使“永遠”的企圖幻滅。因此愛情的“考古”游戲仿佛西西弗斯神話中日夜勞作卻徒勞無功的一場悲劇。
但徒勞本身終止不了斯萬的“主觀”愛情,即便痛苦又虛妄,斯萬還是要將游戲進行到底,這種感受也鮮明地外化于斯萬對小樂句的理解之中。小樂句時刻提醒著斯萬,快樂無法持久。但幸福的回憶卻使此刻的憂愁也變成了昨日的甜蜜。可以說,小樂句既是保留愛情新鮮感的刺激物,又承載了斯萬愛情的多重情感。
但即便他對愛情用心良苦如此,當他的愛情之病“痊愈”之時,卻意識到將自己其實是將“最熱烈的愛情”給了一個“不合口味的女人”,其間的反諷意味不言而喻。
三.此情可待成追憶
作為愛情保鮮劑的小樂句也終會有過期的一天。遺忘一旦到來,荒誕的愛情就化作一場“追憶”。此時愛情的必然性指向了逝去的時光本身。為何時光能成為必然性最好的確證?因為偶然性對應著人生中無法預先確定的各種選擇,而必然性往往是無數選擇被烙印上“過去完成時態”后的呈現。而“預兆”就可以被理解為某種無法避免的天意,不僅出現在“時間開始前”,還重現于“這段時間結束前”。⑤必然性結局與上文所論的偶然性初見相對應,而重現于“時間結束之前”的預兆則不僅僅是意識到將來某人必定會成為我們所愛之人,它更是對這段戀情走向終結的預知。
此時,斯萬的愛情已由“確證屬實”過渡為“論證失敗”階段。但與其說斯萬對自己愛情始末有自覺的反省,倒不如說是小樂句給了他提示。它使斯萬仿佛站在自己愛情先知的立場上,對愛情的失敗加以最后的論證。小樂句鑲嵌于未來某段時間的固定序列中,并被此刻的意識所捕捉。它在樂章之間的跳躍,使斯萬感受到了由小樂句貫穿起來的“分散的主題”,這恰恰隱喻著他與奧黛特之間的愛情主題。但這一主題“就像在必要的結論中的前提”,⑥于是斯萬開始確信,奧黛特終將在他的世界中變得無足輕重。⑦由此可見,這時期的斯萬對于小樂句的感受已經超出了追尋與欣賞,而成為了對未來某一時間的把握和印證。在對小樂句“重現”的角逐中,斯萬意識到了時間的力量。但如果重現是必然的,那么重現過后呢?小樂句隨著時間流逝不也是必然的嗎?因此在他的假設中,奧黛特最終會變得“無足輕重”也成為自然而然之事。
在時光流逝之中,遺忘才是大敵。遺忘意味著擺脫。擺脫體驗不幸、痛苦與掙扎,同時也擺脫發現奧秘的快樂、趣味與把玩。但對于斯萬而言,當他意識到奧黛特曾經對他的感情在時光流逝中不復重現時,卻仍無法自覺遺忘。原因在于,遺忘同樣是流逝時光的給予。因此,即使預知了愛情的游戲難逃失敗的結局,他還是無法自動終止游戲程序,而只能繼續沉淪其中。他的窘迫,他的被動,迫使他最終意識到,其實是愛情的游戲在“玩”他。正如斯萬自己的反省的那樣,在愛情中幸與不幸兼而有之,既“身在福中不知福”,又“身在禍中不知禍”。
愛情在混淆中變得面目全非,客體在時間序列中不可捉摸,寄遇于愛情之上對于藝術的追求,對生活的想象,對多重情感的體驗會因愛情的消逝而淡化。逝去的時光導致了遺忘,若遺忘所有,便只能指向瞬間。從這個意義上,“斯萬之戀”追問的深層問題還在于,愛情的泡沫一瞬如何指向滄海桑田的永恒?只有“追憶”是與時光抗衡的力量,使瞬間凝聚為永恒的新生,使斯萬之戀的必然性得到最終的確證。
注 釋
①徐兆正.普魯斯特與嫉妒[J].藝術廣角,2019(1):88.
②[法]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 第1卷,在斯萬家那邊[M].徐和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4):282.
③[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 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江寧康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4):313.
④[法]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 第1卷,在斯萬家那邊[M].徐和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4):235-236.
⑤[法]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 第1卷,在斯萬家那邊[M].徐和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4):381.
⑥[法]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 第1卷,在斯萬家那邊[M].徐和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4):352.
⑦[法]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 第1卷,在斯萬家那邊[M].徐和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4):353-354.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