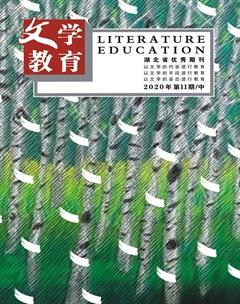涅斯梅洛夫詩歌話語中的悲憫情懷研究
內容摘要:阿爾謝尼·涅斯梅洛夫(1889-1945)是20世紀的俄羅斯詩人,作家,記者,他從1924年開始居住在哈爾濱,是最具代表性的俄僑詩人之一,我想讀過他作品的人很難不被貫穿其中的悲憫情懷所深深觸動。于巴赫金而言,對話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于文學作品中,他主張從文學內部去闡述文學的社會特性,更加注重人文精神的探究。運用巴赫金對話理論來研究涅斯梅洛夫詩歌中的悲憫情懷既為研究涅斯梅洛夫提供了新的視角,又是將巴赫金對話理論應用于文學作品研究的具體實踐。
關鍵詞:涅斯梅洛夫 悲憫情懷 巴赫金 對話理論
阿爾謝尼·涅斯梅洛夫(1889-1945)是20世紀的俄羅斯詩人,作家,記者,1924年開始居住在哈爾濱,是最具代表性的俄僑詩人之一。白軍軍官的經歷為他帶來榮譽的同時也導致了他后半生顛沛流離的人生境遇,我想讀過他作品的人很難不被貫穿其中的悲憫情懷所深深觸動。悲憫是悲傷和同情之意,“悲”是慈悲,它是指一個人對人世間苦難有一種感同身受的情感;“憫”的意思是同情。
前蘇聯著名文藝學家、文藝理論家、批評家巴赫金在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藝術的解讀中提出對話理論,對話理論對文學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巴赫金批判地吸納了社會學文藝學與形式論文藝學的積極成果,主張“從文學內部去闡述文學的社會特性”[1]154,這使得對話理論的內涵掙脫了語言結構和系統的框架,從而更加注重人文精神。巴赫金理論的對話性既表現在不同意識主體的言語行為中,又蘊含在同一價值主體的心理意識中。運用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去探究涅斯梅洛夫作品中的悲憫情懷有助于人們更深刻地了解涅斯梅洛夫和他的作品,同時這又是將巴赫金對話理論應用于文學作品研究的具體實踐。
一.詩歌中的悲憫情懷
涅斯梅洛夫創作的優秀詩篇和小說是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一頁。《中國俄羅斯僑民叢書》回憶錄卷中提到:阿爾謝尼·涅斯梅洛夫是哈爾濱僑民中最有才華的詩人[2]109。
顧韻璞曾說,“我譯涅斯梅洛夫的第一個感覺是他的詩出手不凡,與我過去譯過的許多俄蘇大詩人水平不相上下[3]16—19”。我們注意到涅斯梅洛夫在與祖國隔絕的情況下創作了自己最好的作品。移民促使他發現了自己的詩意天賦,流亡的悲慘境況使他具有抒情的力量和深度。如今,涅斯梅洛夫對俄羅斯文學的創造性傳承已為讀者所接納,這使我們能夠談論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并將他的名字與20世紀最重要的俄羅斯詩人相提并論。
到目前為止,研究者對于涅斯梅洛夫的詩歌研究主要涉及了中國元素、中國情感、藍色情懷、意象研究、其詩歌中蘊含的葉賽寧傳統、神學思想、及其藝術風格獨特性這幾個方面。如榮潔在《涅斯梅洛夫的生平與創作》中主要介紹了涅斯梅洛夫從莫斯科輾轉符拉迪沃斯托克最后定居哈爾濱,直到1945年逝世的人生經歷和其主要創作;康棟的《論涅斯梅洛夫詩歌中的藍色情懷》主要從色彩學、藝術表現手法和宗教三個角度對貫穿涅斯梅洛夫詩歌中的“藍色情懷”進行探究;康棟2012年發表的《論涅斯梅洛夫的詩歌創作》中涉及到了涅斯梅洛夫詩歌中的戰爭、愛情,和中國主題;李暢的《俄僑詩人涅斯梅洛夫詩歌創作中的中國情感》寫詩人詩歌中獨具韻味的中國情調及其對中國獨特的感情;李盼盼2019年發表的探究中國元素的《俄僑詩人涅斯梅洛夫詩歌中的中國元素》等。
筆者通過前人對涅斯梅洛夫的研究發現,研究者對涅斯梅洛夫的詩歌研究多于對其小說的研究,且康棟運用跨學科的方法,用色彩學研究涅斯梅洛夫詩歌中的“藍色情懷”,令人耳目一新。但總體來講,在對涅斯梅洛夫的詩歌和小說的研究中,像戰爭、愛情、死亡這樣的傳統主題居多,且因為涅斯梅洛夫是俄僑詩人,所以探究其作品中的中國相關的主題也相對較多。由此可見,對于涅斯梅洛夫作品的研究視角還有待被進一步挖掘。
我們都知道,每一位作家獨特寫作風格的背后都折射著其生活的時代背景,體現著其個人經歷。所以我們在鉆研作家作品的同時,還要注意觀察個人閱歷的增加和思想的沉淀使作家內心發生的變化。生存在孤獨、寂寞和無奈的環境中經常使涅斯梅洛夫產生悲憫之情。
筆者通過閱讀文本,發現涅斯梅洛夫的多部作品中均體現出對話性,這種對話性體現在作者與主人公之間、主人公與主人公之間,甚至是主人公的獨白之中等。當然,研究對話性不是最終目的,最重要的是揭示對話性的背后所隱含的詩人內心深處的哀傷和同情。巴赫金對話理論注重人文精神的這一內涵使得借助對話理論探究涅斯梅洛夫悲憫情懷這一研究更具合理性。無論是詩歌還是小說,至今還沒有人運用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并結合涅斯梅洛夫的人生經歷來探究他作品中的悲憫情懷。
二.對話中的人文精神
巴赫金對話理論內涵博大精深且影響廣泛,在文學領域更是彰顯出了強大的生命力。
巴赫金批評了以洪堡和福斯勒為代表的將語言研究完全局限于個人心理范圍的“個人主義的主觀主義”學派和以索緒爾為代表的認為語言規則存在于封閉的語言體系的語言符號之內的“抽象的客觀主義”語言學派,他主張從社會學的觀點出發研究語言,強調注重語言中的意識形態意義,而人的意識形態的形成離不開集體的、有組織的社會交往。
“大型對話”和“微型對話”是巴赫金對話理論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又分別對應“復調”和“雙聲”概念。“復調”主要指小說結構上的一種特征,“雙聲”主要指兩種不同指向的對話,強調注重“他者”的思想,其中蘊含的人文精神更是值得我們深入探索。
巴赫金對“復調性”概念的論述是基于其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語言創作藝術的研究提出的,與之相對的則是“獨白性”概念,巴赫金認為獨白性和復調性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作者和主人公的關系上。在獨白型小說中主人公完全受制于作者,主人公單純地將作者意識機械傳輸出來,作者一人主宰小說的藝術世界。而在復調型小說中,主人公擁有自己的主體性,主人公擁有與作者平等的意識和價值。也就是說,這時,影響主人公意識的便不僅僅是作者,主人公周圍的世界和生活同樣會對主人公的意識形態造成一定的影響。
巴赫金同樣認為獨白與對話的區別是相對的,“每個對話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獨白性(因為是一個主體的表述),而每個獨白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一個對話,因為它處于討論或者問題的語境中,要求有聽者,隨后會引起爭論等等”[4]35。
20世紀40至50年代,新批評派將話語分為“詩歌話語”和“小說話語”。巴赫金曾說,“在抒情詩中,作者的形式傾向最為強烈,也就是說他消融在外在聲音形式和內在的繪形繪色的節奏形式之中,因而好似他不存在,好似他同主人公融為一體;或者相反,沒有主人公,只有作者。事實上即使在這里,也有主人公和作者相互對立,而每一話語中都回響著反應之反應”[4]86。詩人生活在一定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空間里,詩人的詩歌創作和詩歌語言必然帶上時代和社會的標志,詩歌話語跟小說話語一樣包含社會因素,蘊含社會文化中的多種聲音,巴赫金所言的雜音和多音現實不可能只環繞并哺育小說家,而不影響詩人,它們也不可能只滲透進小說話語,而不進入詩歌話語,詩歌話語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識性和社會性[5]176—181。因此,同小說話語一樣,詩歌話語也具備話語對話性的本質特征。
在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話語進行分析時,巴赫金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通過“我”與“他者”意識的對立來來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這種不同意識的對立通過兩方面表現出來,一是不同價值主體之間的對話,二是同一價值主體內心的對話。而同一價值主體內心的對話則又分為兩點,第一點是主人公內心不同聲音的爭斗,第二點是借助“他者”的意識形態同自己內心的價值取向構成對立,以此構建對話。巴赫金的雙聲語對話便指的是這種具有不同指向性的對話。巴赫金在論述抒情詩中作者與主人公的關系時曾表示,“……像這樣把一些抒情短詩匯集成一個大的整體,僅有統一的主題是不夠的,首先必須有統一的主人公及其統一的意向;有的時候,甚至還可以談談抒情主人公的性格如何”[4]92-93。筆者在研究涅斯梅洛夫的詩歌作品時發現,孤獨落寞的詩人所創作的詩歌話語中充滿了自己內心的對話,這種內心的對話或以彰顯內心的矛盾,或以把他人意識作為內心對立的話語進行對話的形式表現出來,且這種對話都有一個核心思想,那就是抒發詩人內心的悲傷、苦悶甚至是自憐。
三.悲憫情懷的藝術體現
筆者將以涅斯梅洛夫具有代表性的詩《致后代》和《摒棄》為研究示例,揭示詩歌話語中的對話性,并運用巴赫金對話理論進一步闡釋詩人內心深處的悲憫情懷。
《致后代》(節選)有時我想起這樣的情景:往后再過一百個年頭,打開那本長篇大論的《我們在中國的僑居》之后,遙遠未來的青年定將要把悲慘流放犯的命運思考。//兩種目光頓時相接,……后代將深表同情地說://“……為什么你們這樣倔強,為什么你們不返回故鄉?”……“你成長,沒有監獄,沒有墻,墻磚被子彈摳出許多紋,在我們時代沒有投降過,因為當年不納降敵人!”……我們彼此都互不理解,冷冷地抬起眼皮相望……[6]33!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詩人內心的痛苦與掙扎。代表“想返回故鄉卻不能返回”和“不被后代理解”兩種不同意識的聲音展開對話,這兩種意識由“我”這一主體分化出來,詩中有兩種力量在相互影響著。由于兩種復雜的感情存在于獨白中,可以認為是主體自身意識的分化造成的,主體和分化出去的“我”展開對話,獨白中滲透進了對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筆記里,巴赫金也曾表示,在深刻的獨白性的言語作品之間,也總存在著對話關系。即使兩個表述出現的時間不同,空間上也有較遠的距離,但只要它們在涵義上顯現出一定的關聯性,這兩個表述也是有可能存在著對話關系的。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致后代》中的詩歌話語已經獲得了巴赫金所言的“對話性”。在這首詩中,詩人在自己內心建構了一個跨越時空的對話場景,在這場對話中詩人預想到若干年后自己不返回故鄉的決定將不會被后代理解,兩代人只能“冷冷地抬起眼皮相望”,筆者透過這場對話看到的更多的是詩人的哀傷和自憐,傷心自己不被理解,憐憫自己想回故鄉卻又無法如愿(詩人當初聽信了紅軍要將白軍統統槍斃的傳言)。
雙聲是對話性的表現形式之一,而且對話性也可以通過人物的手勢和面部表情展現出來。涅斯梅洛夫的《摒棄》(節選)便是一個極好的示例:生活在黑暗貧民窟的我被賦予愛心和憐憫心,用它們來對付溫順的麻雀,也對待外來貓,它可是咬人。//那只麻雀在水罐里淹死,那只貓活了一陣也死了。貓在自己臨死之前,用責備的目光望了望我。//我哭了,并且痛苦地想:啊,流浪漢,平庸的寫詩者,你都沒有保護好麻雀,沒有給貓盡可能的幫助。//自私自利者,有害的馬大哈,你為什么活著——不清楚。對于自己的親人和朋友,你已是不堪承受的重負……[6]75。
巴赫金認為,“在言語的交流中,話語是具體的,是一種具有指向性的個人言語行為,即表述”[4]33。表述可以是口頭的,也可以是書面的。表述的范圍,小至一個詞語,大至一部著作,但并不是任何詞語、句子都能成為表述,表述具有一系列的特征。其中,表述的完成性并不等同于詞語、句子的完整性,兩者的本質區別在于,表述具有引起回答的能力,而語言學中的詞語、句子基本都是中性狀態的,它們與他人的表述沒有關系。筆者認為涅斯梅洛夫《摒棄》中的“責備的目光”這一詞語帶有明顯的意識指向性,并且也具備引起回答的能力,也就是說,“責備的目光”已經引發了相應的答語,很顯然,回應的話語就是緊隨其后的詩人痛苦的心理活動。不難發現,詩人的心理活動又充滿了矛盾與掙扎,“對于自己的親人和朋友,你已是不堪承受的重負”,在這句對話式的內心獨白里同時有兩種聲音,也就是詩人自己的聲音及其親人和朋友的聲音:于現實生活而言,詩人已是親朋好友的負擔;詩人因自己現如今仍茍活在世的現實而深深自責,甚至是諷刺自己為保全性命不得不離開自己深愛的故土。一個話語里隱含著兩種聲音,這便是雙聲語了。在這首詩中,詩人在表述自己矛盾的內心時并沒有用第一人稱“我”,而是運用可以與之進行平等對話的第二人稱“你”,人稱的變換使詩人內心的痛苦與掙扎極具表現力,并且詩人借助自身分裂出來的“他者”形象來責備自己對麻雀和貓的憐憫與照顧不周。不管是親朋好友還是弱小動物,詩人總是對其充滿了深深的憐愛之情,由此便可感悟到詩人內心深處的悲憫情懷。
參考文獻
[1]趙一凡.西方文論關鍵詞[M].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7年,第154頁.
[2]李延齡.中國,我愛你[M].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09頁.
[3]顧蘊璞.涅斯梅洛夫和他的詩[J].俄羅斯文藝,2002(06):16-19.
[4]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86、92、93頁.
[5]汪小英.詩歌話語對話性:巴赫金對話理論的一個重要維度[J].求索,2017(01):176-181.
[6]李延齡.哈爾濱,我的搖籃[M].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33、75頁.
(作者介紹:苑靜雯,大連海事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語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