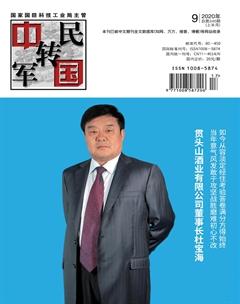白衣天使的核軍工歲月(上)
何廣華 何明圓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我國在四川廣元搶建了一座生產(chǎn)軍用核材料的大型軍工企業(yè)——821廠,并為之配套建設(shè)了821職工醫(yī)院,聚集了300多名來自北京、上海、南京、武漢、天津、鄭州、蘇州等大醫(yī)院的醫(yī)療精英,形成了一個技術(shù)精湛的醫(yī)療團隊。
五十年來,這些白衣天使們堅守強核強國的夢想,用青春和熱血踐行希波克拉底宣言,為我國核工業(yè)做出了重要貢獻,成為廣元地區(qū)醫(yī)療水平最高,核工業(yè)系統(tǒng)西南片區(qū)實力最強,設(shè)備最好的醫(yī)院之一。
今天,當(dāng)我們穿越時光隧道,在那記憶的最深處,在那塵封的檔案里,在那光輝的史冊上,在那親切的回憶中,觸摸到白衣天使們那些艱苦奮斗、披肝瀝膽、無私奉獻的歷程,仍然能夠感受到一段歷史脈搏的跳動,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沖擊和震撼……
大山的呼喚
1969年11月5日,周恩來總理簽發(fā)國務(wù)院、中央軍委密件,決定我國核工業(yè)重要生產(chǎn)基地404廠2465名員工從戈壁灘遷到四川,其中1735人遷到821廠,廠址在廣元三堆鎮(zhèn)。
“各路大軍齊參戰(zhàn),白龍江畔旌旗卷,機器轟鳴震天響,千軍萬馬戰(zhàn)猶酣。”中國人民解放軍工程兵8865部隊、409部隊10中隊、 7797部隊警衛(wèi)營來了;二機部所屬土建、建筑安裝公司和四川省交通廳、郵電管理局、成都鐵路局的施工隊伍來了;西南通信工程局、西南電力工程局、武漢航運工程局、交通部武漢第二航務(wù)工程局的隊伍來了;笫二設(shè)計研究院的科技隊伍來了;經(jīng)過嚴格挑選的10多所大專院校的近千名大學(xué)生來了;戰(zhàn)斗在羅布泊核試驗基地的800名工兵戰(zhàn)士脫去戎裝來了;全國各地的建設(shè)者懷著青春夢想來了。
幾乎是一夜之間,廣元三堆鎮(zhèn)周圍大大小小的山頭上全都是人。十里峽谷,紅旗招展,熱火朝天。施工高峰期,現(xiàn)場3萬多人,每分鐘有近62輛車進出峽谷。各式施工機械轟鳴,各種車輛車水馬龍,大喇叭放著雄壯高亢的革命歌曲,開山放炮聲此起彼伏,震耳欲聾。
從1969年10月開始,昭化火車站每日進貨幾十個車皮,有時高達120個,現(xiàn)場運輸汽車達307臺。
“叮鈴鈴!叮鈴鈴!”急促的電話鈴聲一陣緊似一陣,工程指揮部不斷接到人員傷亡的報告……
先是22公司一輛滿載水泥、油毛氈的卡車翻了,負責(zé)裝卸的8個民工姑娘,一個當(dāng)場死亡,另一個身負重傷,其他傷勢不一;
接著,在搶修寶輪至三堆的道路時,工地現(xiàn)場放炮,石頭飛出去,把一個帳篷里面搞地質(zhì)勘探的同志砸得血肉模糊;
緊接著,3分廠徒工連3個職工拉著板車運菜過江,由于太重把吊橋壓跨,3人全部跌入江中,當(dāng)即造成一死兩傷;
還有更嚴重的,在搶建寶輪至三堆道路的工地上,工程兵某部7名戰(zhàn)士不幸光榮犧牲;
某施工單位的卡車,因避讓不及與迎面駛來的大貨車相撞,翻入白龍江中,15名職工當(dāng)場死亡……
1969年6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機械工業(yè)部軍事管制委員會發(fā)出了二軍字362號秘密文件:請415醫(yī)院為821工程配備200張床位的醫(yī)院。這份文件明顯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主要有3點:
(1)821醫(yī)院黨政醫(yī)務(wù)干部及其他人員,必須是經(jīng)過文化大革命考驗,忠于毛主席,突出無產(chǎn)階級政治,經(jīng)過清理階級隊位,未發(fā)現(xiàn)政治重大歷史問題;
(2)職工醫(yī)院所需各種醫(yī)療設(shè)備,醫(yī)療器械由415醫(yī)院抽調(diào)配備;(3)進入職工醫(yī)院的所有人員家屬子女暫不進入現(xiàn)場,仍留原地。
文件最后要求:希望你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活學(xué)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無產(chǎn)階級政治,搞好思想革命化,發(fā)揚艱苦奮斗,勤儉創(chuàng)業(yè)的革命精神,盡快地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衛(wèi)業(yè)醫(yī)療隊伍。
在“好人好馬上三線”的時代號召下,湖南衡陽415醫(yī)院97名醫(yī)護人員奔赴廣元;甘肅404醫(yī)院的30多名醫(yī)護人員奔赴廣元;成都、北京、福州、武漢、鄭州等地的10多名醫(yī)護人員奔赴廣元,用一生去踐行希波克拉底誓言。從此,創(chuàng)業(yè)與奉獻、光榮與夢想,猶如鏗鏘的詩行,吟誦在川北大地上……
大學(xué)生夫妻入川
張玉琴時任821醫(yī)院婦產(chǎn)科主任,江蘇張家港人,1964年畢業(yè)于蘇州醫(yī)學(xué)院,當(dāng)時,二機部來院挑了100多名學(xué)生支援三線建設(shè),張玉琴也被選中,分到404職工醫(yī)院。在那里,她認識了哈工大畢業(yè)的陳希平,后任821廠副總工程師,1967年初兩人在大漠深處結(jié)為夫妻,年底生了個男孩,取名陳濤。
1969年3月,珍寶島沖突爆發(fā),蘇聯(lián)欲對中國實施核打擊,404的選址、性質(zhì)甚至生產(chǎn)規(guī)模蘇聯(lián)都了如指掌。
戰(zhàn)爭的陰云蘢罩在戈壁灘上空。當(dāng)時,廠里組織職工在廠區(qū),生活區(qū)周邊挖戰(zhàn)壕、筑掩體,每周一期軍事培訓(xùn),識別蘇聯(lián)飛機型號、特征、以及蘇聯(lián)飛機從起飛到抵達404上空的時間。
這年冬天,戈壁灘上寒風(fēng)凜冽,狂風(fēng)裹挾著沙石,打在臉上生生的痛。11月13日,廠里傳達了林彪的‘一號通令,宣布了人員分流名單,并要求17日搭乘軍列離廠,全部東西自帶,準(zhǔn)備時間只給了三天,倉促可想而知。
17日下午四點,開往廣元的軍列在專用線上準(zhǔn)備出發(fā),送行的同志擠滿了站臺。那種生離死別的情形非常感人,至今歷歷在目。
南下的軍列夜行晝息,第三天早晨6點鐘,軍列抵達廣元火車站。數(shù)千名職工和家屬分散安置在廣元周邊52個公社。陳希平則被分到了虎跳。
虎跳是一個美麗安靜的小鎮(zhèn),四周有大山環(huán)繞,有嘉陵江流過。陳希平被安排在虎跳中學(xué)禮堂,用稻草鋪墊睡地鋪,每天上下午各2個小時學(xué)習(xí)毛主席著作,知道轉(zhuǎn)移到廣元是為搶建821。
1970年2月,張玉琴攜2歲兒子入川,來到虎跳與丈夫團聚,由于丈夫經(jīng)常出差,她既要帶孩子,又要到一里外挑水,做飯用的是煤油爐,而煤油則要憑票定量供應(yīng)。
9月,張玉琴一家搬到了三堆范姓農(nóng)民家里,那是靠近白龍江的一處四合院,住著五戶人家,有三戶821廠職工住在這個院里。
四合院是木結(jié)構(gòu)房屋,沒有灶房,他們只能在過道上壘灶做飯,燒木柴。用水需到250米外的白龍江去挑,洗衣服拿到白龍江去洗。
1971年7月的一天,兒子陳濤突然發(fā)燒,體溫達到39.5°C,夫妻倆慌了,馬上送兒子去醫(yī)院。當(dāng)時821醫(yī)院在16公里外的寶輪鎮(zhèn)。
821汽車隊在兩公里外的井田,需經(jīng)過白龍江吊橋才能到達。幸好院里的兩個老鄉(xiāng)幫忙,幫他們抱著孩子一路狂奔趕到了井田。汽車隊立即派了一輛越野吉普,向?qū)気嗎t(yī)院疾駛而去。
醫(yī)院里都是張玉琴的同事,剛把孩子放到病床上,他就抽搐了,眼睛上翻、口吐白沫、渾身抽搐。夫妻倆嚇得不知所措,醫(yī)生及時地給他輸了氧氣,幾分鐘后他緩過來了,喊了一聲媽媽,張玉琴激動地抱住兒子慟哭起來。
兒子檢查結(jié)果為急性細菌性痢疾,對癥治療三天,病情明顯好轉(zhuǎn),張玉琴的心才算落了地。
張玉琴說:“我們注定是奉獻的一代。我當(dāng)年的同學(xué)都在北京、上海、南京、無錫等地,有的做了政府官員,有的成了專家教授,月工資上萬元,而我只有區(qū)區(qū)4000余元。有一年我回蘇州的時候人家都說,你咋不回來 人家都回來了 我說我回來干啥,我走了就不回來了。”
1996年,張玉琴退休后,先后在廣漢人民醫(yī)院,成都滿地可醫(yī)院干了17年,2016年才笫二次退休。
劉玉貞的婚姻
劉玉貞至今仍珍藏著丈夫孟慶福年輕時的照片,照片中的丈夫一身戎裝,英氣逼人,胸前掛了6枚軍功章。她說,這張老照片是丈夫留給自己惟一的念想了。
孟慶福系北京人,解放戰(zhàn)爭時期參軍,歷經(jīng)大小戰(zhàn)斗20多次,曾任連隊指導(dǎo)員,因救火吸入大量濃煙,肺部受到嚴重損傷,切掉了一根勒骨。1959年轉(zhuǎn)業(yè)到415醫(yī)院。1969年任821職工醫(yī)院黨總支書記,后任821廠組織部長。2012年去世,享年83歲。
“我是福建福清市人,13歲就沒了父親。16歲那年,時任福建水利局長的表哥讓我到福州去相親。我跟著干媽,坐了2個多小時車船,去孟慶福一個戰(zhàn)友家見面。
我壯著膽子看了孟慶福一眼,他上身穿了件豆沙色帶拉鏈的便服,下著卡其布褲子,又高又黑,一臉胳腮胡。介紹人說他在部隊當(dāng)官,比我大5歲。
我那時年紀小,還沒有答應(yīng)人家,便稀里糊涂跟他去照了相。分別時,他還送了我一支鋼筆。
回到福清,我有些后悔,我對媽媽說,那個人比我大5歲,又瘦又黑,媽媽說不大不大,你父親比我大11歲哩!
你別說,孟慶福還真會來事,不久便給我媽寄了25塊錢看病。不久,媽媽病故了,我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等我和孟慶福結(jié)了婚,才知道他比我整整大了11歲。
不過話又說回來,老孟為人忠厚老實,對我很好,疼我寵我,呵護我,我們先后生了3個孩子。
1970年6月,我千里迢迢帶著3個孩子到了寶輪821職工醫(yī)院,孟慶福對我說,洗衣房沒人,你去那里干吧。我心想,哪有你這樣當(dāng)領(lǐng)導(dǎo)的,把自己的老婆放在最艱苦的地方,但嘴上又不敢說。
洗衣房只有2個人,要洗全院的工作服,床單,被子及尿布,那上面不但有膿血,還有屎尿。我們用手搓,用腳踩,然后燒開水消毒,還要做被子,工作服,帽子和口罩,每天累得腰酸背痛。
后來,有個院領(lǐng)導(dǎo)看我太辛苦,準(zhǔn)備把我調(diào)到二分廠開電梯,可老頭子不同意,說這兒沒人,我在洗衣房一干就是20年,直到退休。”
悲壯的奉獻
李維音,現(xiàn)年85歲,高級工程師,1953年6月入黨,享受國務(wù)院特殊津貼,核工業(yè)部勞動模范,入選《兩彈一艇人物譜》。這位堅強樂觀的科學(xué)家,寫了一部10多萬字的回憶錄《堅持,挺住,我的人生故事》,感人至深,催人淚下。現(xiàn)摘錄如下:
“1959年7月,我從蘇聯(lián)列寧格勒建筑工程學(xué)院畢業(yè)歸國,8月30日與同院留蘇副博士劉啟陸結(jié)婚,先后生了兩個女兒。啟陸回國后被分配到了二機部。我任核工業(yè)二院堆廢水處理小組長。
1969年5月3日,為了讓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覺,啟陸去了821,在指揮部負責(zé)施工。同年10月,我也攜10歲大女兒劉瑛和7歲小女兒劉珂來到821,任工程設(shè)計員。
劉瑛生性活潑,聰明伶俐,人見人愛。在幼兒園跳扭脖子的新疆舞,跳得有模有樣,幼兒園在大禮堂演出,老師讓她報節(jié)目,她一點也不怯場。進了三堆鎮(zhèn)小學(xué)兩個月后,老師就讓她當(dāng)了班長。
到了821后,孩子們就和啟陸一起生活,早上自己上學(xué),放學(xué)后,自己乘擺渡船過江到指揮部找爸爸,晚上再一起坐小船回家。而我則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住在半山上借用的安裝公司勻出的工棚宿舍里,只有周末和他們團聚,那已經(jīng)是諾大的幸福了。
1971年4月15日晚,啟陸晚上7點下班后,帶著孩子到指揮部的渡口過江,萬萬沒有想到,船剛撐出,就撞上了平板運貨船,船一下子失衡,站在船頭的啟陸和拉著他衣服的大女兒一下子就被甩下了船,消失在了湍急的白龍江中。
慌了神的乘客們紛紛爬上運貨船,站在船艙里的小女兒是被別人拽上去的,她發(fā)現(xiàn)沒有了爸爸和姐姐,開始拼命地狂叫,可是人已被狂流吞沒。后來啟陸被撈出,大女兒則不見了蹤影。
那天,細雨蒙蒙,深夜1點,我在工棚里被人喚醒。我似乎有第六感覺,匆匆跟著來人,奔下濕滑的山路,鉆進了小汽車,一路上沒有一個人開口。我被引進了821職工醫(yī)院的大屋,接著被告知:晚上7點,啟陸在從指揮部乘渡船返回對岸駐地時,小船撞上了運貨船,不幸落水。
我在哭泣中被領(lǐng)到旁邊一間小屋,啟陸就躺在平床上,渾身已經(jīng)冰涼,鼻子下還有一些血跡。我輕輕地撫摸他的身體,呼喊著他的名字。很快,我被扶到一間病房,他們讓我坐在床上,讓護士給我注射葡萄糖液,然后,一位領(lǐng)導(dǎo)開口了:跟他一起走的還有你們的大女兒,至今沒有找到人。
父女慘死,天塌地陷,丈夫才41歲,大女兒還不到11歲,當(dāng)時,我在床上繃跳狂喊:我的孩子啊!我的啟陸啊!我哭了丈夫哭女兒,哭了女兒哭丈夫,我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絕,在場的醫(yī)護人員,領(lǐng)導(dǎo)同事也哭成一片……
10天后,我?guī)е鴨㈥懙墓腔易狭嘶乇本┑幕疖嚕驮诨疖囬_動的一剎那,傳來了大女兒被找到的消息,不久,我收到了她的骨灰盒,卻再也沒能見到她的人。
在二機部為劉啟陸召開的追悼會上,我哽咽地大聲宣誓:一定要把啟陸開創(chuàng)的這項工程中我承擔(dān)的部分圓滿完成,一定要照顧好他留下的女兒。
從那以后,每次去821工程現(xiàn)場,每次望見那滔滔的白龍江水,我都會忍不住嚎啕大哭……
1976年10月,821反應(yīng)堆整體進入安全運行。我完成了我的使命。821反應(yīng)堆正式順利投運的巨大意義在于,我們的原子彈有保障了!
后來,821廠向國家科學(xué)大會申請了集體獎,獎狀掛在廠部辦公樓里,這個集體獎的第一名就是我。
這就是我們那一代人,任務(wù)就是生命,使命就是擔(dān)當(dāng)。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我拼命在心中默念這句話,和我親愛的丈夫和女兒化作一體去奮斗,為了我們的原子能事業(yè)……”
席棚子的記憶
“我今年84歲啦,又叫80后!”剛見面,時任821職工醫(yī)院院長的張寶萍,便用普通話風(fēng)趣地對我說。
張寶萍畢業(yè)于河南醫(yī)學(xué)院,后供職于河南省人民醫(yī)院,1963年與喬恒明(后任821廠長)結(jié)婚,先后生了兩兒一女。1970年3月隨夫支援821工程,任821醫(yī)院婦產(chǎn)科主任。1992年亨受國務(wù)院特殊津貼。
“開始我們住在寶輪榮校禮堂樓上,男女生分住兩邊,打地鋪,吃飯在寶輪中學(xué)食堂,后來自己動手建食堂,搭席棚,才有了臨時的家……
想想那個年代真是難忘,住的是席棚子、燒的是蜂窩煤、睡的是大鐵床,一躺下“嘎吱、嘎吱”直響。所謂“席棚子”,就是用牛毛氈、竹席子、木頭棒子搭建而成,房頂用油毛氈覆蓋以防雨水。類似四川人叫的‘鴨兒棚棚。到處透光,從里面就能望見外面,也不隔音,外面說點什么都能聽見。
當(dāng)年,能擁有這樣一間‘席棚子,那就相當(dāng)滿足了。一家吃回鍋肉,整個院子的人都能聞到香味。哪家吵個架,全院子的人都跑來勸。‘席棚子庇護了創(chuàng)業(yè)者的喜悅和憂傷,也記錄了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席棚子僅4一5平方米,少的住2-3人,多的住5-6人,中間就隔了一張竹席子。因為屋頂僅僅是一層油毛氈,夏天熱得使人窒息,而冬天呢,蓋上兩床被子也不會覺得暖和。當(dāng)時大家思想很單純,對于苦累想得少,覺得能為三線建設(shè)做貢獻,已經(jīng)很光榮了。
那時,喬恒明在廠里搞基建,整天忙得的團團轉(zhuǎn),別人一星期回來一次,他20多天才回來一次。開始,我不會封蜂窩煤爐子,常常被熏得眼淚直流。被譽為“草帽書記”的廠黨委書記楊唯青,手把手教我封火時留的空隙大小,如何封時間長點,而且讓它不滅。
席棚子特別潮濕。我既要上班,還要照顧孩子,每晚都要起好幾回,給孩子換尿墊。床尿濕了,我就把孩子挪到自己這邊,自己睡到尿濕的地方,再尿濕了,就把孩子挪回自己剛暖干的那邊。時間長了,被子被漚出一個大洞。
一天下班回來,我突然發(fā)現(xiàn)孩子不見了,不由心一沉,左看右看也沒有,嚇得我都要給老公打電話說孩子不見了,才發(fā)現(xiàn)孩子卡在鐵床和圍‘墻之間的縫隙里了,幸虧發(fā)現(xiàn)的早,孩子并無大礙。
1970年11月,我在席棚子里生下小兒子,因工作實在太忙,不到1歲就交給遠在河南開封的母親帶,6歲才到四川。
由于感情不深,小兒子跟我形同路人,不喊我,不理我,平時連阿姨都不叫,這讓我很是痛苦,一直到孩子14歲上初中那年,才突然喊了聲媽媽,這一聲媽媽,叫的那么甜蜜,叫的那么暖心。那一刻,是我最幸福的瞬間。
艱苦并不是當(dāng)時記憶的全部。還是有留戀的,懷念那個時候大家在一起,有說有笑的時候。那個年代娛樂活動很少,每個星期放一次露天電影,就成了職工們最期盼、最為之興奮的事。”
張寶萍說:“我入川后,河南人民醫(yī)院的領(lǐng)導(dǎo)一直想讓我回去,并把婦產(chǎn)科主任的位子紿我留著,他經(jīng)常給我寫信,問我啥時回去,我說再等等看,這一等就是幾十年,那位領(lǐng)導(dǎo)去世前,婦產(chǎn)科主任的位子都是空著的,我卻始終沒有回去。這里有我的青春、我的事業(yè),更有我的夢想,廣元已成為我的笫二個故鄉(xiāng),靈魂深處永遠的家園。”
劉靜梅的眼淚
劉靜梅曾是821醫(yī)院藥劑師,她回憶道:
“我父親叫劉同榮,祖籍山東臨沂,解放后在東北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后轉(zhuǎn)入404,與同鄉(xiāng)姑娘結(jié)婚,先后生了7個孩子。不幸的是,我11歲那年,母親在生孩子時大出血死了,從此,父親終生沒有再娶。
1969年11月,父親帶著我和弟弟妹妹坐火車赴川,3個哥哥則留在了404廠。記得火車在寶雞停了一天,父親帶我到街上去逛,他買了一捆山東大蔥,3斤寶雞咸菜,我看見有人賣梭角,2角錢一斤,我平時特喜歡吃,便纏著父親買,并撒嬌說,你不買我就不走了,父親拗不過我,只好給我稱了2斤。
我們一家在下寺公社一個楊姓農(nóng)民的家安頓下來,住在了老鄉(xiāng)敬奉先人堂屋里,老鼠大白天都跑來跑去,吱吱叫著。晚上我們害怕,關(guān)上門還不放心,又頂了幾根杠子。
因父親每天要到數(shù)十里外的三堆上班,星期六才能回家,16歲的我就承擔(dān)起家庭主婦的角色。開始,弟妹們吃不慣大米,一到吃飯就哭,我就把米飯炒一下,再給他們兩毛錢,在學(xué)校買碗菜湯。后來,父親就拿米換老鄉(xiāng)的面。
回想當(dāng)初的困難,我自己都想掉眼淚。每天,我要到清水河邊去撿柴,到1里外的半山腰挑水,還要洗衣煮飯,房東看我們怪可憐的,平時做點好吃的如扣肉,炒紅苕藤等,就給我們端一些。我呢,有時便帶著弟妹幫房東打場,老楊就讓老伴給我們做些好吃的。
由于水土不服,很多人都得了黃水瘡,我也末能幸免,滿臉都是,奇癢無比,根本睡不著覺,我只好用圍巾掩面去看醫(yī)生,醫(yī)生看后大吃一驚,唉呀!怎么成了這樣呢 臉上留下疤痕就不好看了。他用紫藥水給我擦后,又給我開了盒金霉素軟膏,叮囑我按時涂抹,千萬不能抓撓,以免復(fù)發(fā)。一個星期后,黃水瘡治愈了,萬幸的是,我的臉上沒有留下疤痕。
記得這年立冬后,有一天下大雨,清水河漲水,漫過了漫水橋,廠里接送職工的大卡車過不了河,40多個工人穿著雨衣,又冷又餓,眼巴巴地望著河對岸,盡管幾公里外就是他們的住地,就是他們的親人,但他們卻過不去。只有站在河邊癡癡地等,等啊等,從晚上7點一直等到次日凌晨3點,也許是他們的堅持感動了老天,也許是他們的執(zhí)著打動了河神,雨終于停了,河水逐漸退去,漫水橋露出來了。
怦怦怦!半夜4點過,急促的敲門聲把我嚇壞了,我壯著膽子問誰呀 父親說靜梅快開門,是爸爸!聽到父親熟悉的聲音,我趕緊點燃煤油燈,拿開扛子,推開堂屋門,只見渾身濕透的父親站在門外,凍得瑟瑟發(fā)抖,我的眼淚一下就流出來了。我立即點燃柴禾讓父親烤火,又燒了些水,讓他洗了把熱水臉,換上干衣服,并煮了一碗面給他吃,忙完這一切,房東家的公雞已開始打鳴了。
10個月后,我們一家搬到了三堆,我還專門買了點心,回下寺看望了老房東一家。如今幾十年過去了,不知老房東是否安好 ”
(注:笫一作者為廣元市報告文學(xué)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