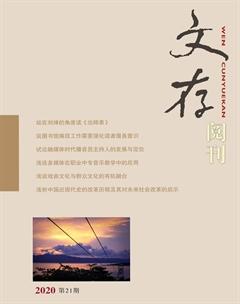鄉土文學的文學史展望
劉文
摘要: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小說家們將筆觸對準都市空間中的眾生相,在大眾文化大行其道的文化語境下,“娛樂至死”的聲音不絕于耳。當生存空間被重重擠壓,鄉土文學該何去何從?
關鍵詞:鄉土文學;困境;重建
一、鄉土文學的概念
鄉土文學的創作可以溯源至魯迅,在他故鄉式寫作的引領下,上世紀20年代鄉土小說作家群成為了他的忠實追隨者與效仿者。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將鄉土文學界定為:“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但這又非如勃蘭兌斯所說的‘僑民文學,僑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卻不是這作者所寫的文章,因此也只見隱現著鄉愁,很難有異域情調來開拓讀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而1936年茅盾《關于鄉土文學》中則表明鄉土文學除了特殊的風土人情外,更應深入到命運掙扎的內涵層面。
隨著文化語境的變遷與城市化的發展,本論文將鄉土文學界定為:自魯迅的故鄉式創作以來,展現鄉土中國的常與變,帶著對故鄉獨有的情感傾向,展現鄉土中國的民俗民風、地域風情、人情人性,滲透著作者人文關懷與尋根意識的作品。
二、鄉土文學發展的百年脈絡梳理
魯迅的作品“把平凡而真實的農民,連同他們襤褸的衣著,悲哀的面容和痛苦的靈魂一道請入高貴的文學殿堂”,其鄉土文學寫作的要義也在于此:關心普通真實、卑微甚至卑賤的中國農民,他們的悲歡離合,他們的精神麻木與人生困境。
上世紀20年代深受魯迅影響的鄉土小說作家群,如王魯彥、彭家煌、許杰、臺靜農、蹇先艾等人,也繼承了魯迅的故鄉模式,有如朝霧一般揮散不去的鄉愁,也有古舊中國村民們的精神愚昧。這些作家的作品中展現出一個幽暗的鄉土世界,裹挾著不斷上演的種種丑陋民俗而來,如水葬、典妻、械斗、沖喜、冥婚等。
上世紀20年代的廢名,卻在走田園牧歌的路子,20世紀30年代的沈從文延續了廢名的文風,把一個帶著夢幻感、超離感的湘西世界展現得淋漓盡致。同期,茅盾的鄉土創作則加入了更多的階級斗爭的內容。自此,對于鄉土中國的描繪有了兩大傳統:田園牧歌傳統與階級斗爭傳統。
無論是20世紀40年代趙樹理作品中的農村本相,還是周立波《暴風驟雨》或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階級對立與土改運動,都為之后三十年的農村題材小說做足了榜樣。當《紅旗譜》《山鄉巨變》《創業史》等紅色經典退去了他們的時代光環,拋卻其中宏大的政治主題與驚心動魄的階級對立、現實斗爭,其中的地域風情、民風民俗、民族心理、情感蘊藉卻超越時空,獲得了永恒的魅力。
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新鄉土敘事,因為有了賈平凹、莫言、閻連科、劉震云這一眾作家扛起鄉土寫作的大旗,鄉土文學的發展并未止步。他們的作品是對中國鄉村歷史多重性的發現,包括鄉村的精神危機、鄉村的生存困境、鄉村的凋敝破敗、鄉村的瑣碎日常,滲透著作家深層的責任意識與人文關懷。
在這百年的鄉土文學歷程中,這些作品給我們書寫著鄉土中國的“常”:農耕、農忙、農閑的景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蟬鳴松落和雞鳴狗吠,無不帶著田園牧歌、詩情畫意的情調;也有婆媳妯娌、三姑六婆、封建迷信、男尊女卑的鄉間人倫;或有祭祖祭祀、歲時節氣,喪葬嫁娶等各具地域特色的民風民俗;亦帶著游子的鄉愁綿綿不絕。
這些作品也在書寫著鄉土中國的“變”:社會結構的變化,宗法人倫制度的淡化,農村的破敗與蕭瑟,傳統民間文化的失落等現象也將一個殘酷的生存空間展現出來。
三、鄉土文學的困境
現代化、城市化成為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農村的空間在不斷縮小,賈平凹“村子里連抬棺材的人都沒有了”這種喟嘆也不是偶然。今天很多的作家,很多的讀者大多生活在城市空間,時有漂泊與無可歸依之感。如格非《人面桃花》中的花家舍一樣,故土承載著少年的夢想與愛戀,是永遠回不去的精神故鄉,是永遠無法割舍的靈魂歸處。而今后的作家,更多的生存空間不再是鄉村,他們對鄉土中國的記憶可能是一片空白。故鄉作為作家的精神烏托邦,作為作家創作的根據地,與鄉村有關的文學經驗隨著時代浪潮將會成為歷史。
在大眾文化的浪潮中,網絡成為了文學創作與消費的主陣地,都市題材、科幻題材、青春愛情題材等作品層出不窮,快餐式閱讀、碎片化閱讀成為時尚,加之精英文學的失落,讀者審美趣味的變化,鄉土文學的生存空間的確在不斷被擠壓。
四、重建文學與鄉土的血肉聯系
那么,創作者們該如何駐守好這一方精神根據地,將鄉土中國的山水風情、歷史風云,將個體的人生經驗、情感體悟,都內化于一部作品之中,從而激發鄉土文學的活力與生機?
首先,創作者們重走故鄉路,重新審視故鄉。可以是實際行動上的故地重游,去看看童年家門口的那棵樹,那片池塘,那座山;去聽聽鄉音;去嘗嘗故鄉的野菜;再體驗體驗故鄉的風俗儀式;再感受感受故鄉的人情冷暖。抑或是做一次精神還鄉。
其次,將鄉土文學的創作與閱讀放在全球化的語境中。今天的鄉土文學創作不應局限于對于故鄉、故土的摹寫;也不應只把眼光放在故鄉的一草一木,一屋一瓦上。更應該穿越歷史與現實,帶著地域特色與情感蘊藉,重新挖掘與表現鄉土,著眼鄉土的精神家園屬性,著眼鄉民的生存圖景,著眼創作者自身的崗位意識與人文情懷。
最后,時下文化市場的讀者,面對魚龍混雜的文化市場應保持自己的理智和清醒,不斷提升自我的審美趣味與文學素養。在生活中無處安放自我的情感,無處寄身自我的靈魂時,可以在鄉土文學經典作品中進行一次精神還鄉之旅;在城市中對公共空間煩躁、失望時,可以去鄉土文學作品中感受作家的個體經驗,感受一個或幽暗殘酷或溫情脈脈的鄉間,觸摸一顆帶著自己的深情與真誠書寫著鄉土的靈魂。
參考文獻:
[1]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M].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9.
[2]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M].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171.
[3]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