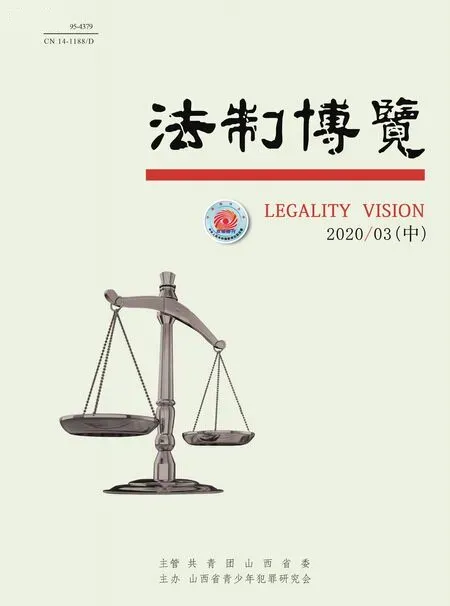新時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探析
張怡婷 耿祎輝
河南博同律師事務所,河南 洛陽 471000
2019 年10 月31 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我們要“建構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自2013 年浙江省桐鄉市率先探索實施現代意義“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實踐以來,2017 黨的十九大將“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鄉村社會治理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而我們有必要對作為現代鄉村社會治理主要方式和手段的自治、法治、德治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和相互關系展開一定的分析,從而為有效應對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中的問題和挑戰提供一些思路。
一、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的提出及內涵
首先,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的提出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治理理念的體現。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理念是新時代黨和國家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理念的具體實踐形式之一,體現了國家對基層社會從管理到治理,從治民到民治的理念的轉變。鄉村社會治理的三治融合的治理理念是在實踐經驗總結的基礎上產生的,其尊重地域差異和民眾訴求,尊重民眾的首創性,充分的體現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從其目標上看,三治融合的治理理念的最終目標在于有效化解基層社會的矛盾糾紛,滿足民眾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提升農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其次,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的提出是自下而上的鄉村民眾治理實踐經驗總結和自上而下的國家頂層設計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的探索是鄉村民眾積極的開展自我改革、自我超越、大力發展合作治理、共同治理,努力探索自主治理機制的結果。2013 年桐鄉市為了解決在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拆遷以及社會發展矛盾突出的問題,從而試點在原有的法治基礎上提出三治合一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此后桐鄉市三治合一的鄉村社會治理模式經過提煉和推廣,成為當前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實踐經驗。另一方面,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斷的深化和充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內涵的論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更是通過了《決定》,為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科學的指南和基本遵循。
最后,自治、法治和德治治理理念的提出是對中國傳統社會治理文化和經驗的傳承及反思。其一,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基層自治的傳統。中國古代自郡縣制以來,政權往往只設在縣級,因而農村基層社會長期存在著“鄉紳自治”的治理格局。以熟人社會、宗族自治為核心的傳統鄉村自治方式雖然和現代流動性社會和半熟人社會之間的社會自治需求存在一定的差異,但現代鄉村社會自治仍然需要充分發揮新鄉賢等在鄉村自治中的積極作用。其二,我國古代的雖然也有依法而治的說法,但其主要是為了保障皇帝的專制權力的,其和現代意義的法治含義完全不同。我們現代的法治建設正是在反思傳統的法律工具主義思維的基礎上而展開的。其三,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德治的社會,十分重視道德教化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現代鄉村社會治理中的德治也傳承了我們的德治基因,積極發揮倫理道德在形成鄉村社會治理秩序和規范個人行為方面的作用。
二、自治、法治、德治之間的關系及其實現方式
關于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在鄉村社會治理中的關系,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論述。通過對學者們論述的分析,本文認為,我們應當以自治為基礎,以法治為保障,以德治為支撐。
以自治為基礎就是在鄉村社會治理中,無論是德治還是法治都需要以村民自治的方式來具體的落實,同時德治和法治也是圍繞如何更好地實現自治來展開的。要落實鄉村自治首先要明確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界限,明確村民可以自治的領域,從而改變原有的村委會職責不明確使得由于權責嚴重不一致而產生的村委會不堪重負的情形。我們可以通過村民會議等方式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逐條梳理明確村委會的治理職責,從而提升其治理的正當性和權威性。其次,對于村委會這一村民自治的重要組織而言,常常會出現民眾過多地關注民主選舉,而對于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實現卻缺乏有效的方式。因而我們應當轉變這一局面,積極努力的推進基層群眾深入全面的參與基層社治理的實踐,同時提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提高等的水平。
鄉村社會治理中還應當積極發揮法治的保障作用,無論是自治、還是德治都應當在法律的框架內展開。要發揮法治在鄉村社會治理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做起:首先,應當完善涉農領域的立法和行政執法工作。完善的立法是實現法治保障功能的前提,我們應當立足新時代農村發展的新需求,對于那些涉及保護農民權益、農業生產問題、農村社會矛盾問題等領域加強相關立法工作。此外,我們還應當積極改革基層執法工作,強化執法隊伍、合理配置執法力量和執法資源、規范基層執法行為、加強對基層執法人員的監督等,從而提升基層執法人員的法治素養和文明執法水平。其次,還應當強化鄉村司法工作,發揮其保障作用。強化司法便民工作,減少民眾的訴訟負累。積極推進法院、檢察院等依法展開對破壞農村生態環境、農村黑惡勢力、侵占農用耕地以及農村集體財產等行為的打擊力度,妥善處理涉農糾紛,防止矛盾擴大化。最后,應當加強鄉村公共法律服務機制建設,強化鄉村法治宣傳工作。完善鄉村法律服務熱線、法律服務站等的建設,打造一站式的服務窗口,為農村基層組織和個人提供優質便捷的法律服務。
鄉村現代化治理體系的建設也離不開德治的支撐。我國傳統社會十分重視道德在維持社會秩序,解決社會糾紛中的引領、規范、引導作用,在廣大農村大力推廣道德教化、禮治秩序,從而追求社會的“無訟”。新時代,我們仍然要強調道德在鄉村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一方面,我們應當傳承傳統鄉村的優秀文化,大力弘揚鄉村美德和優良家風。通過完善村規民約的制定,從而有效地針對婚喪嫁娶的鋪張浪費、不注意維護村容村貌、不積極主動承擔養老責任等不道德行為予以制約。另一方面,可以通過設立鄉賢參事會等,吸納本地區具有榜樣性的新鄉賢參與基層社會治理,充分發揮其在鄉村社會中的決策咨詢、弘揚優秀傳統道德,促進和諧鄉村鄰里關系中的引領和示范作用。
三、結語
實踐經驗表明,自治、法治、德治作為鄉村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采取任何單一的方式都無法有效實現鄉村社會的良好治理,三治融合的治理方式的質量和水平要高于單一治理或兩兩組合的治理方式。同時三者的結合并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和方式,需要和基層實踐需求相結合,否則只追求單一的善治模式可能會造成水土不服的情形,從而無法有效發揮出三治融合的優勢。這就需要在黨的領導下,各地基于自身的實際需求積極地展開探索,從而因地制宜,選擇不同的治理組合強度,如在更加需要德治的地區著重強化道德宣傳,在更需要法治的地區深入完善法治保障等。我們沒有必要追求最佳的善治,而是應當努力建構最符合本地需求的最適宜的三治融合的治理方式,從而能夠有效地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推進鄉村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轉型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