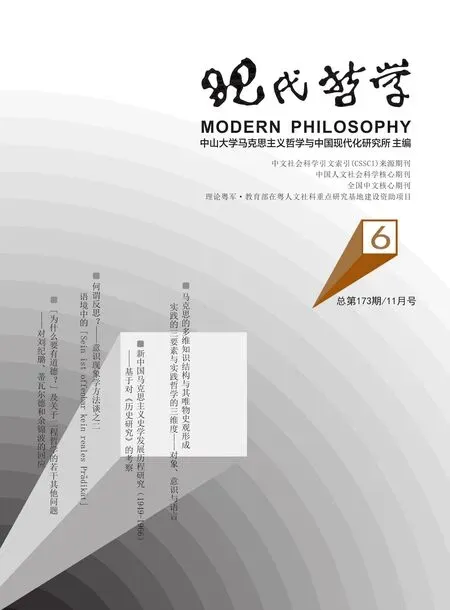“社會-歷史”空間的辯證闡釋與政治旨趣
解麗霞 邱 婕
西方社會思潮的空間轉向,引起“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是否存在空間缺場?”(1)后現代主義者斥責歷史唯物主義是“進化論的某種翻版”“去空間化的歷史決定論”,試圖宣告時間性敘事方式的終結。面對這一發難,需“回到馬克思”并重申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理論。(參見[美]蘇賈:《后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王文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的論爭。實際上,歷史唯物主義打破了形而上學的空間思考框架,將空間闡釋轉向社會領域。面對空間占有的區隔、空間矛盾的激化,馬克思恩格斯審視空間的目光不再是“玫瑰色的”,而是試圖跨越斷裂的“卡夫丁峽谷”,建構以實踐為核心的社會空間,關注資本主義批判的歷史空間,呼喚以解放為旨趣的空間革命。重申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維度、空間旨向、空間價值,既是回應西方學界關于歷史唯物主義弱化空間的責難的理論需要,也是當今全球化、城市化空間變遷中保衛空間正義的實踐需要。
一、社會空間:以實踐為核心的空間重構
社會空間是人類寄寓的處所、實踐活動的場域。此前哲學家們理解空間的分歧在于“絕對概念和相對概念之間的一種對立”(2)[英]哈維:《地理學中的解釋》,高泳源、劉立華、蔡運龍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53頁。。持“絕對空間觀”的一派,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牛頓為代表,以“容器”為喻,將空間規定為容納萬物的承載體,是獨立的、絕對的實在。持“相對空間觀”的一派,以萊布尼茨、洛克、休謨為代表,以“場”取代“物”,將空間視為事物關系的場所,是依賴于主體經驗、相對的存在。絕對化、抽象化的空間認知模式懸置了人、人的實踐。歷史唯物主義消彌了絕對空間與相對空間的對峙,將空間闡釋從本質世界拉回現象世界、從自在自然空間轉向人化自然空間,以人的存在為源始性奠基,開啟以實踐論為基礎的社會空間研究,實現空間闡釋的理論推進。
(一)自在自然空間:超越絕對空間和相對空間
自古希臘以降,空間闡釋理路無不以物理學、幾何學為基石,探究空間是不變的還是變化的、無限的還是有限的、虛空的還是充實的,形成“絕對空間觀”和“相對空間觀”。這兩種空間觀的對立割裂了物質空間和抽象空間,也是機械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分歧所在。對此,歷史唯物主義以空間的客觀實在性證偽抽象化的“相對空間觀”、以空間與運動的內在關聯性批判機械化的“絕對空間觀”,揚棄了以先驗抽象或經驗直觀去理解空間的哲思方式。
空間是絕對性和相對性的統一。首先,歷史唯物主義以空間的絕對性,即空間是客觀實在的,來批判“相對空間觀”。“相對空間觀”把空間觀念化為感覺經驗的集合。如洛克所言,“人心能以做出無數花樣的形相來,因而重疊了簡單的空間情狀”(3)[英]洛克:《人類理解論》,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135頁。,這顯然是將空間置于感性經驗領域的主觀化闡釋,囿于經驗感知,企圖“嗅到空間”。恩格斯認為,空間“離開了物質當然都是無,都是僅僅存在于我們頭腦之中的空洞的觀念、抽象”(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頁。。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空間是客觀實在的,空無一物的虛空不存在,駁斥將空間理解為印象摹本的知覺觀念,避免“相對空間觀”滑向主觀唯心主義深淵。
其次,歷史唯物主義以空間的相對性,即空間與運動不可分離,批判“絕對空間觀”。“絕對空間觀”把空間抽象為獨立于物質運動的參照系統、靜止框架。牛頓定義:“絕對的空間,它自己的本性與任何外在的東西無關,總保持相似且不動。”(5)[英]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趙振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7頁。恩格斯批駁牛頓式的自然科學“不是從運動的狀態,而是從靜止的狀態去考察;不是把它們看做本質上變化的東西,而是看做固定不變的東西;不是從活的狀態,而是從死的狀態去考察”(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4頁。自然界,這種自然科學的考察方式被移植到哲學,導致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以費爾巴哈為代表的機械唯物主義從客體出發,把空間理解為與人完全無關的純粹自在之物,處于靜止的、不變的、死的狀態。實際上,空間是相對的、變化的、具體的。運動在空間中發生,空間形式也依賴不同狀態的物質運動,空間在運動、變化、活的狀態中得到現實性。
歷史唯物主義從空間的自然屬性出發,指出空間作為物質的存在形式不取決于主體知覺,同時客觀存在的空間絕非等同于靜止不變的固定容器。空間絕對性和相對性的統一,表明物質存在的絕對形式與運動的相對狀態共屬一體。歷史唯物主義進一步追溯這種統一是如何實現、超越以往物理主義式的空間理念又是何以可能,根源是人類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對空間的建構。
(二)人化自然空間:自然空間轉向社會空間
時間、空間是兩種最基本的存在形式,人“在空間之中存在”(7)借用海德格爾提出的存在論意義上此在的基本建構:“在世界之中存在。”從此在的空間性討論空間問題,通過具有去遠和定向性質的尋視操勞活動,賦予上手事物以位置和場所,由此勾畫出世內空間。不言自明。人存在的生命活動是自由的、有意識的,符合人的“類特性”地改造自身存在空間,使空間除了自在的物性之外還具有“屬人性”(8)張康之:《基于人的活動的三重空間——馬克思人學理論中的自然空間、社會空間和歷史空間》,《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馬克思區分“自在自然”(空間)和“人化自然”(空間),人化自然空間是對自在自然空間的積極否定,是人“類本質”的主體力量和自在的自然客體相耦合而生成的有機整體。
人化自然空間生成的邏輯前提是人的“類本質”。人在空間之中存在的行動不同于動物的本能行為,雖然動物也為生存筑造洞穴,甚至蜜蜂建造的蜂巢之精細讓人類建筑師都自愧不如,但“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于對象”(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頁。。人的“類本質”正是這種“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10)同上,第162頁。,由此回答了人是如何作為有理性的動物而存在的重要問題。
人的“類本質”規定突出兩大特性:其一,在空間之中存在的人是自由的。人之所以區別動物而成其所是,在于“把自身當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頁。。與其他物的類相比,人能自由自覺地將自身與自然相區別,不受固有尺度的束縛自由地筑造處所。人的自由性駕馭了空間的自然性,因此空間不僅是自在自然空間,而且是作為人的認識對象事先加工、生產的人化自然空間。其二,在空間之中存在的人是有意識的。人在與自然界交互過程中能夠辨明自然客體對主體的價值,并有意識地按照美的規律加以改造。“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12)同上,第162頁。馬克思將“有意識的生命活動”上升為“實踐活動”,探索人的本質及其“現實性”——“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3)同上,第501頁。。因此,經過實踐環節的人化的空間,必定是關系性的社會空間。
“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過渡,亦即空間的自然形態向社會形態的轉變。藉由人的“類本質”,空間不僅是一切存在的客觀前提,更是經由實踐主體自由的生命活動、有意識的勞動活動所創造的人化的空間。實踐將自然、人、社會勾連起來,描繪了人之存在的社會空間的整體圖式,展現了人與自然、周圍世界之關聯整體。
(三)屬人的空間實踐:社會空間的本質規定
人化的空間揭示了社會空間的規定性,超越了哲學史上物理主義空間觀的流俗之見。社會空間是人類實踐改造自在自然空間的結果,實踐是其理論基石。具體而言,實踐型構了交織在各個地點、位置中的社會關系,社會空間是實踐生產的社會關系的固定化。
社會空間是實踐的對象化產物。對對象、現實、感性的認識,機械唯物主義單純“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唯心主義卻“把能動的方面抽象地發展了”,馬克思則提出應將其“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14)同上,第499頁。。從物理空間的自然性窠臼解蔽空間的社會意義,是歷史唯物主義與舊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空間觀的區別。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明確使用“社會空間”概念,“使每個人都有社會空間來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現”(15)同上,第335頁。。空間實踐是人作為“類存在物”的能動活動,具有表現人的自由本質的社會現實性。所以,空間是主體空間實踐的作品,是人類本質力量的復現,是人、自然、社會相統一的空間。
社會空間的本質內容是社會關系。基于實踐論理路,“現實性”的人置身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中,而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16)同上,第525頁。。“類本質”力量創造的社會空間也具有屬人的“類特性”,進一步說,“類”指向社會關系。社會空間和社會關系具有交互作用:一方面,作為實踐產物的空間,是實踐生成的社會關系的投射,是社會化了的空間;另一方面,社會關系交織的空間是實踐場域,反過來規制實踐主體,社群中每個個體都要在其中找準定位。所以,空間既被社會關系生產,也生產社會關系,社會空間的意義即在此。
以實踐為核心的社會空間重構,是歷史唯物主義空間理論的復歸。歷史唯物主義超越了古代本體論“只見物、不見人”和近代認識論“只見人、不見物”的空間觀。畢達哥拉斯、牛頓的自然空間樣態轉向由主體空間實踐改造的社會空間,其本質是社會關系的鏡像形式,與人類存在、社會進程休戚與共。空間實踐具有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社會空間必定是現實的、歷史的,對空間的本體論、認識論的釋義進入到歷史視域,是歷史唯物主義空間理論生成的歷史性維度與必然性進路。
二、歷史空間:以資本主義為對象的空間批判
歷史空間是社會空間的動態展現、空間實踐的具體刻畫。馬克思提出“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頁。,洞悉了社會空間的歷史軌跡,實踐的時空嵌合是理解歷史空間的出發點。歷史空間不僅是社會空間的時間性演變,也是現實性形態。人類社會形態的歷史更迭勢必引起空間的重構,每一種社會形態、生產方式,都生產它自己的空間(18)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p.31.。歷史唯物主義把空間批判置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性中,從工人生存空間、城鄉空間、全球空間三個維度揭示資本的空間生產,從空間異化、空間分離、空間剝奪三個層面全方位批判資本現代性,資本空間化與空間資本化投射出社會結構的不平衡、社會關系的不對稱。如果說社會空間是生存實踐設置的舞臺,那么歷史空間就是資本生產規定的故事情節。歷史空間的意義由是觀之。
(一)工人生存空間的異化
生存空間是個體社會角色地位的展示。資本主義社會個體生存空間有鮮明的階級劃界與空間區隔,資產階級主導空間占有與規劃,工人階級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成為“馬拉松賽”(19)借用“馬拉松賽”的比喻,意指工人階級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甚至從社會結構的底層被排擠出去。(參見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的掉隊者。
空間的資本化使工人生存空間具有交換價值,成為資本家兜售的商品。資本家為牟取最大剩余價值,最大限度地壓榨勞動者的生存空間,將工人勞動生產的場所、日常生活的處所規劃到最狹小的空間范圍。恩格斯痛斥這一社會現象,工人“被吸引到大城市來,在這里,他們呼吸著比他們的故鄉——農村污濁得多的空氣。他們被趕到這樣一些地區去,那里的建筑雜亂無章,因而通風條件比其他一切地區都要差”(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10頁。。工人原先的住宅空間在資本的席卷下頃刻湮滅,喪失了生存空間的獨立性和完整性,被拋入“無家可歸”的境域之中。
工人的存在方式被改寫,淪為資本的工具。馬克思揭示勞動者生存空間的異化,他們被迫“退回到洞穴中居住,等等,然而是在一種異化的、敵對的形式下退回到那里”(21)同上,第233頁。。商品住宅作為勞動產品與勞動者相異化,工人生產空間的勞動投入越多,獲得的生存空間就越少,但包含剩余價值的空間商品卻被批量生產,資產階級企圖通過壟斷優勢地理空間獲得更多的級差地租。所以,出現住宅空間不斷擴大再生產與工人階級對住宅購買力不斷下降的矛盾,勞動創造了文明卻使工人退回到野蠻狀態。
(二)城市鄉村空間的分離
城市和鄉村的空間關系是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的一大表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2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頁。,機器化大生產激起的技術穿透力使城市成為資本文明的代表,鄉村發展則日漸式微。究其根本,城鄉空間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分工的結果。
城鄉空間關系是人類發展歷史分期的線索。城市、鄉村是社會的兩大子系統,運行過程中的空間關系勾繪出歷史發展的演變路徑,即城市鄉村化-城鄉統一-城鄉對立-鄉村城市化。“古典古代的歷史是城市的歷史,不過這是以土地所有制和農業為基礎的城市;亞細亞的歷史是城市和鄉村的一種無差別的統一……中世紀(日耳曼時代)是從鄉村這個歷史的舞臺出發的,然后,它的進一步發展是在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中進行的;現代的[歷史]是鄉村城市化。”(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3—474頁。空間是城鄉關系中最具顯示度的一個面相,不同社會的物質生產方式、空間實踐,生產不同的城鄉空間結構,以大工業城市為中心的城鄉二元分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現代性空間模式。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啟了城鄉空間分離的城市化進程。隨著野蠻向文明、部落向國家、地域局限性向民族開放性的過渡,城鄉對立貫穿資本主義文明進程,“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2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6頁。。城市、鄉村兩極化的根源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是分工,即工商業與農業的分化。鄉村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下,生產具有地方空間的狹隘性;而城市在現代性的流動和商業市場的擴張下,成為地域結構的中心。二是生產工具,即生產力的“落后”與“先進”之分。鄉村作為生產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的供應者處于資本循環鏈的底端,落入封閉、分散的邊緣空間。由此,鄉村屈從于城市,而“這種屈從把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城市動物,把另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鄉村動物”(2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6頁。。資本使物凌駕于人之上,主體被迫屈從于客體,成為受局限的動物,并以城市、鄉村為領地邊界,形塑了二元對立的等級化空間結構。
(三)落后民族空間的剝奪
空間是資本較量的權力場域,資本空間化構造出普遍物化的全球空間版圖。資本向宗主國的集中加劇了對殖民地的空間剝削,呈現為封閉性與開放性、地域性與全球性的空間對立,空間生產幕后的結構性權力得以顯明。
資本宰制下的全球空間發展不平衡,形成“中心-邊緣”的差序性空間格局。資本的空間性力求打破地域界限,“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26)同上,第566頁。。發達國家通過商品輸出建立起全球殖民體系,壟斷了空間的主導權,榨取土地等生產資料、傾銷商品,使落后民族、國家陷入搖搖欲墜的邊緣地帶,成為宗主國轉移資本危機的“垃圾堆”(27)[英]鮑曼:《流動的生活》,徐朝友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頁。。各民族、國家空間資源占有嚴重失衡,在共時性的空間并存之中形成耗散、斷裂的結構。
全球地理不平衡發展是權力結構的空間表現。全球空間的社會化形塑機制存在雙重剝削:其一,全球空間被置于權力的監視下無所遁形。“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2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頁。資產階級以變革交通、開拓市場為手段,將落后民族國家納入資本主義生產體系,這實際上是權力的嵌入,全球空間的擴張亦即權力的再分配。其二,發達國家通過運用將空間差異轉向時間差異的戰術,掩蓋世界市場擴張中的空間霸權。宗主國給殖民地貼上“落后”的標簽,以“先進-落后”的時間性話語遮蔽空間發展的失衡,“將共存的空間異質性涂抹成單一的時間系列”(29)[英]多琳·馬西:《保衛空間》,王愛松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95頁。,抹去全球資本生產的空間兩極化現實,弱化在現代性馴化下重新激發“他者”空間抗爭的可能性。美其名曰“先進”,實質是全球空間內嵌入式的權力結構。
根植于資本主義批判的歷史空間審視,是歷史唯物主義空間理論的批判性維度。“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3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頁。,斷不能把人倒置為實現目的的手段。歷史空間是對資本主義異化空間的戰斗,指向未來希望空間的獲得。具體而言,工人生存空間的異化、城市鄉村空間的分離、落后民族空間的剝奪,披露出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本質以及空間“拜物教”的極端化。歷史空間審視觸及了社會歷史現實的空間實在,是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反抗話語,空間的非正義問題倒逼了空間正義的出場,探尋將“人”從“物”的殖民空間中解放的空間路徑。
三、空間政治:以空間正義為旨趣的空間革命
從實踐論探究空間問題,不只是以不同的哲學理路闡釋空間,而是“改變世界”(31)同上,第502頁。。歷史唯物主義對“社會-歷史”空間之解蔽與批判,繼而轉向政治意義的空間突圍,尋求實現“空間正義”的革命路徑。空間正義并不指涉中立的容器式空間,而是對住宅問題、城鄉對立、全球發展失衡等空間非正義問題給予政治回應。歷史唯物主義闡釋了資本、空間與現實性的人之間的辯證關系,洞悉資本主義空間矛盾之源,將空間作為政治抵抗的場域。勞動者身體空間對資本殖民的反抗,是空間革命的主體覺醒;自由的生產者聯合起來建立共產主義共同體空間,是空間革命的必經之路。解構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以共產主義空間革命實現政治空間解放,是歷史唯物主義空間理論的政治旨趣。
(一)革命理想:空間正義與人類解放
當資本空間化和空間資本化超過一定限域,必然使資本危機的空間轉移遇到天花板,社會沖突和階級矛盾也就爆發在即,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合法性基礎岌岌可危,空間正義必然出場。那么,何謂空間正義呢?哈維指出,空間正義是“社會關系和競爭性權力構型與特定時間內調節和安排地方的物質社會實踐之間的密切聯系”(32)[美]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胡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0頁。。空間與社會關系、權力構型的作用機制,隱喻了空間的政治品格。地理差異不是自在的,空間非正義問題必須通過空間革命解決,最終通達空間正義。
社會關系是空間正義的切入點。馬克思將人類歷史劃分為自然發生的“人的依賴關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以及全面發展基礎上的“自由個性”三大社會發展階段(3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108頁。。這一進程也是人的交往從“最狹小孤立的地點”到“片面的地域性局限”再到“世界歷史性”的空間化過程。早期人類生存范圍受自然空間限定,以“人的依賴關系”為特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突破了自然空間的壁壘轉向并存式的空間樣態,擺脫了人身依附關系,但卻是在“物的依賴關系”上的個人獨立;共產主義社會是對原始的“人的依賴”以及現代的“物的依賴”的揚棄,掙脫奴役、物化的社會關系,是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可見,“現實性”的人是社會性、空間性存在,人只有在普遍性交往活動、豐富性社會關系中,才能實現自身存在的全面性。社會關系的解放,在政治關系、經濟關系之外,隱含了空間關系的革命。
從社會關系建構來看,共產主義革命是政治性的空間解放。資本主導的空間生產機制給社會關系套上自然物的“硬殼”,“技術性的大動亂使人的關系和隨后的日常生活變得如此委頓”(34)[法]列斐伏爾:《什么是現代性?——致柯斯塔斯·阿克舍洛斯》,李鈞譯,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1—42頁。,以致自由的闕如。為破除空間拜物教的意識形態神話,馬克思指出“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3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0頁。。保衛空間正義,正是試圖以一種替代性的力量,解構資本主義社會主導二元空間結構的權力關系,使積極的主體間關系從商品物神化的客體關系桎梏下解放出來,建構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空間。
(二)革命力量:抵抗規訓的身體空間
資本主義社會的空間矛盾與空間爆炸,必然引起共產主義空間革命。那么,借用何種力量才能通達理想空間?資本空間化運轉始于割裂工人生存空間的整體性、占有其總體性勞動空間。所以,“現實的個人”是抵抗空間規訓的革命力量,勞動者身體空間的反抗是保衛空間的起點。反思身體空間如何被資本規訓、如何成為政治策略的一部分,指向勞動在資本附庸中如何重獲自由與解放、確立自由全面發展的身體空間。
首先,身體空間是社會有機體的細胞、社會結構的基本要素、社會關系的縮影。身體空間是歷史性的社會存在,“壓制、社會化、約束和懲罰的力量所要施加于的正是這種空間。身體存在于空間里,或者必須服從于權威”(36)[美]哈維:《后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267頁。。資本主義社會高度細化的社會分工割裂了整體性勞動空間,使勞動者身體空間碎片化、固定化,成為可替換的“機器部件”(37)《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05頁。。如福柯所言“全景敞視主義”(38)[法]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219頁。的權力場域,空間規訓顯現出社會政治權力對勞動者身體空間的嵌入與殖民。
其次,空間與資本的相互作用導致身體空間的單向度化。資本邏輯從抽象、空洞的自然屬性去理解人的存在,將其視為現成的自然存在物以及物質財富的生產機器,以最大限度攫取剩余價值為目標,褫奪了主體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一切物本是人與人交往的產物,但資本主導的空間生產使社會關系被物化,資本對身體空間的殖民使冰冷的物的關系遮蔽了溫情的人的關系。對此,共產主義空間革命號召勞動者抵抗資本主導的空間生產,消解異化、壓迫的社會關系,以獲得自由的生存發展空間。
最后,身體空間為敞向空間正義提供可能。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的身體空間是“通過與資本積累動態之間常常是創傷性的、沖突性的關系而形成”(39)[美]哈維:《希望的空間》,胡大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8頁。。身體空間的受限性正是保衛空間正義的力量來源,瓦解非正義空間的生產機制需要從生產場所的“螺絲釘”開始,即將勞動者身體空間作為空間革命的基本單元。空間革命指向破除資本對身體空間的枷鎖,讓自由得以顯現。馬克思言明真正的物質生產勞動領域彼岸的“自由王國”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40)《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8頁。。被權力規訓的身體空間隱含了具有反抗力量、打破工具理性化的空間“硬殼”的“他者空間”,是空間政治抵抗的革命力量之能在。
(三)革命路徑:自由人的空間聯合
共產主義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歷史唯物主義將其視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理想。通過自由人的聯合開展世界范圍的普遍交往,建構全面自由的社會關系,建立共產主義共同體空間,從閉塞、分散的地域空間轉為開放、整體的全球空間,是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與規律。
自由人的聯合是共產主義空間革命的基本手段。資本全球擴張不斷激化的空間矛盾,為無產階級革命實踐帶來契機。馬恩指明了一條空間革命之路,即“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4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21頁。。“自由聯合”的空間革命拓寬人的自由活動空間、使人不再被拋入受外在性物質力量所控制的深淵之中,開拓了政治行動的可能性空間。“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聯合的人的產物,處于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42)《資本論》第1卷,第97頁。共產主義革命的核心在于觸及空間實踐的社會性本質,經由“地域性個人”轉向“世界歷史性個人”的轉變,克服地域空間的狹隘性和單面性,使資本之謎得以破解。
自由人聯合起來的空間革命之路最終通往空間正義的共同體。馬克思揭露歷史上以統治和服從的社會關系為基礎的社會有機體具有空間狹隘性,是“虛幻共同體”,“真正的共同體”是自由人聯合起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即“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4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頁。,是主體間世界性的空間關系。作為良性社會關系投射的共同體空間,不再是束縛主體的外部自然環境,而是主體空間本質力量的彰顯。共產主義社會實現的空間正義,是完成的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的一種面相。
歷史唯物主義從“社會-歷史”兩個向度重建“空間想象力”。首先,將空間置于社會實踐與社會關系場域,剖析空間的社會意蘊。實踐呈現人與空間的關系,映照出空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多重社會品格,超越自在自然空間的是由實踐加以改造的人化的社會空間。其次,基于歷史空間的向度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解構資本主導的空間生產。資本主義社會的空間分離實質是政治區隔,對此要掀起一場總體性的共產主義空間革命以通達空間正義。總之,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解空間提供新的致思路向,從社會實踐破解自然空間之謎,由空間實踐生產的空間結構應是維護社會良性運行的基石,自然、社會、歷史三個領域由此構成一個共在、共生、共融的空間,開啟了對以往形而上學空間哲學的顛覆,擦亮了此后都市馬克思主義審視社會的“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鏡頭”(44)[英]哈維:《新帝國主義》,初立忠、沈曉雷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