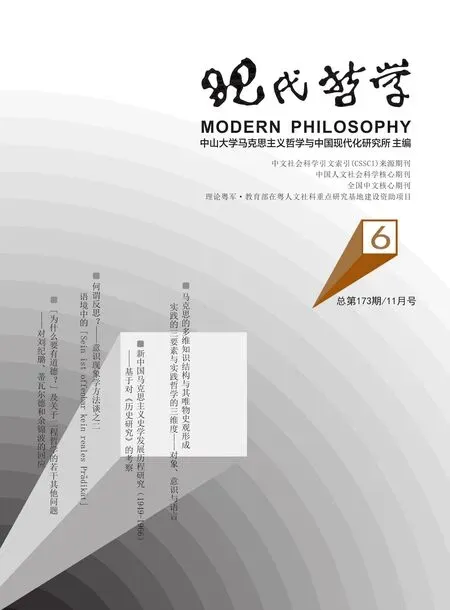論康德對公民資格的先驗闡釋
居 俊
在康德的政治哲學中,“公民”無疑是核心概念。實際上,康德政治學說的整體可以視為以公民概念為邏輯起點進行推演的體系。由它衍生而來的“國家公民”“世界公民”“永久和平”等話題雖已膾炙人口,但這并不代表我們有了對該概念的確切理解。當前國內外學界對它的闡發大多集中于政治法律層面。例如,霍華德·威廉姆斯(Howard Williams)指出,康德的公民概念涉及私人公民領域、公共的國家領域與國際性的公共領域三個部分(1)Howard Williams, “Bürger”, Kant-Lexikon, hrsg. von Marcus Willaschek, Jürgen Stolzenberg, Georg Mohr ,Stefano Baci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5, S.314.;而在羅納德·貝納(Ronald Beiner)看來,在康德公民概念中存在著與道德相關聯的高自由主義與僅限于政治的低自由主義兩種維度之間的張力(2)Ronald Beiner, “Paradoxes in Kant’s Account of Citizenship”, Responsibility in Context, ed. Gorana Ognjenovic, Dordrecht: Springer, 2010, pp.19-22.;韓水法則歸納了康德公民概念的三重語境,即社會契約論語境、時代背景語境與未來的世界公民語境(3)韓水法:《康德法哲學中的公民概念》,《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第38—40頁。。這些觀點雖然頗具洞見地剖析了“公民”在康德政治哲學中的多重含義,卻忽略了他給予它的先天性。事實上,先天性是其先驗哲學附加在公民這一政治概念上的本質屬性。公民概念的先天性不僅意味著康德給予政治的先驗提升,更預示著先驗哲學鮮為人知的政治意涵。現今,公民概念的先天性由于缺乏重視還沒有得到合理闡釋。在我們看來,公民概念先天性的最初來源是先驗哲學中的普遍主體理念。這一理念首先體現在理論性的先驗自我之中,隨后也表現在作為實踐自我的自由意志之中。作為普遍道德法則的發布者,自由意志具有普遍性,是公民先天性的直接源頭,也造就了法權領域。在該領域中,作為公民體制典型的國家理念與先天的公民原則(自由、平等、獨立)得以出現。而這種對公民概念的先驗闡釋證實了康德哲學在根本上具有的政治性。
一、先驗自我的普遍主體意蘊
雖然以公民概念為核心的法哲學與政治哲學直到康德晚年才構建完成,但公民概念的先天性卻扎根于早已巋然屹立的批判哲學之中。羅爾斯曾頗具洞見地指出:“在康德的觀點中,個人與社會的基本觀念之基礎……是其先驗觀念論。”(4)[美]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萬俊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92頁。譯文有所改動,參考了英文版的Political Libr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韓水法也認為,康德的公民概念“是從先天的理性法則中演繹出來的”(5)韓水法:《康德法哲學中的公民概念》,《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第40頁。。那么,在其廣博的先驗哲學里,究竟什么可以作為生發公民概念的源泉呢?如果霍華德·威廉姆斯指明的康德公民概念從私人、國家擴展到世界的趨向是正確的,那么我們就必須認可公民概念具有的普遍性。可以說,康德的公民概念表達了一種政治性的普遍主體身份。而在批判哲學中,這種普遍主體意蘊的始基必須追溯至先驗自我(統覺)。因為先驗自我經由自己包舉宇內的統攝力,將一切表象都歸之于自己名下。康德明確說道:“一切不同經驗性的意識都必須被結合在一個惟一的自我意識中,這個綜合命題是我們的一般思維的絕對第一的和綜合的原理。”(IV87)(6)[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第1版)》,《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本文所引康德著作原文,全部基于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李秋零主編的中譯本《康德著作全集》。由于李秋零譯本根據普魯士皇家科學院版《康德全集》(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hrsg. von K?niglich Preuβ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Berlin: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05-)譯出,因而為簡便起見,本文所用引文將只標明普魯士皇家科學院版《康德全集》的卷數與頁碼。引文需調整之處,依據該全集進行改動。正是通過將一切表象結合在先驗自我之中,先驗自我變成對一切知識擁有普遍效力的最高裁判官,它的普遍主體意蘊也得到彰顯。
不過,先驗自我的普遍主體意蘊并不指示著它自身可以產生這些表象。毋寧說,它只是通過在伴隨這些表象時保持自身同一,進而使得所有表象以它為中心產生聯結。這種伴隨和聯結的功能就是先驗自我自發性(Spontaneit?t)的表現。先驗自我的自發性僅僅意味著形式性地對諸表象進行整理和歸納,卻無權過問表象的實質來源。在康德的眼中,表象是由我們的感性接納進來的,而作為知性應用的至上原則,先驗自我只負責將這些表象統一起來。康德由此表達了先驗自我的普適性:“我因此是就一個直觀中被給予的表象的雜多而言意識到同一的自己的,因為我把這些表象全都稱為我的表象,它們構成一個表象。”(III110)正如倪梁康所言,先驗自我的意義在于“它使……我進行的所有的意識活動被意識為‘我的’”(7)倪梁康:《自識與反思》,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66頁。。
正由于先驗自我始終代表著形式的統一性,所以它的普遍主體意蘊是受限的。進言之,它與現實的經驗主體也不盡相同。對于康德來說,經驗自我由內感官塑造,在任何時候都是可變的,進而“在這種內部現象(Erscheinung)的流動中不可能存在任何固定的或常駐的自我”(IV81)。事實上,經驗自我與先驗自我的區別正如亨利·阿利森(Henry Allison)所道明的:“經驗性統覺是通過日常的反思或內省達成的。它總是在與內感官的關聯中發生,這也許是康德有時為何將它們等同起來的原因。與之相對,先驗統覺則是一種哲學或先驗反思的產物。”(8)Henry 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74.但這并不意味著經驗自我與先驗自我無關。毋寧說,先驗自我是經驗自我的基礎,因為“我們先天地意識到我們自己一貫的同一性……它是一切表象的可能性的必要條件”(IV87)。所以,就經驗自我同樣是我們的表象(更確切地說現象)而言,它也在先驗自我的終極統攝性之下。
如若先驗自我可以作為經驗自我的基礎,那么先驗自我是否就是終極的自我自身呢?我們知道,康德先驗觀念論的基本特征是對世界進行的現象與物自身的二分。他對此解釋道:“我把一切現象的先驗觀念論理解成這樣一種學術概念,按照它,我們把所有的現象均視為純然的表象,而不視為物自身……”(IV232)這樣,一切事物在他看來都必須區分為現象與物自身兩個層面。我們所能認識的只是事物的現象,它作為我們的表象而存在,而事物的物自身那一面是不可知的。由此,作為物自身的自我在他的視域中也不可能被認識。他認為:“我因此擁有的對我的認識,不是如我所是的那樣,而僅僅是如我向我自己顯現的那樣。”(III123)也就是說,我們平常所能認識的只是經驗自我,卻不會是自我自身。
這是否暗指著,我們憑借先驗自我也不可能達及自我自身呢?康德確實是這么認為的。他指出:當我們從不包含任何雜多的先驗主體概念出發,推論出這個主體本身的絕對統一時,這一推論就是純粹理性的謬誤推理(Paralogismen)。(III261-262)在他看來,笛卡爾正是這一謬誤推理的始作俑者,因為笛卡爾相信“我是一個實體,這個實體的全部本質或本性就是思維”(9)[法]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集》,龐景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85頁。,“我思”由此被當作持存常駐的思想實體。與之不同,康德認為,作為先驗自我的“我思”僅是一個自發性的表象,“必然能夠伴隨所有其他表象并在一切意識中都是同一個東西” (III108)。所以,雖然笛卡爾和康德都將理解世界的基礎歸于“我思”這個阿基米德點,但兩者的意味截然不同。前者的“我思”是實質性的終極存在者,而后者的“我思”是形式性的統括行動。進言之,在康德看來,笛卡爾的錯誤在于“他將形式的或先驗的我等同于真實的或本體的自我”(10)Henry 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ce, p.282.。由于先驗自我(我思)的功能是為了將所有其他表象結合在自身之中卻不產生這些表象,因此先驗自我是“單純的、自身在內容上完全空洞的表象:我”(III265)。質言之,先驗自我是一個空洞的形式自我,“一個思考性主體(思想的一個邏輯主體或‘一般主體’)的單純形式性概念,亦即當內感官的內容被抽離時的所有剩余物”(11)Ibid., p.283.。因此,先驗自我并不構成對于自我本質的洞見,而僅僅意指著思考世界的一個主體性原點。易言之,在“我”的意識中呈現的一切都將絲毫不差地被“我”把捉。
先驗自我的普遍必然性是康德先驗哲學的基本原理,他對公民概念先天性的界定同樣與先驗自我的普遍必然性息息相關。在最源始的意味上,“公民”從私人到國家、再到世界的擴展必須基于一種普遍主體身份。舒遠招精當地指出,“康德的世界公民概念本身即具有典型的普世意義”(12)舒遠招:《從世界公民概念看康德的普世主義思想》,《廣東社會科學》2012年第4期,第74頁。。而在康德哲學中,公民概念的普世意義最初導源于先驗自我的普適性。因為先驗自我所表達的普遍主體理念,和康德賦予公民的公共性訴求一脈相承。由于先驗自我是純然形式化的表象,因而它的普遍主體理念不可避免地是一種形式。一旦用諸種經驗質料對該形式加以充實,那么在它之下就會呈現出各各不同的經驗自我。相對于作為普遍主體的先驗自我,這些經驗自我就是個別主體。我們日常所見的人倫世界,恰好由個別主體聚合而成。但從經驗自我與先驗自我的關系中可以推出:諸經驗個別主體建構的人倫世界,必須以先驗普遍主體為標的。易言之,即便先驗普遍主體是不可見的,它也是可見的經驗個體將自己確立為主體(亦即理性存在者)的準繩。在批判哲學的視域下,經驗要素展示人們相互差異的方面(如出身、財富、性格等),但先驗要素卻道明他們彼此一致的淵源——理性。正如瓦爾特·斯懷德勒(Walter Schweidler)分析的,“我作為理性存在者是普遍的精神,而我作為個體是自我中心的和自私的自然”(13)Walter Schweidler, Der gute Staat-Politische Ethik von Plato bis zur Gegenwart, Wiesbaden: Springer Fachmedien Wiesbaden, 2014, S.127.。由此,康德才頗為自豪地宣布:“理性完全從自身創造的東西,都不可能隱匿自己,而是只要人們揭示了它們的共同原則,它們本身就會被理性帶到光天化日之下。”(IV13)
這樣,理性在本質上表征一種普遍性力量,而這種力量在康德理論哲學中的最佳代表是先驗自我。先驗自我的普遍主體意蘊集中體現在先驗自我對經驗自我的奠基作用之中。無疑,這種作用發源于先驗自我的自發性。實際上,這一自發性是先驗自我成為普遍主體的根據。盡管先驗自我的自發性僅僅意味著對諸表象的綜合統一,但“這種自發性卻使得我把自己稱為理智(Intelligenz)”(III123)。事實證明,康德將先驗自我視為理智這一點是意義重大的。在楊寶富、張瑞臣看來,理智非但是自我的本質規定,而且打開了自我從思辨領域進入實踐領域的大門。(14)楊寶富、張瑞臣:《康德實踐哲學中的自我問題》,《求是學刊》2015年第4期,第26—27頁。當先驗自我轉變為實踐自我,它的普遍主體意蘊才得到更充分和本真的開顯,作為公民概念基石的普遍意志概念也終于“登上舞臺”。下面就進入康德的實踐哲學來探討該問題。
二、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
在批判哲學中,先驗自我向實踐自我的轉化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如上所述,理智這個概念是兩者變換的樞紐,而這一轉換依舊始于現象與物自身的二分。由于在康德看來,人只能認識現象,無法認識物自身,所以他將世界劃分為感性世界和理智世界。“其中前一個世界按照各種世界觀察者里面感性的差異也可以極為不同,但作為其根據的后一個世界卻始終保持為同一個世界”(IV451)。既然對于人來說,也存在著經驗自我與自我自身的二分,那么將前者歸入感性世界、后者歸入理智世界就合情合理。因此,人發現自己同時處身于感性世界與理智世界之中。正是在歸屬理智世界的意義上,人作為理性存在者才能將自己稱為理智。
由此,康德之所以把先驗自我稱為理智,是因為先驗自我表達了知性的自發性,而這種自發性與感性的接受性相反相成。盡管先驗自我意指著一種僅可思維、不可直觀的有限知性,但畢竟揭示了自我自身不同于被動感性的行動本質。用康德的話說,“我思表現著規定我的存在的行動”(III123)。亨利·阿利森也指出,先驗統覺“并非當一個人在判斷時所做的另一件事(對一個人正在進行認識的二階認識),毋寧說它是一階的行動本身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15)Henry Allison,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Cambridge: Cambridge Uinversity Press, 1990, p.37.。即便我們在思辨領域中不可能經由先驗自我直接把捉到自我本身,但先驗自我的確預示了自我本身是“某種不可見的、自行活動的東西”(IV452)。那么,自我何以能具備這種自行活動的能力呢?康德認為,這恰好是由于人具有理性,而理性就是純粹的自動性(Selbstt?tigkeit)。理性的自動性高于知性的自發性,這不僅是因為就知識體系的建構而言,理性居于知性之上,更是因為理性的自動性完全超出感性的束縛,而知性的自發性在沒有感性配合的情況下無法發揮作用。
這樣看來,知性只是暗示作為本體的理智自我的存在,而理性足以證實它的存在。理性不僅是指對于感性條件的獨立性,更是自行開啟事件序列的能力,亦即自由。正是從奠基于理性的自由理念中,自我才獲致積極行動的能力。這也是康德將自由與自我意識相等同的原因。他在評注形而上學的遺稿中說:“自由……盡管不能被解釋為第一原則,卻是先天的自我意識,只要它是理性自身的一個行動和因果性概念。”(XVIII182)顯然,自由所展示的這種自我意識是實踐性的。這樣,先驗自我的自發性就過渡到實踐自我的自由。
如果我們承認自我本身是實踐性的,進而是自由的,那么自由理念就將先驗自我在思辨領域尚且受限的普遍主體理念提升到了絕對高度。換言之,自由理念展現了真正意義上“至大無外”的主體觀念,這一觀念是康德公民概念先天性的直接來源。不過,要理解這一點,首先要從他對自由的規定談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自由是與“自然必然性”相對立的概念。“先驗辯證論”部分第三個二律背反表達了這一對立:“正題:按照自然法則的因果性,并不是世界的現象全都能夠由之派生出來的惟一因果性。為了解釋這些現象,還有必要假定一種通過自由的因果性。反題:沒有任何自由,相反,世界上的一切都僅僅按照自然法則發生。”(III308-309)那么,自由與自然必然性之間的背反如何化解呢?正如阿倫·伍德(Allen Wood)所指明的,“由自然因果性而來的規定應用于作為現象世界之部分的我們的行動之上,但康德堅持認為,當我們被思考為物自身時,這一應用與將我們自身認定為自由是一致的”(16)Allen Wood, “The Antinomies of Pure Reas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on, ed. Paul Guy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63.。所以,還是經由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前者中的自然因果性獨立于后者中的自由。不過,鑒于人所能直觀的只是為自然因果性決定的現象界,因而即便我們覺察到作為本體的自我可以自由行動,也不能直接證實自由的存在。
可見,人如何能夠確證自身的自由依然是一項有待解決的任務。康德認為,這項任務只有通過對道德法則的意識才能完成。而他對這條道德法則的表述是廣為人知的:“要這樣行動,使得你的意志的準則在任何時候都能同時被視為一條普遍立法的原則。”(V30)在此,意志的準則是經驗性的,由個體特殊的稟賦、習慣和環境等塑造,因而僅僅被個體視為對其意志有效。而普遍立法的原則是公共的,對每個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而道德法則要求的是:人將自己意志的主觀私人準則上升為普遍立法的客觀公共原則。因為“對我進行道德性的規定就是克服作為個體的我”(17)Walter Schweidler, Der gute Staat-Politische Ethik von Plato bis zur Gegenwart, S. 127.。人若想獲得自由,其意志理應經歷“由私到公”的轉變,因為“道德法則將作為理性存在者的我們相互聯結在一起”(18)Ibid., S.126.。換言之,“每一個理性存在者都必須通過自己意志的一切準則而把自己視為普遍立法者,以便從這一觀點出發來評價自己以及自己的行為”(IV433)。
正是通過道德法則,人的意志才能摒棄種種私欲的影響,回歸到普遍立法的終極意志。在康德的看來,這個普遍立法的意志就是自由意志。這一論點成立的關鍵,是他對“意志”所作的形式與質料之分。在他看來,意志的結構一般可以分為普遍立法的形式和作為意志對象的質料。這樣,意志的形式是理性所具普遍必然性的外現,是唯一且恒定的;而它的質料由經驗對象構成,是雜多且變動的。顯然,一個普遍立法的意志的規定根據不能是作為意志客體的經驗對象,只能是普遍立法的形式。只有這種形式才能避免各個私人主體將自己的經驗偏好當作意志的規定根據。而當一個人意志的規定根據是經驗性的偏好之時,那么他/她的意志就是私人的、暫時的,不能擔當普遍立法的重任。相反,一個普遍立法的意志必須超出此種狹隘境地,“以天下為己任”,因此才將普遍立法的形式視作旨歸。正如克里斯多夫·霍爾恩(Christoph Horn)所指出的,“在一個離棄了所有目標的形式中去思考意志,同時意味著在它那未被染污的、未經蛻化的形式中去理解它”(19)Christoph Horn, “Wille, Willensbestimmung,Begehrungsverm?gen(§§1-3,19-26) ”,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hrsg. von Otfried H?ff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2, S.48.。這一形式“只能由理性來表現,因此不是感官的對象,故而也不屬于現象”(V28)。一個以普遍立法的形式為規定根據的意志,即普遍立法的意志必定獨立于現象,進而獨立于現象內蘊的自然因果法則。在最嚴格的意義上,對自然因果性的獨立就是自由。這個普遍立法的意志正好達致對自然因果性的獨立,所以它就是自由意志或純粹意志。進而,“它僅僅依據一種具備普遍化能力的法則的表象而變得有行動效力”(20)Ibid., S.48.。
經由自身所立的道德法則,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對人的行動有最普適的規約性。正如黃裕生指出的,自由意志是真正的主體之“我”。(21)黃裕生:《德國哲學論證自由的三個向度——論德國哲學在論證自由問題上的貢獻》,《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第117頁。就此而言,自由意志所代表的實踐自我,占據著最強意義上的普遍主體性。而在認識領域中,先驗自我被拘囿在對經驗性材料的普遍聯結之中,僅僅表達一種受限的自主性,其普遍主體意蘊是有限的。與之相對,在實踐領域中,實踐自我經由自由意志直接對人的行為產生“應然”意義上的強制,因而臨在于個體自我的意識之中。這種普遍主體的規約性是絕對的,因為這一規約的對象不再是認識論意義上的外部對象,而是實踐性的個別主體自身。易言之,這是實踐自我對各個主體的無條件規訓:“人們應當絕對地以某種方式行事。”(V31)我們在此應當依循的行事方式,只能由普遍實踐主體來規定。對此,斯懷德勒評論道:“人之本性……具體化在那種張力中,在其中我們中間的每個人作為受動機規定的‘經驗主體’遭遇到了一種普遍理性化的要求。”(22)Walter Schweidler, Der gute Staat-Politische Ethik von Plato bis zur Gegenwart, S. 126.無疑,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是這種普遍理性化要求的發起者。由此,實踐自我的普遍主體內涵徹底地宣告出來。只要我們承認自己理性存在者的身份,由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頒布的道德律令就不由分說地呈現給我們,不管我們最后的行為是否依循它。由于道德法則與自由意志是互相回溯的,在道德法則現身之時,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將同時在場。據此,該意志所表征的、實踐自我意義上的普遍主體也直接地為我們所察覺。
這個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呈示的普遍主體理念對康德公民概念的生成是決定性的,因為“公民”從私人擴展到世界的公共性根據就在于這個意志的普遍性。下面將展現康德從普遍意志推演出公民概念的詳細進路。
三、基于法權的“公民之公”
康德的實踐自我所表征的普遍意志首先是道德的基礎。不過,這一普遍意志同時是法權(Recht)的來源。他明確指出,只有按照先天必然聯合起來的全面的立法意志之原則,一種一般而言的法權才是可能的。(VI263)問題在于,一種道德性的普遍意志如何成為法權領域的創生者呢?如前所述,康德的普遍意志概念從意志規定根據的普遍化律令中產生,因此這個概念首先針對一般意志的因果性,它所賦予人的是一種與自然因果性相對的自由因果性。這種內在的意志自由與我們一般理解的自由選擇還沒有直接聯系,只有當它與產生客體的行為能力的意識相結合,它才演變為意決(Willkür)(23)Willkür一詞的翻譯在學界頗受爭議。據不完全統計,目前的譯名有任意、任性、意愿、選擇、決斷、抉意等。本文采納“意決”的譯法,意思是意志的決斷。的自由。這一自由指受普遍意志(即純粹理性)的規定去行動。如果人受感性偏好的刺激而行動,他/她的意決就是不自由的、動物性的。只有當普遍意志降臨到每個人的意決之中時,個體的行動自由才得到彰顯。在康德看來,每個人意決指向的外在行動在一個普遍的自由法則之下保持一致的總體關系即是法權領域。這樣,從作為初始根據的普遍意志向意決的外在行動的擴展,證明了創生道德領域的自由意志同時是法權領域的締造者。正如溫純如指出的,“康德把法權思想放在道德哲學框架內給以道德化,自由意志是道德和法權共有的基礎”(24)溫純如:《論康德從意志到自由意志的思想》,《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第42頁。。
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創造了每個人的意決自由相互協調的法權空間,這個空間被康德稱為公民體制(die bürgerliche Verfassung),而“公民體制是自由人的一種關系,這些自由人……畢竟處在強制性法則之下”(VIII290)。就此而言,自由意志所創設的公民體制指涉著擁有意決自由的個體之間的“強制性聯合關系”。這一關系的協調經由如下“普遍法權法則”進行:“如此外在地行動,使得你意決的自由使用能夠根據一個普遍法則與任何人的自由共存。”(VI231)換言之,只要“我的”行動自由沒有現實地侵擾“你的”,“你的”也未現實地干涉“我的”,那么“我”和“你”就處在該法權法則制定的良性秩序之中。康德甚至說:“每個人都可以是自由的,即便我對他的自由全然不關心,或者即便我內心很想破壞他的自由,只要我通過自己的外在行為并沒有損害他的自由。”(VI231)概言之,這條法則闡明了什么是正當的,因而保障了所有人的自由不被侵犯。與之相應,它包含了一種普遍的交互強制,即所有人都不可侵犯他人的自由。康德指出:“嚴格的法權也可以被表現為一種與每個人根據普遍法則的自由相一致的普遍交互強制的可能性。”(VI232)
處在法權關系中的人們當然是自由的,因為他/她們的外部行動任何時候都不可被侵犯;但他/她們又處處受強制,因為他/她們任何時候都不可去侵犯他人的外部行動。法權概念正是表達了人與人之間自由與強制交相對等的均衡關系網。公共法權是將這些均衡關系“公之于眾”的總和。在康德看來,公共法權對人自由與強制的總體界定是公民體制。易言之,當所有人都處在由普遍法權法則構成的自由與強制的交互關系中時,公民體制就誕生了。公民體制的出現意味著人贏獲了公民的資格。事實上,公民體制下的所有成員都通過參與制定對普遍意志進行規定的法則而成為公民。(25)Howard Williams,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Oxford: Basic Blackwell Publisher Limited, 1983, p.179.
康德認為,統攝在普遍意志下的人處于公民狀態之中。易言之,公民體制和公民資格植根于普遍意志之中,更確切地說起源于先驗自我與實踐自我所表征的普遍主體理念。在普遍主體理念的視域下,理性人在外部關系中必須維持相互間的自由與強制關系,否則他/她們就不配享有“理性存在者”的稱號。如上所述,這種交相對等的自由強制關系正是公民資格的誕生地。因此,批判哲學中的“公民”雖然涵蓋源自現實經驗的要素,但在根本上是衍生自人之理性本質的先天概念。簡言之,只要人認可自己理性存在者的身份,那么他/她天然地具備公民資格,不管他/她就目前的狀況而言生活在一個共和國或專制國之中。
所以,康德哲學在根本上含有政治性。這主要是因為他對普遍理性主體的強調使公共性從一開始就是其哲學的題中之義。從他實踐哲學的兩條“金規則”——道德法則和法權法則可以看出:無論是人的意志自由還是意決自由,都與作為公共性尺度的普遍意志發生關聯。進言之,批判哲學從理論性的先驗自我出發,最后落腳于世界公民的永久和平理想上,這絕非偶然。如上所示 ,先驗自我與實踐自我展示的普遍主體理念,藉由普遍意志可以融貫地導出政治性的公民資格。
總之,先驗自我和實踐自我作為普遍主體理念的代言人,預示了公民在公共法權狀態下必然聯結的可能性。進而,作為共同體的國家得到其建構的先天基礎。因此,國家的合法性是基于公民將自己構成國家的源始契約理念,“根據這個契約,人民中的所有人……都放棄自己的外在自由,以便被視為一個共同體的諸成員……而立刻重新接受這種自由。”(VI315)這樣,只有當所有公民放棄外在自由之時,各公民的意志才集合為形成源始契約的普遍意志。在這一普遍意志下,公民的外在自由得到恢復,作為共同體的國家也出現了。顯然,國家在理念上是保護公民外在自由的法權共同體。
既然國家之為法權共同體的本質特征由普遍意志決定,那么公民作為國家主體的內在原則也來源于該意志。在康德眼中,只有一個源始地和先天地聯合起來的意志才能產生公民狀態。而自由、平等和獨立這三個在啟蒙時代振奮人心的口號,是公民狀態內含的三條先天原則。易言之,“公民狀態僅僅作為有法權的狀態來看,建立在如下的先天原則之上:1、社會中作為人的每個成員的自由;2、社會中作為臣民的每個成員與每個他人的平等;3、一個共同體中作為公民的每個成員的獨立”(VIII290)。
由此,公民所具的自由、平等與獨立諸原則依舊從“法權”概念引申而來。首先,公民的自由依據普遍的法權規則得以界定。康德指出:“每一個人都可以沿著他自己覺得恰當的途徑去尋求自己的幸福,只要他不損害他人追求一個類似目的的自由……這種自由是能夠按照一種可能的普遍法則與每個人的自由共存的。”(VIII290)在這里,公民的自由表現為與他人自由共存的對自身幸福之追求。由于“公民自由”是指在法權意義上對外在行動的規定,所以在一種均等的公民體制下,他人不可干涉我的行動,我亦不能侵擾他人的行為,我與他人盡可按各自所想追求自身幸福。需要注意的是,“公民自由”是價值中立的法權概念,但它真正的根源是道德學說中的“意志自由”。康德明確將兩者的關系類比于空間與時間的關系:空間中有外感官的對象,時間中則有一切對象,內感官對象和外感官對象都在其中;同樣,公民自由只是外在自由,而意志自由是自由的本源,既包含內在自由,也涵蓋外在自由。
既然“意志自由”可以從與之互相回溯的道德法則中推演出來,那么“公民自由”同樣源自普遍的法權法則。事實上,法權法則首先表現為對公民自由的規定。但從這一法則出發,公民的平等和獨立也可得到解釋。康德曾對公民的平等作出規定:“即就他自己而言,不承認人民中有什么上司,而只承認這樣一種人,對這種人他有在法權上進行約束(verbinden)的道德能力,正如這種人可以約束他一樣。”(VI314)所以,公民的平等是指公民之間在法權上的相互約束關系,即“共同體的每一個成員都對任何其他成員擁有強制性法權”(VIII291)。那么,為何每個成員都對其他成員擁有強制性的法權約束力呢?這是由于“作為普遍意志的表達,法權只能有一種,而且它涉及法權的形式”(VIII292)。因此,每個人都可經由公民身份將自己提升至普遍化的形式法權之中,這就對其他公民產生強制性。這是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康德闡釋。在他的眼中,該法實乃普遍意志所立的公共法,即普遍的法權法則。由于這條法則,“所有屬于人民的人都作為臣民處在一種一般的法權狀態中,亦即處在一種依據普遍的自由法則相互限制的意決的作用與反作用的均等狀態之中”(VIII292)。所以,每個人就其外在自由的使用權限而言一律平等。正因為普遍的法權法則導出了自由與強制的交互關系,因此每個人都處于穩定的關系結構中,進而他們作為公民完全平等。換言之,每個人都在普遍法權法則下得其自由、受其制約。對此,尤里烏斯·艾賓豪斯(Julius Ebbinghaus)解讀道:“平等的基本權利僅僅禁止,掌權者將人們偶然的自然差異當成一種對他們的自由從法則上加以限制的差異的法權根據。”(26)Julius Ebbinghaus, “Das Kantische System der Rechte des Menschen und Bürgers in seiner geschichtlichen und aktuellen Bedeutung”, Archiv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Vol.50, No.1,1964, S.44.公民之所以是平等的,是基于他們在法權法則下的身份平等。任何經驗性變動造成的差異(如出身、財富和才智等),都無法構成對這一平等身份的挑戰。這是公民平等的要義。
與之類似,“公民之獨立”也必須在法權法則的框架內,進而在與公民的自由與平等的銜接中得到理解。正如艾賓豪斯所言:“普遍的可能的獨立是對于自由與平等的正當聯合必需的第三者和為康德所要求的政治基本權利。”(27)Ibid., S.51.康德解釋道:“公民的獨立屬性,即不能把自己的生存與維持歸功于人民中另一個人的意決,而是歸功于其自己作為共同體成員的法權和力量,因而是公民的人格性,即在法權事務中不可為任何人所代理。”(VI314)換言之,公民的獨立首先意味著人格性的獨立,即在法權身份上不可依附于他人、不能為他人所代理。個人的生存和事功必須溯源至獨立的法權人格。我們不能也不應從自己與他人的依附性關系中理解自己的人格構成。很明顯,從普遍的法權法則中,每個人都獲致有邊界的行動自由,并與他人共享身份平等。如果“我”依據法權身份是自由的且與他人平等,這就意味著“我”既不依附于他人、也不讓他人受制于自己,同時“我”既不位列他人之上、也不置身他人之下。而這樣的“我”理應是獨-立的(selbst-st?ndig)。當“我”與他人處于自由平等的交互關系中時,“我”的人格必須持守在自身中,不可為他人所左右。進言之,既然“我”作為公民只服從普遍的法權法則,而該法則又乃我的理性本性所立,那么“我”只須聽從自身所立之法,僅依循此法立己之身。因此,“我”之獨立在于“我”與“法”的合一。由之,公民的獨立性也源于普遍的法權法則。
總之,在康德那里,公民所具的自由、平等和獨立作為先天原則從普遍的法權法則引申而來。由于這條法則來源于普遍意志,進而扎根于先驗自我與實踐自我所展示的普遍理性主體之中,因而對他公民概念的完整理解必須追溯至更本源的先驗哲學,不能拘囿于其政治哲學之內。在批判哲學的視域下,公民不僅是關于現實政治的經驗概念,而且是從純粹理性中生發的先驗概念,因為“公民之公”的根本在于純粹理性指示的普遍主體性。藉由此種普遍主體性,普遍意志對道德與法權的雙重立法才得到捍衛,公民的自由、平等和獨立則通過這種立法完成自身證成。倘若我們在康德哲學中能夠發現一條從先驗自我出發、經由表征實踐自我的普遍意志導向政治共同體的構建之路,這就說明公民概念從一開始在先驗哲學中就有其根據。這樣,他的公民觀念不但是共和國的立基之本,更是普世永久和平降臨的保證。一種“公民”的先驗闡釋既然在批判哲學中是順理成章之事,那么這種先天的公民身份既是現代國家的構成主體,也是世界整體價值的最終承擔者。從內在的道德動機邁向外在法權的公共生活,并介入國家與國際關系的建構,批判哲學在基底上是一貫的。對公民概念的先驗考察可以讓我們體認到這種一致性。所以,他的公民概念不單表述了一種政治法律意義上的資格,更展現了對共和國與大同世界的形而上學希望。不過,雖然康德公民概念蘊含遠大的理論指向,但他并未將現實的公民資格賦予所有人。他認為,擁有財產的積極公民有投票權,而無財產的消極公民沒有投票權。這說明了他公民觀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本質。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只有與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相適應,公民資格才轉變為普通人的真實權利。這一點是康德所忽視的,卻是我們必須堅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