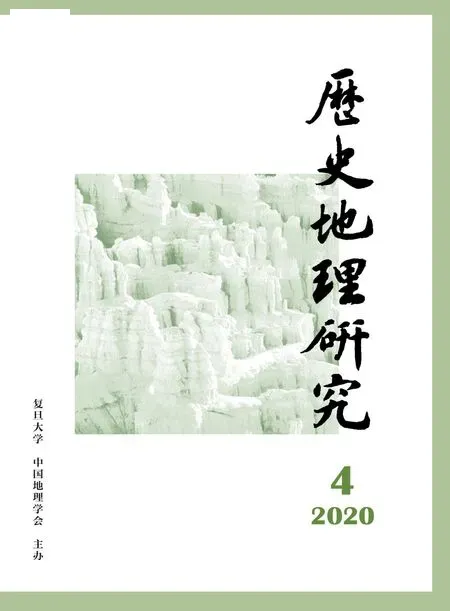心安做學問
——鄒逸麟先生走過的路及其叮囑
侯甬堅
(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陜西西安 710062)
鄒逸麟先生,1935年8月出生在上海。1952年高中畢業時,參加了考試,為山東大學歷史系錄取,這成為先生的一個人生轉折。到晚年做口述史時,他這樣看待他和親屬們走過的路:
我們鄒家,父輩都是白手起家的成功的工商業者,到我這一代,我與堂兄弟們都是選擇上大學,通過升學,成為有一技之長的專業人士,得以在社會上立足。其實這也正是我們父輩的心愿,他們希望積累的財富能為下一代提供最好的教育機會,彌補他們的人生缺憾。(1)鄒逸麟口述,林麗成撰稿: 《鄒逸麟口述歷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頁。
鄒先生的這一看法很有道理,因為人是跟著時代走的。1952—1956年他在山東大學歷史系學習,后來不斷努力,發展成為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學專業著名的教授、博士生導師,的確是擁有一技之長的專業人士。具體幫助和指導鄒先生的人,是他的老師譚其驤教授。《鄒逸麟口述歷史》(以下簡稱《口述歷史》)記述了鄒先生在北京第一次拜見譚先生的情景:
1957年1月7日,我和王文楚尋至譚先生宿舍,那是歷史所內的一間平房,他恰不在,我們就站在門口等著。譚其驤的名字我在山大歷史系讀書時就曾聽到過,系里的楊向奎、童書業教授,三十年代與譚其驤先生一起在禹貢學會工作過;但他們講課時從未談起歷史地理學,我也從未讀過譚其驤先生的文章,所以對歷史地理學科一無所知。……不一會兒,譚先生回來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譚其驤先生。(2)鄒逸麟口述,林麗成撰稿: 《鄒逸麟口述歷史》,第65頁。
在同日的譚其驤日記里,記有“今日未赴社,在寓準備講稿。終日來人不斷,計有王文楚、鄒逸麟、吳宜俊、胡厚宣、袁昌、國平、張德鈞、敬山八人……”(3)葛劍雄編: 《譚其驤日記·京華日記》,文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頁。一段文字。這一見一談重要極了,決定了半個月后鄒、王兩位年輕人跟隨譚先生回到上海的復旦大學,做起了編繪歷史地圖、搞歷史地理學研究工作的終生事業。1973年1月,大家編繪的這套地圖,上級正式認可為《中國歷史地圖集》,因其工作量極為浩繁,有的人很是受不了,鄒先生對此卻保持著清醒的認識,他是這樣來看待的:
……有人覺得歷史地理搞啥么子,一天到晚政區、州縣、沿革,頭也痛煞了;只有自己對這個學問真正有興趣、有想法,才會自愿吃這個苦頭的。任何學科都是這樣,只要自成學科,必定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否則誰會為它奮斗終生呢?
可惜這種能心安做研究的日子稍縱即逝,此后十幾年,都沒了機會。其實,只要看看國內其他學者的著作目錄,就可知道這是我國大多數學者的普遍現象……(4)鄒逸麟口述,林麗成撰稿: 《鄒逸麟口述歷史》,第75頁。
筆者手頭有一本吳宏岐、王京陽編輯的《史念海教授紀念文集》,內附一份《史念海先生著述目錄初編》就有鄒先生所說的這種情形。這部“著述目錄”的學術論文部分里,在1965年刊發的《陜西地區蠶桑事業盛衰的變遷》論文之后,是1975年刊登在《陜西師范大學學報》上的《秦始皇直道遺跡的探索》,中間相隔整整十年。(5)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編: 《史念海教授紀念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1頁。因為缺乏能心安做學問的日子,許多學者的著作目錄,就出現了較長時間沒有論文刊出的空白期,即鄒先生所說的“這是我國大多數學者的普遍現象”。此種情形在鄒先生既是刻骨銘心,故而記憶猶新。
接著,鄒先生又對照著自己的情況,繼續講到:
最最讓我感覺幸運的是,與同輩人相比,因為參與歷史地圖這個毛主席交辦的項目,在那政治生態極不正常的環境下,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我這輩子沒怎么荒廢時間,我這幾十年始終在搞歷史地理專業,這對一個人的成長是非常有利的。(6)鄒逸麟口述,林麗成撰稿: 《鄒逸麟口述歷史》,第76頁。
他細說道:“1966年8月學校開始搞‘文化大革命’,停止一切業務工作;1969年5月歷史地圖項目恢復運轉,我就被從奉賢農村叫回來了,僅僅荒廢了三年。”(7)鄒逸麟口述,林麗成撰稿: 《鄒逸麟口述歷史》,第77頁。尊敬的鄒先生啊,說出了他內心多么想從事的科研方面的實際工作的心聲!
鄒先生是很有書卷氣的高級知識分子,在《口述歷史》中,他多次回顧自己走過的路,極為誠懇地做出自我評價:
由此說來,人生也真是禍福相依。因為肅反運動中被沖擊留下的心理陰影,才使我決意離開了山大;然后輾轉回到上海,隨譚先生走入歷史地理學科領域。我這一生,沒有刻意去追求什么,只是認真做事、誠懇為人,完全是偶然的天賜良機,能讓我在這個領域俯首耕耘,并為之付出無悔的一生。(8)鄒逸麟口述,林麗成撰稿: 《鄒逸麟口述歷史》,第77頁。
如今的中國,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從事各類科研工作的人越來越多,怎樣才能做到“心安做學問”這一點?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體會好前人走過的路,學習前人給后人留下的教益。閱讀《口述歷史》下來,筆者思忖有這么三條值得注意: 一是要看遇到的是什么時代,二是要看自己的具體工作環境,三是要看自己是什么樣的心態。
對于第三條,鄒先生有許多真切的叮囑。
第一,對待學問,只要你真正下功夫,就必有成果。鄒先生愛讀文學作品,他記得電影《亂世佳人》的末尾,郝思嘉想起她父親對她說的一句話:“土地是永遠不會辜負你的!”鄒先生說:“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我認為做學問也是這樣,研究機會難得,用心做一定會有成果的,學問也是不會辜負你的。”
第二,熱愛生活,諸如愛國愛家,愛妻愛子,喜愛閱讀,幫助學生,等等皆是。生活里的精神世界豐富了,對于學問上的追求就會有更大的勁頭。
第三,搞學問一定要有興趣,不要湊熱鬧。總是跟風,流行什么做什么,這是不行的。再就是現在這個時代的紛擾和誘惑太多,各種名利的東西都在散發著最大的影響,需要學人們去辨別。做不到心無旁騖這一點,就可能荒廢時間,難于自善其身。如果相反,年輕人能孜孜不倦地研究一個東西,進入到物我兩忘的境地,最后他一定是有成果的。
我們知道,在鄒先生的身旁,有一種精神支撐,那就是譚其驤先生的師恩和榜樣力量。在2011年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上,鄒先生自報以“譚先生的一名老學生”身份上臺發言的情景,給予筆者的印象極深。1992年譚先生逝世時,鄒先生情不自禁地寫道:“從那時起(指1957年1月)到今天已經整整三十五年了。1978年前的二十多年里,他幾乎天天上班,與我們學生朝夕相處,我們在工作中遇到什么問題,隨時向他請教,他總是不厭其煩地一一作答,這是我們在業務上長進最快的時候。1978年以后他因病不能每天來上班了,但對我們的指導和幫助卻從未停止過。以我個人而言,不論參加集體科研項目,還是專題研究,莫不是在他指點下進行的。我雖然沒有聽過他開設的大學課程,也沒有當過他的研究生,但我今天算能在歷史地理領域做一點工作,離不開譚師對我指導和幫助,數十年的培育之恩使我永生難忘。”(9)鄒逸麟: 《追念恩師譚其驤教授》,《歷史地理》第1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1頁。鄒先生的回想、感念、自謙、承恩諸種心情,皆在其中。
鄒先生當然很了解自己的老師,他曾寫道:“譚師為人耿直,敢說真話,在學術上堅持真理,實事求是。對學術界某些弄虛作假,見風使舵,浮夸不實的學風,深惡痛絕。他常常教導我們做學問在于求真,不求聞達。并身體力行,成為我們的楷模。”(10)鄒逸麟: 《追念恩師譚其驤教授》,《歷史地理》第1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1頁。譚先生師生長此以往,嚴格要求自己,在學界形成了嚴謹的譚門學風。鄒先生也一直強調,搞學問不能太功利,工作來了,首先考慮它對自己有什么好處,有好處干,沒好處不干,這是不行的。
對于自己的老師,鄒先生也是極為真誠地表示過心跡。他說:
從1957年初跟隨譚其驤先生治學,至1992年他離去,三十五年程門立雪、耳濡目染,先生的為人、治學之道已融入我的謀生為學之途,此生受益非“感恩”一詞所能表達。譚先生為學一甲子,桃李滿天下,我在他的學生中絕不是最具才華的,也不是最有成績的,但在共同經歷那些年的疾風驟雨后,我認為自己是能與他推心置腹、風雨同舟,從不違背他的意愿的弟子。(11)鄒逸麟口述,林麗成撰稿: 《鄒逸麟口述歷史》,第107頁。
1982—1996年,鄒先生先后擔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長、所長,2000—2004年擔任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2000—2010年擔任《歷史地理》輯刊主編,所以,在鄒先生心里又經常在盤衡著一個學科、一個學術研究機構如何發展的問題。1998年,撰寫了《我與中國歷史地理學》一文,在這篇文章里他回顧四十余年科研工作的經歷,和大家交談了四點治學體會,即:
1. 加強基礎研究,開展大型集體科研項目,是發展學科、培養接班人的重要途徑。
2. 為學科建設添磚加瓦,是年輕科學工作者成長的重要途徑。
3. 小題大做,墨跡戰術。(12)鄒先生解釋“墨跡戰術”的意思是: 學者“從小問題做起,可以往深處著手,同時也可由此題像墨跡一樣劃開去,逐步擴大,一步一個腳印,日漸形成一個方面”。參見鄒逸麟: 《我與中國歷史地理學》,《椿廬史地論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88頁。
4. 多讀書,勤思考,力求有所創新,力求有所發明。(13)鄒逸麟: 《我與中國歷史地理學》,張世林編: 《學林春秋》三集下冊,朝華出版社2000年版,轉引自鄒逸麟: 《椿廬史地論稿》,第580—592頁。
做學問,做專業研究,這是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事情,是可以為國家做的具有專長的該做的事情。鄒先生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專業典型,言行上符合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科學家的優勢不僅靠智力,更主要的是專注和勤奮,經過長期探索而在某個領域形成優勢。要鼓勵科技工作者專注于自己的科研事業,勤奮鉆研,不慕虛榮,不計名利”。上述四條治學體會,乃是一位身經百戰的歷史地理學宿將,面對自己鐘愛的學科和事業而發出的,這些話對個人尤其是青年學者而言是指點,對各所研究機構而言是建言,目標皆指向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延續及發展。鄒先生自報“是譚先生的一名老學生”,在與譚先生終生為歷史地理學科做出奉獻的事跡相比擬之后(14)參見侯甬堅: 《歷史地理實干家譚其驤先生》,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編: 《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50頁。,我們完全可以說,鄒先生在復旦大學繼承了譚先生開辟的學術事業,鄒先生真是譚先生培養的一名好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