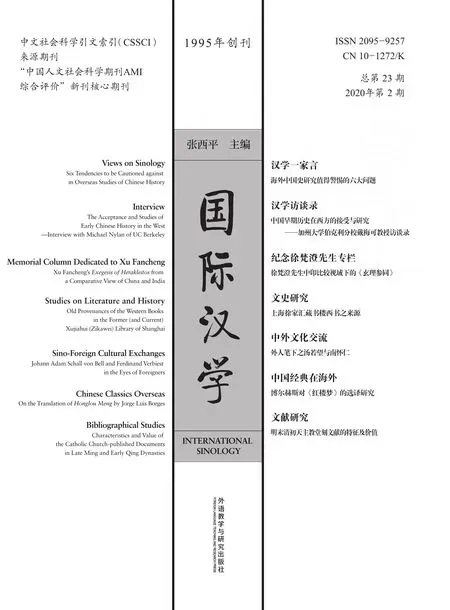明清“天學”之辯與基督教神名的中國化*
紀建勛
一、晚明大變局、早期全球化與早期“上帝全球化”
明末清初是一個天崩地解的時代,不僅僅是因為改朝換代,作為外族與“蠻夷”的滿人入主中原,成為華夏帝國新的領導者和主人;更因為晚明還是一個“大變局”的時代,從16 世紀開始,西歐文明開始全面與古老的東方文明交接并互相影響,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傳教士先后梯航東來,受其影響,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儒家基督徒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進而言之,始于15 世紀一直到17 世紀的“大航海時代”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把世界上的幾大代表性文明聯通在一起,國人再也不能以“中央之國”與“天下”“世界的中心”而自居。15 世紀到17 世紀中葉的這段歷史,還是“世界歷史大變局的開端”(1)李伯重:《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北京:三聯書店,2017 年,第25—29 頁。,自此歐洲用了250 年實現了工業化,這深刻地影響了世界和人類文明的走向。因此,如果我們把上述幾種情形串聯起來,不難看出,明末清初的這場中西文化交流實際上還是人類早期全球化時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一般認為這種早期全球化是今天整個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前夜,明末清初的中西交流作為早期全球化時代的重要一環,其主要特征還是早期經濟上的全球化趨向。換言之,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火槍加賬簿”,是推動東亞世界乃至整個人類社會從傳統社會邁向近代現代化社會發展的動力。(2)同上,第397 頁。這也進一步啟發著我們把這場“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探究由晚清上推至晚明。但我們如果仔細比較16 世紀以來西方文明在華傳播的兩次浪潮——相較于清末民初華夏文明面對西方文明的全面弱勢與被動,明末清初東西方兩大文明基本上還是處在一個平等對話的交流層面——會進而發現明末清初這段時期實際上還是一個基督宗教的全球化時代,歐洲的基督教與世界各地的文明尤其是與東方的儒教進行著一場影響深遠的“上帝之賭”。從一定意義上來講,這段時期也是一個“上帝全球化”時代。
在早期全球化時代,火槍與賬簿的威力固然不容懷疑,只是我們還應該看到當時中西雙方處在國力上勢均力敵的平等地位,這與今天主要由西方主導的以經濟為中心的全球化時代有質的不同。因此,除掉惡行滿滿的火槍與血跡斑斑的賬簿,精神上的狩獵與社會傳統信仰以及宗教間的對話,也是早期全球化時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面向。
今天的國人,一提到“上帝”,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基督教的至上神“GOD”,而不會是我們先秦典籍“四書五經”中在在皆是的“上帝”;(1)紀建勛:《漢語神學的濫觴:利瑪竇的“帝天說”與上帝存在的證明》,《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2014 年第1 期,第47—74 頁。同樣,一提到“天主”,國人首先想到的必然還是基督教的至上神“GOD”,而不會是《史記·封禪書》里作為儒家祭祀源流的“八神”之一,也不會是佛教里被稱為“忉利天主”的帝釋天“釋提桓因”,更不會是道教里的“真人”。(2)紀建勛:《明末“天主”考》,《世界宗教研究》2019 年第2 期,第134—150 頁。即便原本在中文語境里含義更為寬泛的“神”也未能幸免。實際上,在今天最為廣泛接受的中文和合版《圣經》中,“GOD”的兩個最流行的譯名就是“上帝”和“神”。這說明“上帝”“天主”“神”等這些代表著傳統中國社會宗教核心理念的關鍵詞匯在明末發生了含義嬗變。晚明中西上帝觀的相遇,作為儒家文明之根的帝天崇拜與西方基督教系統神學中的上帝論在晚明進行著沖撞與融合。“中國禮儀之爭”正是兩種不同范式的社會宗教在核心理念與傳統儀軌兩方面沖突的集中體現。“禮儀之爭”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或許是失敗了,“上帝之賭”卻意味著基督教在地化,尤其是基督教神名中國化的成功,這是漢語神學的濫觴。
一般認為,基督教于清前中期在中國的傳播被強行終止,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又一次失敗了。實際上,比較16 世紀以來西方文明在華傳播的兩次浪潮,明末清初所對應的第一次浪潮其主要特征固然有早期經濟全球化方面所帶來的深遠影響,但卻不足以完全覆蓋這次中西交流的大潮所席卷而起的全部浪涌。伴隨著早期全球化,西方文明在華傳播的第一次浪潮,至少還有一個主要面向是基督教在華的廣泛傳播及其與華夏文明的互動。從此角度而言,早期全球化的主要特征還不全部都是早期經濟的全球化,早期全球化還是早期基督教的全球化,是基督教的上帝論與儒家的帝天崇拜的相遇,是基督教中國化的最初階段。
在晚明大變局中,我國固然未能抓住早期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與西歐一起攜手走向近代化,然而也正是基督教與中國傳統社會宗教在此過程中的遭逢,經由中西上帝觀的沖撞,讓今天的我們有機會透過禮儀之爭的巨大差異與沖突,看清中國傳統社會宗教“雙向度”的性質與特點。(3)紀建勛:《“中國禮儀之爭”的緣起和中西學統的關系》,《世界歷史》2019 年第1 期,第118—121 頁。儒家文明的這種“雙向度”,完全不同于“單向度”的基督教社會,這對于今天我們正視、調試與振興儒家文明精粹,復興作為儒家文明之根的帝天崇拜,回應當今社會飛速發展所帶給國人精神與信仰上的嚴重危機,與西方文明更好對話,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與啟示價值。
1872 年李鴻章上《籌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說:“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4)(清)李鴻章:《籌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載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五卷奏議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107 頁。與李鴻章憂國憂民的呼召相差一百年之后的1973 年,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在其遺著《人類與大地母親》手稿中指出:
由西方商人和帝國的創建者們掀起的層層浪潮所帶來的西方文明,是形態各異的。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為代表的第一個浪潮,力圖完整地輸出西方文明,包括他們本民族的宗教。而在任何文明中,本民族的宗教都是該文明整體的核心。所有具有力量的非西歐民族都成功地抵抗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這一企圖。所以,荷蘭人—法國人—英國人掀起的,在不信基督的異教地區傳播西歐文明的第二個浪潮,輸出的僅是經過篩選的西歐文明。荷蘭和英國的私商和官方都對傳教士的活動皺眉蹙額、表示不滿。從17 世紀開始在人類文明世界中滲透的、這種刪節了的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宗教,而是技術。其中,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是為戰爭服務的技術。(1)阿諾德·湯因比著,徐波譯:《人類與大地母親:一部敘事體世界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476 頁。
李鴻章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就清末民初中西交往的被動形勢而言,在經歷了充滿屈辱與劫難的鴉片戰爭后,一般認為中國社會的近代史由此開始了。而回望明末清初的中西交流,晚明的這場歷史大變局實際上是中國社會近代化的萌芽。此“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其肇端實在不僅僅起于1840 年的鴉片戰爭,而是從1583 年利瑪竇與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1543—1607)進入中國就開始了。
始于16 世紀的這場中西“上帝之賭”,是因西方基督教在本土的地位與影響受到挑戰,隨著大航海時代的開啟,傳教士們轉而尋求海外的市場,開啟了基督教這一宗教信仰方式的全球化。以鴉片戰爭為分界點,伴隨著火槍與賬簿,19 世紀中期西方文明在華傳播的第二次浪潮中,基督教反而淪落為西方文明的幫兇與附庸。技術與經濟全球化漸次成為中西交流的主旋律,科學技術登堂入室,正式取代基督教文化,一變成為西方文明的代名詞,開始全面凌駕于華夏文明之上。從此以后,包含中國在內的全球范圍,基督教不再是世界的主人,它漸次從中央退隱到邊緣。今天的地球,各國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全球化時代早已真正到來,然而宗教問題卻又變得日益尖銳與突出,這向世界提出了新的嚴峻挑戰。新時代下我們應對宗教危機的一個重要參考,就是回到晚明大變局所帶來的這場圍繞著各路“天學”所開展的“上帝之賭”中,去尋找更多經驗教訓上的有益借鑒。
二、明清“天學”之辯
何謂“天學”?“天學”這一術語容易引起人們的誤解,其定義的內涵和外延并不是特別清楚。因此,我們首先要把“天學”的定義加以厘清。在明末,存在各種“天學”說法,可以說,基本上當時各路主流思想都突出談論“天”概念,這是明末清初學術的一個特點。在當時,不僅天主教主張“天學”,主流儒學強調“事天敬天”,甚至佛教大德也標舉“天說”。“天學”作為明清中西交流史研究的關鍵詞,在明末社會存在著各種“天學”,有廣義與狹義之分,有中西之別,也有儒耶釋三家之論。因為天主教的傳入,儒釋耶諸家圍繞“天”概念和上帝觀發生了本體論層面上的砥礪,其影響深遠且意義重大。 “天學”作為關鍵詞足以代表明清中西交流史研究的各個面向,涵蓋了此領域宗教、歷史、文學、語言、思想、科技史等各個層面的研究進路。
“天學”即“天主教”,此可謂“天學”之狹義。耶穌會士和儒家基督徒以為儒家的“事天之學”同于天主教,故用“天學”來稱呼“天主教”,這個層面上的用法,正如同用“天學”來表示“神學”,用“儒學”來稱呼“儒家”“儒教”。
天學者,唐稱景教。自貞觀九年入中國,歷千載矣。其學刻苦昭事,絕財色意,頗與俗情相戾。要于知天事天,不詭六經之旨。稽古五帝三王,施今愚夫愚婦,性所固然,所謂最初最真最廣之教,圣人復起不易也。(2)(明)李之藻:《刻〈天學初函〉題辭》,載吳相湘編《天學初函》,臺北:學生書局,1965 年,第1—2 頁。
廬居靈竺間,岐陽同志張庚虞惠寄唐碑一幅,曰:“邇者長安中掘地所得,名曰:《景教流行中國頌》。此教未之前聞,其即西泰氏所傳天學乎?”余讀之良然。(3)同上,第77 頁。
“天學”者,“唐稱景教”,今稱為天主教,“所謂最初最真最廣之教”,也即“西泰氏所傳天學”(按:即神學,西泰是利瑪竇的字),“天學”即“神學”,“神學”即“天主教”。此一層意思,可謂明末中西交流語境下“天學”之狹義概念。
“天學”作為明末中西交流的出發點,即祭天與儒家事天敬天之學。“天”在先秦時代具有比較濃重的意志主宰內涵,相應的敬天儀式,自遠古便已經開始了。作為古代敬天儀式的郊祭,《禮記·中庸》中解釋說“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祭天的儀式一向為自稱天子的帝王所專用,他人不得僭越,而敬“天”就是敬“上帝”(1)關于上帝與天崇拜的商周之變,請參見傅佩榮:《儒道天論發微》,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第1—36 頁。,敬天人人有份。不過,與祭天的儀式一直延續到清代帝制終結不同,“天”的含蘊卻發生著緩慢而深刻的變化。由先秦的意志主宰神,經漢儒特別是王充以及魏晉名教與自然的多重滌蕩,至宋明理學興,“天”被進一步條理化、物質化,自然之理與人倫之理統屬為“天理”,“天”的意志主宰含蘊愈發淡漠不彰了。
自晚明至清初,除了皇家的祭天大典之外,尚有民間的兩股敬天思潮更值得我們重視。這段時期“天”的含蘊又出現了人格、意志化的傾向,這時的中國出現了一種與宋明理學不同的“敬天”的思潮。此一思潮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天主教徒的“敬天”,二是非天主教徒的“敬天”。具體的呈現方式雖有差異,但其實質則有內在相通之處:都自覺將先秦典籍中的“天”予以人格意志化的重釋,這是一種因為相信天的意志主宰品質而形成的思潮。它在各地傳播流衍,催生出了各種各樣的“他律”色彩的道德實踐形式;敬天儀式的承擔者也不再是帝王,而是各種身份的士大夫。(2)劉耘華:《依“天”立義:許三禮的敬天思想再探》,《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2009 年第1 期,第115—118 頁。所以,在明末從“天學”概念之狹義角度而論,它往往意味著儒家事天敬天之學與天主教神學的互動。
儒耶“天學”互補互鏡。明末儒家基督徒楊廷筠(1562—1627 ,字仲堅,號淇園,浙江仁和人,1592 年進士)曾任監察御史,早年習“王學”,出入儒釋,是杭州著名居士,后又辟佛入耶,洗名彌格(Michael),故又號彌格子。楊氏戮力于儒耶之間的會通,曾經提出:
儒者本天,故知天、事天、畏天、敬天,皆中華先圣之學也。《詩》《書》所稱,炳如日月,可考鏡已。自秦以來,天之尊始分;漢以后,天之尊始屈。千六百年天學幾晦,而無有能明其不然者。(3)(明)楊廷筠:《刻〈西學凡〉序》,載吳相湘編《天學初函》,第9—10 頁。
楊廷筠筆下的“天學”就是指“儒者本天,故知天、事天、畏天、敬天,皆中華先圣之學也”,所謂“千六百年天學幾晦”,就是指宋明理學把“理”“氣”“心”“性”等概念作為儒家本質,導致“天”的意志主宰神含蘊被“屈”不顯。他們找到的具體補救方法就是“帝天說”。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把先秦典籍中的“天”“上帝”與天主教的惟一主宰“陡斯”(拉丁文Deus)等同起來,區分先儒和后儒,認為自秦火以來,道統不繼,正需要天主之學來“明其不然”。
推崇“漢學”為明末學界風氣,利瑪竇通過《天主實義》證明上帝的存在,宣稱:“神父們一直在強調的是天主教的法律與生來的良知完全相合。他們堅持中國古代學者所說的良知與天主教的道理非常相近,這種理論早在偶像出現之前就有了。他們又說,他們并非廢除自然律,而是補充自然律所缺少的,也就是天主所啟示的超自然的法律。”(4)利瑪竇著,劉俊馀、王玉川譯:《利瑪竇中國傳教史》,臺北:光啟出版社,1986 年,第137 頁。楊廷筠繼續傳達此觀點,“西來諸賢,猶漢前儒者之風”,“惟我西方天學,乃始一切掃除,可與吾儒相輔而行” 。(5)(明)楊廷筠:《代疑續篇》,載鐘鳴旦、杜鼎克、蒙曦合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6 冊,臺北:利氏學社,2009 年,“信獨章”第430 頁、“別似章”第454 頁。明末另一天主教柱石徐光啟更提出天主教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使晚明的“人心世道,必漸次改觀”,長期以往,便可“興化致理”,“出唐虞三代之上”,“永萬年福祉,貽萬世乂安”。(6)(明)徐光啟:《辨學章疏》,載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431—436 頁。宋儒用關于“理氣” “心性”的討論來振興儒學,明里暗里借鑒佛教義理,宋明理學漸次成為官學;在明末,以顧炎武、黃宗羲為代表的不少士人深感心學“游談無根”,空談心性,可謂誤人誤國,最關鍵的是不能夠“通經致用”,遂提倡“實學”。這其中,“通經”的一方面主要是經由清代的乾嘉學派完成的,而“致用”的一方面,葉適、陳亮的“事功之學”和朱、陸“道學”之爭姑置不論,另外很重要的一個向度與明清來華的西學有關系。在明末,信奉天主教的儒家基督徒們一個普遍的主張就是認為天主教可以“救正佛法”,扭轉“宋學”“漢學”的悖謬與頹勢,接續與復興自漢代以來一直不彰的“古儒”。
傳教士認為天主教神學,和古代圣人講的“知天、事天、畏天、敬天”之“天學”是一樣的道理,儒學與天主教神學足可以相互發明。這種發明,被受過很好基督教人文主義教育又熟讀“四書五經”的耶穌會士用來最為嫻熟。明末天主教徒談“天”,強調其至高無上,推證上帝的存在,其實質是用吾儒“事天之學”與“西方天學”互相發明。(1)關于明末中西上帝觀的比較研究,參見紀建勛:《明末清初天主(上帝)存在證明的“良能說”——以利瑪竇對孟子思想和奧古斯丁神學的運用為中心》,《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4 年第1 期,第120—125 頁;《明末清初天主(上帝)存在的“道德論證”——以利瑪竇的“良能說”及其對孟子思想的運用為中心》,《基督教文化學刊》總第32 輯,2014 年,第22—42 頁;《誰的“上帝之賭”? ——帕斯卡爾與中國》,《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4 期,第81—92 頁。這一做法與當時耶穌會士和儒家基督徒流行將天主教最高神“Deus”稱呼為頗具儒家倫理色彩的“大父母”(2)有關“大父母”神名研究,參見紀建勛:《明末天主教“Deus”之“大父母”說法考詮》,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2012 年,第103—140 頁。一樣,兩者同為漢語神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同為耶穌會士借中西“天學”的互鏡互釋來推證上帝存在的典型例子。
明末儒釋耶三家圍繞“天學”展開思想論爭。天主教反對偶像崇拜和多神,對儒釋道三家采取聯合儒家、嚴厲批駁佛教和道教的策略。與之相應,佛教為維護自身社會地位,也是采取聯合儒家、反對天主教的態度。這其中,雙方爭論的一個焦點就是“天學”,三家都提出了基于各自立場的“天學”。以清初的順治皇帝為例,很多人關注順治的信仰歸屬問題,并以此反思明末清初的佛耶論爭,在這場論爭中基督教落于下風。且自清初開始,基督教就一直在禁教的邊緣徘徊,政治環境與社會輿論對他們不利。
傳教士對佛教的攻擊,于學理于策略是否得宜,在此不予討論。而儒耶釋三方就“天學”之主戰場展開激烈拉鋸戰,則是事實,這也說明利瑪竇附會先儒并提出“帝天說”,在當時引起了各方主流思想的交鋒。蓮池大師云棲祩宏(浙江仁和人,字佛慧,號蓮池,1533—1615,晚明最聲名卓著的佛學大師)就挺身而出,首先提出了佛教“天學”,進而認同儒家“天說”以表明自己的立場:
彼雖崇事天主,而天之說實所為諳。按經以證,彼所稱天主者,忉利天王一四天下,三十三天之主也。此一四天下,從一數之而至于千,名小千世界,則有千天主矣。又從一小千數之,而復至于千,名中千世界,則有百萬天主矣。又從一中千數之,而復至于千,名大千世界,則有萬億天主矣。統此三千大千世界者,大梵天王是也。彼所稱最尊無上之天主,梵天視之,略似周天子視千八百諸侯也。彼所知者萬億天主中之一耳。余欲界諸天,皆所未知也。又上而色界諸天,又上而無色界諸天,皆所未知也。又言天主者,無形無色無聲,則所謂天者理而已,何以御臣民、施政令、行賞罰乎?彼雖聰慧,未讀佛經,何怪乎立言之舛也!(3)(明)祩宏:《天說一》,載夏瑰琦編《圣朝破邪集》,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 年,卷七第320 頁。
祩宏以佛教的宇宙觀為武器,認為天主教所謂“天主”只不過是佛教欲界中一天,對于色界和無色界諸天則“皆所未知”,傳教士對于佛經“實所未諳”。他認為利瑪竇從古經中推證上帝的方法雖然“聰慧”,然而其“未讀佛經”,難免“立言之舛”。從翻譯角度計,佛教之天主與天主教之至上神固然不能簡單比較,至少在這里,體現出佛教界已經意識到利瑪竇補儒易佛進而超儒的證明策略。再來看祩宏如何總結儒家的“天學”:
復次,南郊以祀上帝,王制也。曰“欽若昊天”,曰“欽崇天道”,曰“昭祀上帝”,曰“上帝臨汝”。二帝三王,所以憲天而立極者也。曰“知天”,曰“畏天”,曰“則天”,曰“富貴在天”,曰“知我其天”,曰“天生德于予”,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是遵王制,集千圣之成者,夫子也。曰“畏天”,曰“樂天”,曰“知天”,曰“事天”,亞夫子而圣者,孟子也。天之說,何所不足而俟彼之為新說也。(1)(明)祩宏:《天說三》,載夏瑰琦編《圣朝破邪集》,卷七第322 頁。
這說明當耶穌會士的“天說”流行江南時,杭州地區佛教徒認為儒家也有“天說”,并且用其來說明西學之謬。從帝王的祭天到二帝三王再到孔、孟之“天”,祩宏對儒家“天學”的精煉綜括相當到位,他敏銳提出儒家“天之說,何所不足而俟彼之為新說也”,自有相當理由。
被斷定為利瑪竇所做的《復蓮池大和尚〈竹窗天說〉四端》中則說:“武林沙門作《竹窗三筆》,皆佛氏語也,于中《天說》四條,頗論吾天教中常言之理。”(2)利瑪竇:《復蓮池大和尚〈竹窗天說〉四端》,載朱維錚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664 頁。補儒易佛的策略從根本上夯實了基督教“天學”立足中國的根基,基督教得以從這場儒佛耶三教圍繞“天學”正統之爭的大論戰中成功突圍。惟當時的佛教人士對耶穌會特別是利瑪竇證明天主的策略并沒有深入體認,因為“利瑪竇規矩”特別是“帝天說”的出發點正是認為先秦主宰與人格化的“上帝”在宋明理學那里被隱晦不彰,天主教東來,就是為了與先秦“天學”相互發明,其目的是為了證明天主教至上神的存在在中國古已有之,這是一種漢語神學,在中國文明的傳統之中發現神學。而明末的佛教界對于天主教駁“近儒”即宋明理學、依附“古儒”即先秦典籍的策略與做法并不認可甚至視而不見。
“天學”即“西學”,此可謂“天學”之廣義。《天學初函》是由李之藻所編、集明末天主教著述之大成的中國第一套基督教叢書,《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說:
《天學初函》,五十二卷……書凡十九種,分理、器二編。理編九種:曰《西學凡》一卷;曰《畸人十論》二卷;曰《交友論》一卷;曰《二十五言》一卷;曰《天主實義》二卷;曰《辯學遺牘》一卷;曰《七克》七卷;曰《靈言蠡勺》二卷;曰《職方外紀》五卷。器編十種:曰《泰西水法》六卷;曰《渾蓋通憲圖說》二卷;曰《幾何原本》六卷;曰《表度說》一卷;曰《天問略》一卷;曰《簡平儀說》一卷;曰《同文算指前編》二卷,《通編》八卷;曰《圓容較義》一卷;曰《測量法義》一卷,《測量異同》一卷;曰《勾股義》一卷。(3)(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卷一百三十四子部四十四雜家類存目十一,第3419—3420 頁。
很明顯,所謂“天學初函”之“天學”,理編與器編各十種(4)按:《四庫全書總目》未將《西學凡》所附的《唐景教碑》列入,故云“理編九種”,據李之藻《刻〈天學初函〉題辭》云“理器二編:編各十種” 。,實為包含傳教士所譯著的人文與自然兩大方面科學的“西學初函”。“天學”也即“西學”。
對于“天學”此一層面的含義,《天學初函》理編所收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著《西學凡》體現得更加清楚。《西學凡》是一部簡單介紹文藝復興以后西學規模的小冊子,內中將西學科目設為“六科”:
六科:一為文科,謂之勒鐸理加(Rethorica);一謂理科,謂之斐錄所費亞(Philosophia);一為醫科,謂之默第濟亞(Medcina);一為法科,謂之勒義斯(Leges);一為教科,謂之加諾搦斯(Canones);一為道科,謂之陡祿日亞(Theologia)。惟武不另設科,小者取之材官智勇,大者世胄賢豪。(5)艾儒略:《西學凡》,載吳相湘主編《天學初函》,第27—28 頁。
楊廷筠《刻〈西學凡〉序》在強調西學規模可觀,乃“實修實用”之學的同時,還為我們分隔出另一層面上的“天學”概念。此一層意思,可謂明末中西交流語境下“天學”之廣義概念:由“人學”到“天學”,由“性學”到“超性學”。
以余所聞,又閱多人多載,將若畫一所稱六科經籍,約略七千余部,業已航海而來,具在可譯。此豈蔡諳、玄奘諸人近采印度諸國寂寂數簡所可當之者乎?而其《凡》則艾子述以華言,友人熊子士旗、袁子升聞、許子胥臣為授梓,以廣異聞。夫此其于天學也,猶未諳象緯而先持寸軌以求夙莫者也。……獨竊悲諸誦法“孔子而問禮問官”者之鮮,失其所自有之天學,而以為此利氏西來之學也。(1)《刻〈西學凡〉序》,第15—20 頁。
很顯然,精通佛學的“天主教儒者”楊廷筠更加重視心性層面與神學的會通,認為西學相較于“利氏西來之學”尚有高下之分,這里的“利氏西來之學”也即“天學”,實際上就是天主教神學。
李祖白(明末清初天文學家、天主教徒,供職于欽天監)《天學傳概》除了說“天學,天主教學也”(2)李祖白:《天學傳概》,載吳相湘主編《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臺北:學生書局,1966 年,第1055 頁。,對“天學”即“神學”含義予以說明外,還說西書“有經,有史,有超形性學,有形性學,有修學,有天文學。板藏京師、江南、浙、閩、秦、晉各堂,且總計載來圖書七千余部”(3)同上,第1067 頁。。“超形性學”指神學,“形性學”指物理學,這大致可以與楊廷筠對西學和天學的劃分相對應。
利類思(Lodovico Buglio,1606—1682)《〈超 性學要〉自序》提出“天學”與“人學”之說:
大西之學,凡六科,惟道科為最貴且要。蓋諸科人學而道科天學也。以彼較此,猶飛螢之于太陽,萬不及矣。學者徒工人學不精天學,則無以明萬有之始終與人類之本向生死之大事。雖美文章、徹義理、諳度數、審事宜,其學總為無根,何能滿適人心止于當然之至善享內外之真福乎?故非人學,天學無以先資;非天學,人學無歸宿。必也兩學先后連貫,乃為有成也。天學,西文曰陡祿日亞,云陡指天主本稱陡斯,云祿日亞,指探究天主事理也。(4)利類思:《〈超性學要〉自序》,載鐘鳴旦、杜鼎克、蒙曦合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2 冊,第543—544 頁。
天學即神學,人學包括上已述及的文科(修辭學)、理科(哲學)、醫科(醫學)、法科(法學)、教科(法典,指天主教會法)。(5)關于耶穌會的課程設計及耶穌會士的知識架構的分析,可以參見劉耘華:《詮釋的圓環——明末清初傳教士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及其本土回應》,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36—41 頁。“天學”關乎“萬有之始終”與“生死之大事”,其以“人學”為先資,人之教育與修行,強調兩學先后的貫通,方能有所成就。這里,“天學”與“人學”是相對的概念,傅泛際(Francisco Furtado, 1589—1653)的《寰有詮》則將“天學”與“性學”對舉。(6)傅泛際:《寰有詮》,載任繼愈、薄樹人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天文卷》第8 分冊,鄭州:大象出版社,1993 年,卷一第469、471 頁,卷二第486 頁。
并且我們不要忘記,耶穌會在華傳教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傳教士向士大夫介紹天主教神學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利瑪竇的《天主實義》,之前名為《天學實義》,對于天主教至上神,利瑪竇一向稱為“上帝”,將探討上帝的學問稱為“天學”,后因“譯名之爭”才于1601 年在北京新刻本中改為《天主實義》,以區別于儒家的“天”。利瑪竇和楊廷筠等人以“天學”代指“神學”,正說明了他們的本意是希望通過儒家的“天”與西方的神學共通共享來互相發明。
“天學”即中西“天文歷算之學”。“天文”一詞在古代中國,常與“人文”“地理”對舉,意指天象,即各種天體交錯運行而在天空所呈現之景象;又漸據此引申出第二義,用其代指仰觀天象以占知人事吉兇的學問,即星占學。乃至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近現代意義上的天文學在古代中國并不存在。“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兇之象,圣王所以參政也”,《漢書·藝文志》中的這段對天文性質的看法,正代表了此后兩千年中國社會的普遍觀點。有論者論及“古代中國天學”,認為之所以不適用“天文學”一詞,固然“是為了避免造成概念的混淆”,更重要的是,“古代中國天學無論就性質還是就功能而言,都與現代意義上的天文學迥然不同”。通過討論中國古代對天文現象的觀察和解釋,指出中國“天學”的真原是:中國古代天學具有重要的政治與社會功能,古人通過星占以“通天”,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決策咨詢甚至決策依據,為王權或皇權服務。(1)江曉原:《天學真原》,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1—4、106—108 頁。因此,“天學”與“天文學”兩個概念在古代中國有明顯的區別。
古代中國的天文學實是我們今天所說之星占學與選擇術,在當時具有“通天”“通神”的重大作用和很強的政治意義和社會功能;在明末,因為歷法改革的需要,使中西天文學的會通成為可能。一般來講,耶穌會士和儒家基督徒所說“天學”大都指“西學”“神學”或“天主教”,而教外士大夫所涉“天學”多是指“天文歷算之學”,也即“天文學”。但是中國古代天文學強烈的政治性和人文色彩,以及教皇視星占及選擇術為迷信的圣諭,使傳教士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典型研究如江曉原的《天學真原》與黃一農的《社會天文學史十講》(2)黃一農:《社會天文學史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著力于探析傳統天文學與社會尤其是政治間的密切互動,既有趣且深具開拓性。
學界也注意到“天學”說法常常一詞多義或多詞一義,且在具體的使用中常常互相交叉疊加。從以上種種“天學”的交叉地帶不難尋覓與勾勒出點線面的縱橫交織,來深入討論明末儒釋耶諸家借“天學”展開的本體論層面上的較深砥礪,以及經由這一縱切面來深入觀察與體認明末天主教如何借“天學”來與中國社會進行互動。
“天學”即“實學”。我們看到,因為古代天文的豐富人文精神與政治上的特殊通天性質,又兼明末歷法改革之需,傳教士挾西方“天文學”以傳“神學”,兩方面因素致使“天學”與“天文學”兩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發生了頗為復雜的交叉混融。教內士大夫以“天學”為神學,教外士大夫以“天學”指西方天算之學,不管是“神學”還是“天文學”,“天學”在當時都被看成“實學”。
對于“實學”說法,明末的學者,有稱“博學”為“實學”,有稱“天文歷算”為“實學”,也有稱“考據”為“實學”。儒家把這種修身養性的學問,當作實實在在的學問。值得注意的是,明末的儒家天主教徒把西方神學也稱為“實學”。16 世紀、17 世紀處在歐洲“文藝復興”后期,神學仍然還是包容一切的百科學問。教會里的神學家通過天文、物理等實證學說,嘗試建立各種數理和精神概念,還努力證明上帝的存在。故明末學者認為天主教神學和“空論心性”“游談無根”的“性理之學”“王學”不同,西方由“人學”到“天學”,由“性學”到“超性學”的知識體系與學科系統是“實學”。同為“實學”,這正是儒家基督徒認為“神學”可以與“儒學”互相發明的地方。
在明末,經由熱烈的宗教實踐,中西雙方在“天學”與“超性學”所對應的儒家事天敬天之學與基督教神哲學,“人學”與“性學”所對應的中西天文歷算之學這兩個維度上展開互動與對話。從儒家基督徒對神學的回應來看,具體可以分為兩種進路:徐光啟、李之藻和王徵等人通過與利瑪竇、艾儒略、熊三拔(Sabbatinode Ursis,1575—1620)、傅泛際等人一起翻譯天文、地理、數學、工藝和音韻等著作,把《天主實義》等未能彰顯的“九天”“地圓”說發揮到極致,通過考證《九章》《周髀算經》等漢以后失傳的經典,對《周易》中的“象數”學重新理解,然后證明經典中所謂的“上帝”存在于“宗動天”之上的“天堂”里。這與清初“漢學”的實學風尚又有一定的關聯,盡管當時的“漢學”家們也批判天主教。(3)關于明清時期中西思想對話的兩條進路,參見李天綱:《跨文化的詮釋:經學和神學的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第92—120、145—163 頁。通過六經之首的《易經》,用天文歷算之學把“天”與“主”聯系在一起,這是一條由“天學”所對應的科學技術,尤其是“中西天文歷算之學”的比較研修進到“神學”的路數;而楊廷筠等人深受理學和佛學的影響,注重從心性論的探討、從超世與超性的對鑒中尋找上帝,其“敬天愛人”承接了明末儒釋耶三家在“天學”上熱烈的宗教實踐,這可謂較貼近信仰生活、更適合一般信徒由明末理學、佛學到“天學”所對應的天主教神學的進路。(4)《跨文化的詮釋:經學和神學的相遇》,第42—49 頁。
由以上關于“天學”說法之種種的厘清及其互相之間辯證關系的討論,不難發現,沸騰的明末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沸騰的正是明末“天學”及其實踐。而這其中一個重要的核心命題就是晚明中西上帝觀的相遇,它帶來了基督教神名的中國化與漢語神學的濫觴。深化基督教神名的中國化研究可以帶來廣闊的漢語神學資源和中外文學文化比較研究的空間,推進基督教中國化。
三、論基督教神名的中國化
基督教中國化是一種異質宗教在華夏立足所自然而然的應有進程,它歷經了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溫教、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清末民初的基督新教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基督教兩會、天主教一會一團等歷史變遷;更有景凈(唐代來華的景教傳教士,外文原名、生卒年俱不詳)、利瑪竇、艾儒略、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趙紫宸、吳耀宗等人對基督教神學本土化的接續建構。與基督教中國化歷程相伴隨的一種容易被忽視的現象就是基督教神名的中國化。
推進基督教中國化應加強基督教神名的中國化研究,基督教的中國化首先應該是基督教神名的中國化。從唐朝太宗年間來華的景教算起,“阿羅訶”是景教最重要的文獻“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文對基督教至上神敘利亞文書寫的音譯。前冠以“三一妙身無元真主”,景教在中國的傳播所受佛道諸家之影響可見一斑。845 年唐武宗滅佛,景教也未能幸免。其后的余緒在元代又一度中興,稱為也里可溫教,但信奉者多為原先的游牧族人,在漢人中并未流行。陳垣考“也里可溫”為當時的“蒙古人之音譯阿刺比語,實即景教碑之阿羅訶也”。因此,從來華基督教的早期歷史來看,景教和也里可溫教對神名的常用稱呼,在今天的中國已經完全消散在歷史的塵煙里,只留存在文獻之中和史學家的筆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情形則完全不同。實際上,基督教自明末就已經開始傳播幾個相對穩定且影響深遠的中國式神名:天主、天、主、天地的主、天地萬物之主、上主、大父母、神、上帝,這些神名中的大部分迄今仍然活在中國基督徒的口口相傳里,是中國基督教的一筆寶貴財富。
積極開展基督教神名中國化問題的研究,對深入基督教的中國化、促進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具有重要意義。
基督教神名的中國化研究能夠與我國傳統文化之本根產生互動,對今天的中西文明互鑒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敬天法祖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核心信仰,而最主要的幾個中國化基督教神名如上帝、天主、大父母等,都可以與中華文化之本根很好互動。敬天法祖包括敬天、法祖兩個方面,把基督教的神在中國語境中稱為上帝和天主,是因為在中國文化元典中“天”和“上帝”確實有超越意義;而“大父母”更與中國人“法祖”的血親孝順等倫常思想相聯系,顯得親切。“上帝”“天主”是基督教中國化神名的典型代表,“上帝”神名無疑是其中影響最大者。在基督教神學中,上帝論是對上帝的存在和屬性的論證和闡述,在西方有著一整套論說的體系且影響深遠;與此相應,肇始自商周時期的帝天信仰在中國同樣是載諸典籍,源遠流長。但今天對基督宗教稍有了解的中國人,一提到上帝,首先想到的恐怕不會是儒家經典中所說的皇天上帝,而是基督宗教共同崇拜的那個至上神。這說明,漢語中既有的言語表述與思想資源經過詮釋,會獲得新的神學意義。這給今天反思中國自己的基督教神學的發展以很大啟發:中國古代的帝天信仰和儒家傳統的祭祀禮儀,需要在與基督教神學互動的基礎上充分表彰并發揚光大。這有助于重新發現并定義我們自己的國民信仰,從深層次推進基督教中國化,為社會主義精神建設服務。
基督教神名的中國化研究能夠與西方的基督教神哲學直接對話,這對于今天的中西文明比較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以“大父母”神名為例。與西方常常稱呼天主為“父”“大父”明顯不同,把神名稱為“大父母”是中國基督教的鮮明特點。儒家“大父母”思想肇端于《易經》,濫觴于理學乾父坤母的宇宙論,而天主教傳統中往往強調“父”,也有崇拜圣母的傳統,兩者之間的契合使傳教士和儒家基督徒提出“大父母”神名。這是基督教神學與儒家經學兩者間一次非常經典的對話。另外,“大父母”說法也是一種非常經典的在地化與處境神學的發明,可以表明人神之間的親密關系,也包含著令女性主義神學家們大感興趣的價值。此外,阿奎那(Thomas Aquinas,約1225—1274)在論證上帝存在時使用了宇宙論證明,“大父母”神名實際上也暗含著一種宇宙論的邏輯推理在里面:每個人都有父母,再往上推,就會有一個超越個體的共有的父母,即上帝。這又與天主教官方神學產生了聯系。所以說“大父母”是基督教中國化神名的最佳范例之一,我們可以從適應的方面講“大父母”是教會為適應儒家文化而提出來的,我們也可以從中國化的角度講“大父母”是國人用自己的知識背景為理解教義而提出來的。以上研究及其在現代社會的實踐推廣,無疑對發展與社會主義社會充分適應的中國基督教神學大有裨益。
各級研究機構要從“譯名之爭”中超脫出來,積極開展筑基在中國化神名基礎上的“中西禮學”的研究。由西方基督教的至上神“God”到各種中國化神名,表面上是翻譯問題,背后對應著的正是基督教中國化的漫長歷史與更深層次的本土基督教神學建構。關于基督教至上神之中國名稱的種種糾葛,史學界一般以“譯名之爭”(Term Question)來概括。它包括明末清初“中國禮儀之爭”中的“帝天論”與清末民初由《萬國公報》倡導的“圣號論”兩個論辯激烈的時段。然而,中國基督教的發展史,尤其是“God”的漢譯學術史表明,在翻譯的層面上來討論問題,“上帝”“天主”與“神”的真意反而愈加隱晦不明,對教會以及基督教中國化事業反而弊大于利。
因此,研究基督教神名的中國化,要擺脫與超越譯名孰優孰劣的意氣之爭,在弘揚本土基督教神學事業上努力開拓。我們需要加大對中國化神名的研究投入以及成果推廣的力度,由“爭論”到“本土化”,及時梳理本土基督教神學的發展,最終深入到“中西禮學”的溝通與對話,以實際行動為基督教中國化做出貢獻。(1)《“中國禮儀之爭”的緣起和中西學統的關系》,第120—121 頁。在當下的中國,無論是“基督教中國化”,還是“中國化基督教”,甚至“基督教化中國”等命題,都是政界、教界、學界甚至每一個中國人都無法回避的糾結與挑戰。新時期推動基督教中國化問題走向深入的一個重要面向,就是應該繞開已經變得沒有必要的意識形態與政教紛爭上的無謂糾纏,努力加強基督教神名的中國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