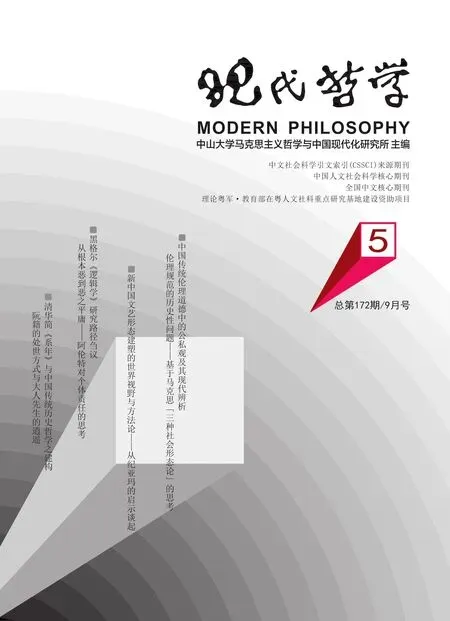統治、剝削和受苦①
——馬克思主義的開放性與法律理論
[英]科斯塔斯·杜茲納 [英]尤尼·沃林頓/著 邱昭繼 林展翰/編譯
馬克思主義理論陷入一場深刻的危機,這場危機對所有社會科學都有影響,包括法律理論。本文討論了20世紀80年代的兩本重要著作,其中一本分析了馬克思主義與法律之間的關系,另一本分析了馬克思主義與正義之間的關系。我們試圖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危機的現狀來評估這兩本書的主要優劣。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在于,對于嚴謹和系統性的最終弄巧成拙的追求,讓它成為一種封閉的思想體系。這蒙蔽了馬克思主義用自己的文本削弱這種論證的可能性。然而,我們認為,下一步不是試圖通過謹慎或幻想的嘗試來消除這些不一致,而是通過理論和政治兩方面實現其潛力來復興馬克思主義。像所有思想體系一樣,馬克思主義陷入權力關系之中。此外,似乎必須證明知識是理性的、系統的和內部一致的,以便權力/知識網絡可以擴展其對社會的控制。我們認為,在馬克思主義和法律理論中,對知識尊重的這些主張是被質疑的,我們希望對權威知識形式去正當化的可能性持開放態度。這將使替代的理論和政治戰略成為可能。這兩本書是本文關注的焦點,我們將在第二部分討論。在關注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提出了解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建議。在第一部分,我們概述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并試圖將我們的批評置于信心崩潰之中。
一
所有政治、文化、法律或制度實踐都是在理論指導下形成的。但是,當相關的實踐陷入危機時,理論生產就會發生巨大變化。它們的基本假設變得明確并且“變質”,它們不再是爭論的理所當然的參數,它們本身就成為爭論的對象。在這樣的危機時刻,理論有兩種開放性策略:它試圖對實踐中出錯的學說提供“正確的”解釋并為其提供新的理由,或者試圖用一種新理論替代舊的和不充分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許多新理論可以被看作是對馬克思主義危機的回應,并且與權力、政治和國家再理論化努力密切相關。它們還回應了法律實踐和理論中的平行危機。出于分析的目的,我們可以將馬克思主義的法律學術視為馬克思主義傳統或法律理論體系內的一部分,使它們浮出水面,并試圖重構或超越前者或后者的基本假設。
我們選擇將批評主要置于馬克思主義之內,而不是法律理論之內。我們的政治原因在某種程度上更具推測性,但它們與如下看法有關:馬克思主義仍然致力于減少各種形式的異化、壓迫和統治(1)Michael Ignatieff, The Needs of Stranger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4; Joseph W. Singer, “The Player and the Cards: Nihilism and Legal Theory”, 94 Yale L.J. 1, 1984.,這是我們設定的現代社會的參數。法律傳統上所體現的最崇高的目標(消除不公正、免受壓迫等)并非完全不同,但這些目標似乎在20世紀向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屈服中丟失了。正是在這一點上,一種開放的馬克思主義形式和一種自覺的法律理論可能開始匯合。
(一)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基礎
在人類進化的所有階段,社會都將現有技術用于現有物質資源,從而再生產物質自身。由于人類的聰明才智,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確保了對自然的不斷提升的控制能力,并且在資本主義社會克服物質匱乏成為可能。但技術活動是在一個制度框架內進行的,該框架規定了獎勵、義務、權利和權力的分配。然后,階級構成了統治-剝削的不對稱位置,感知和組織他們的生活經驗的方式,以及整合或對抗整合的政治形式。這進一步支持或破壞了制度框架。
社會進化可以被視為技術工具和實踐政治活動之間的辯證作用。馬克思的理論是對人類歷史和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描述,是一種批判理論,一種關于統治和剝削以及革命意識的理論。然而,由于馬克思在他的主要理論著作《資本論》中對政治實踐活動的相對冷漠,他的理論的批判性被削弱了。馬克思并沒有給予勞動和經濟所獲得的完整的認識論和哲學基礎。技術工具活動相比政治實踐活動被賦予了優先性。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確定馬克思主義對科學地位的主張。如果經濟層面存在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和驗證的某些法律,那么其方法與自然科學中應該獲得的規律類似。這些規律的必然邏輯構成歷史的理性基礎,開辟了歷史演進中超越現階段的理論可能性和政治必然性。“生產力的過去發展使社會主義成為可能,它們未來的發展使社會主義成為必然。”(2)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 20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二)從馬克思到馬克思主義
在歐洲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政治實踐中,馬克思著作的解釋和這種版本的采納和制度化標志著從馬克思到馬克思主義的轉變。世紀之交的社會主義領導人,如考茨基、盧森堡、列寧、托洛茨基和伯恩斯坦,都認為社會主義改造的代理人是工人階級,這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見解相一致。然而,需要理論化的是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階級之間聯系的本質。實現這一目標的第一種方式是使用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之名宣稱的某些傾向性法律的嚴格框架:資本主義的內部動力導致少數寡頭壟斷企業的財富不斷集中。因此,大部分人口變成無產階級,并被推向工人階級陣營,這個階級變得越來越貧困。資本主義的邏輯導致社會日益簡化,陷入苦戰的兩個主要階級正在為經濟危機引發的最后攤牌做準備。
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這種不斷增加的間隙決定了政治實踐的作用。它的主要任務是聯合階級并用歷史使命把階級聯合起來。完成任務的代理人是非常明確的,即政黨及其知識分子,他們掌握科學,對階級的歷史使命和客觀利益洞若觀火。如果階級在生產關系中具有本體論地位,則政黨的地位是認識教育者;他了解歷史規律并將它們傳授給這個階級。由于階級利益的構成優先于政治,政治實踐的作用是在政治層面上代表它們。政治等于代表,意識形態等于揭露。兩者的結合為“漸進式替代主義”開辟了道路:從階級到政黨,從政黨到領導,從領導到人格崇拜。
(三)政治轉向和基礎-上層建筑隱喻
幾乎所有最近的理論都專注于政治、國家、意識形態和法律。馬克思主義采取了明顯的政治轉向。最近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研究是這一轉向的表現和效果,必須與之相關地進行評估。但是,盡管出現了這種政治轉向,馬克思主義政治意識版本仍然需要掙扎的遺產是馬克思所謂的基礎-上層建筑隱喻。
對決定論的第一個可能的理解是一種機械的、原因-結果的因果關系。原因(經濟)是其結果(上層建筑層面)的外部因素。當根據機械因果關系解讀“建筑”隱喻時,政治、法律和意識形態層面允許的唯一分歧是時間滯后和暫時的不一致。在最強大的臺球模型中,經濟決定政治的形式和內容,法律對經濟的影響微乎其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政治轉向”是基于對該模型的明確拒絕。然而,有一種更有影響力的方式可以分析決定論。機械因果關系將其元素視為彼此的外在因素,它們的聯系是單向的;它無法把握整體對其元素的影響。源于萊布尼茲和黑格爾的第二個版本可稱為“表達因果關系”。社會和歷史被概念化為有機總體,其中各個層次是在經濟層面展開的基本矛盾的附帶現象。存在一種內在的本質,使社會成為整體,并用它的所有現象形式來表達。在化約論那里,機械和表達因果關系幾乎無法區分,其根本的真相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根本矛盾,這種矛盾隨后在經濟層面構成的和社會結構的其他所有層面生產的基本階級之間的不可調和的沖突中表現出來。最近馬克思主義關于政治和法律的學術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了解這種類型的本質主義。
(四)表達因果關系與法律分析
有趣的是,最近在美國批判法律研究中出現了更接近黑格爾式表述的表達因果關系的強版本。社會被認為是由一系列組織觀念滲透的有機整體。然而,所有總體文化方法都面臨著兩個嚴重的問題:第一是分期,即為所考察的時間段的非任意識別提供標準;第二,這些方法必須說明從一個時期到下一個時期的變化。圖什內特認為這兩個問題都非常困難,并用“重建的”基礎-上層結構隱喻提供了一個相當令人驚訝的答案。就法律意識的變化而言,我們了解到,它們“似乎與經濟體系的變化有關”。雖然時期被視為它們潛在意義的表達,意義使法律和經濟成為“單一文化事業的組成部分”,但歷史是一系列這樣的階段,歷史運動規律由經濟給定(3)Mark Tushnet, “Marxism and Law”, Bertell Ollman & Edward Vernoff, eds., 2 The Left Academy 157, New York: Praeger, 1984, at 162.。在這一點上,總體方法與更嚴格的決定論之間的差異并不大。
在這兩種因果關系版本中,層次和實例之間以及概念與現實之間的關系被視為媒介。媒介方法主張從經濟到政治或法律“從一個層次到另一個層次調整分析和發現的可能性”(4)Frederick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22, Cambridge: Methuen, 1982, at 39.。在第二種意義上,如果在現實本身和關于現實的話語之間存在根本分歧,那么話語(如科學、真等)與現實之間的關系必然是一種媒介關系。“真”之理論的概念決定論與現實的客觀決定論直接相關。在機械因果關系中,媒介是外在的;經濟設定了其他層面的限制和局限。在表達因果關系中,媒介是內在的:在各個層面都觀察到類似的過程,就像普遍存在的本質的許多表達一樣。在這兩種情況下,偶然性返回到必然性,差異性返回到同質性,具體返回到抽象,現實返回到概念。
(五)結構主義與自主性
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路易斯·阿爾都塞及其追隨者對機械和表達因果關系提出了最嚴格的批評。阿爾都塞反對基礎-上層建筑隱喻的傳統解讀,認為經濟、政治、法律和意識形態是一種共同結構,即生產方式的層次。原因是結構,不是本質或隱藏法則,而是其結果的內在原因。每個層次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內在歷史和存在條件,與所有其他層次“相對自治”并有助于整體結構的再生產。
結構是各層次之間復雜的關系集,因果關系在于闡明它們之間的實踐和效果。經濟仍然是每個社會“最終情況下”的決定性層次;也就是說,它決定結構的哪個層次將占據主導地位。這種結構因果關系的概念接著承認了各個層次的特殊性和有效性以及它們對整體再生產的必然特征。
上層建筑和法律的“相對自治”成為最近理論著作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戰斗口號,法律來自特定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在“最終情況下”或“最終分析”中具有決定作用。最近經濟論和非經濟論的馬克思主義版本之間的爭論主要涉及歸因于上層建筑的因果效應。然而,對于馬克思主義所面臨的決定論和自治性的雙重問題,相對自治似乎提供了語言的而不是理論上的答案。如果經濟在最終情況下具有決定作用并且在該情況下自治是相對的——無論如何解釋表達式——經濟與上層建筑之間的因果關系仍然是機械的。友善的評論家認為,相對自治只是指向一種理想的分析類型,它保留了經濟與其他層面之間的“聯系”,同時避免了決定論的陷阱,但它仍然是一個沒有理論支撐的概念(5)Alan Hunt, “The Theory of Critical Legal Studies”, 6 Oxford J. Legal Stud. 1, 30, 1986.。
(六)作為建構性理論的批判法律研究
相對自治/終極意義上的決定論這兩個概念的問題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者討論的主題,他們將自己的著作置于批判法律研究運動之中。阿蘭·亨特對批判法律研究的廣泛評論中發現了相對自治性理論的大致輪廓。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法律理論一直專注于法律與經濟/社會之間因果關系的本質。當問題以這種方式出現時,“法律”“經濟”和“社會”這些對象必然被認為是具有完全固定身份的獨立封閉領域。另一方面,批判法律研究方法——“建構性”法律理論——探討了法律和經濟關系的“因果滲透”(6)Id. at 10 & 38.。法律“是一個復雜的社會整體的組成部分,它既構成社會又由社會構成,既塑造社會也由社會塑造”。建構性理論強調法律的效果。
如果馬克思主義要重新發現其理論激進主義,我們建議,它必須放棄封閉概念和固定身份的舒適但膚淺的安全。階級和階級利益、國家、法律和經濟都提到源于西方理性主義的內部同質性和外部媒介。無論向基礎-上層建筑隱喻引入何種程度的概念或語言復雜性,經濟決定論都無法完全驅除:在某些情況下,經濟將被具體化,一個封閉的層次、隱藏的財富或公開的秘密優先于其他一切。尋求確定的自治性將總是在相對的決定性和偶然性在相對的自治性之處發現必然性。二元論不可能被超越。
在這里,正統和馬克思主義法律理論似乎融合了。標準法律理論聲稱法律具有連貫性、意義清晰性和因果有效性,或者說,如果看起來不這樣做,則錯誤在于法律的闡述而不是法律自身的本質。偶然性被承認,但只是在邊緣,正如哈特所說的陰影意義或自由裁量權,或德沃金或菲尼斯所說的錯誤。如果從“自治性”中剔除了“相對性”,那么法律的自我理解似乎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法律理解”。
二
(一)正題與反題:法律,科學與共產主義
我們的第一個文本是休·柯林斯的《馬克思主義與法律》(7)Hugh Collins, Marxism and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在本節中,未歸屬的頁面引用是針對此作品的。。在這本書中,柯林斯試圖概述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法律分析,修復被證明存在缺陷的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的框架。根據柯林斯的闡述,一種理論要能夠契合馬克思主義的范疇,應該遵循兩個主要論題:首先是唯物主義論題——馬克思關于經濟決定社會和歷史的各個方面的主張;其次是共產主義論題——馬克思預言了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法律機構將“消亡”。
柯林斯將唯物主義論題應用于法律,這種闡述明顯體現在《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第四章中。我們建議重點關注這個章節,因為正如柯林斯正確指出的那樣,隱喻是眾多經典馬克思主義論點的核心。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這個隱喻并指出,雖然它最初的合理性和簡潔性使得它在一般的社會理論層面上有著大好的前景,但實際上它很快帶來更多的問題,而不是解決方案。柯林斯在馬克思主義法律理論內部探討了這一難題。在最簡單的層面上,隱喻將沿著以下的路徑適用于法律分析。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馬克思的“卓越洞察力”與社會關系分析相連,這種分析是對社會組織生產和再生產方式的回應。理解社會發展的任何特定階段的關鍵不是人們對所生活的社會的看法,而是維持社會再生產的物質方法。只有充分理解了這一點,才有可能對思想的實踐和形式、政治、法律、宗教等進行嚴格的分析。這就是為什么馬克思花了那么長時間研究“經濟”,而對政治和意識形態形式的分析卻語焉不詳。這種方法產生的結果就是將法律視為任何由經濟決定的特定社會制度的回應。因此,只有先通過對具有一定技術水平的社會的經濟生產規律進行詳細的分析之后,才能解釋封建社會的法律。現代社會也是如此,法律并不是經濟形態的創造者,而僅僅只是它們的創造物。
在柯林斯的馬克思主義中,意識形態只是上層建筑隱喻下的另一個產物。它指的是“在生產關系中產生于社會實踐并由社會實踐構成”(見書第43頁)的一整套主流觀念。這種主流的意識形態出現在“那些有相似經歷的生產資料所有者的階層中,他們在生產關系中發揮著大致相同的作用”(同上)。法律作為一種意識性的社會調節形式,將從主流意識形態中產生。解決唯物主義論題的法律問題的關鍵在于每個社會主流觀念的發展過程。在最初的階段,這些觀念是以習俗和道德標準的形式出現的。在第二階段,這些標準轉化為法律規則。于是,法律產生于意識形態,是對法律前習慣和習俗的一種更精確和準確的表達。
因此,柯林斯認為,法律具有“元規范”性質。隨著社會變得越來越復雜,有必要確保能有解決因習慣關系而產生的爭端的辦法。通常的結果是建立一些權威機構或形成一個群體,賦予他們解決爭端所必需的儀式性質。隨著時間的推移,個人或群體對習慣實踐要求的任何聲明,都變得比實踐本身更重要。法律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因此,法律具有的一個特點是,它們吞沒了現有的習慣標準,并及時成為實踐規則的權威來源。可接受的程序由法律決定,而不是通過調查習慣做法本身來決定其范圍。法律的元規范性是其產生方式的結果。
這一分析顯然使柯林斯能夠解決這個令人頭疼的難題,即馬克思主義理論要求法律既是上層建筑,又不僅僅是上層建筑。正如理論所指出的,法律規則產生于上層建筑,產生于理論要求的意識形態。它們在形式上是上層建筑,因而間接地由生產關系所決定,因為它們是在有條件的意識形態中產生的。然而,法律的元規范性意味著它密切地調整著生產關系,成為唯一賦予生產關系具體形式和具體表述的制度。法律在經濟基礎中發揮作用,即使它是上層建筑的起源。這將導致一個累積的過程。法律的發展允許甚至促進其他社會進程,而這些社會進程將反作用于法律,等等。因此,柯林斯認為自己規避了馬克思主義的法律問題。我們現在有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在談到巴克盧公爵的案例時,他說:“法律應該被視為生產活動和充滿意識性的規章制度之間長期互動的產物。”(見書第90頁)柯林斯承認這破壞了基礎和上層建筑這一分析的簡單性,但也認為物質決定論的關鍵因素仍然需要保留下來。
柯林斯是否成功地將馬克思主義從樸素的基礎-上層建筑隱喻決定論中拯救出來,同時通過他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檢驗?我們認為沒有。起初,他似乎是在回答“法律問題”,但他在分析意識形態和理解階級問題時,卻陷入同樣的老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對階級的理解。法律既是上層建筑也是基礎,是因為它起源于一種意識形態,且界定和調節著生產關系。而階級又是在生產關系中形成的,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受經濟實踐的制約。在法律中被驅逐出來的經濟還原論問題,又重新出現在法律主題和出現地點。法律既可被塑造又塑造其他事物,僅僅是因為階級產生于經濟中,也在經濟中被創造。
這種分析導致了一種與英美法理學相適應的法律視野。在對這個隱喻進行討論之后,柯林斯準備提出的不是法律的定義,而是一幅描繪法律體系主要功能的圖景。如果柯林斯是對的,那么這個令人痛苦掙扎背后的賭注就是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存亡,因為根據柯林斯的觀點,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就不存在馬克思主義,那么我們就必須走得比我們迄今為止所建議的更遠,并同意福柯的觀點。柯林斯的科學方法和共產主義這兩大理論存在潛在的互斥性。
那么,讓我們回到共產主義,正如前面提到的,這是鑒別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第二個考驗。柯林斯并不質疑共產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地位,但對法律的預測并不信服。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內部傳統上對法律抱有敵意,主要原因是馬克思主義者沒有認識到法律在構建生產關系中的重要性。法律的“元規范”性質確保了它在包括共產主義在內的每個社會的生存。除非馬克思主義能夠對共產主義生產關系提出一個與已知的重點有本質區別的“堅定的觀點”,否則“消亡”的命題是無法持續的。那么,我們可以用法律的形式大致闡明柯林斯的立場如下:所有社會中的生產關系,即使最有限的復雜性的生產關系,都受(元)規范的調整。
柯林斯能否在這一問題上戰勝他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目標,取決于他過于寬泛的法律概念能否為人們所接受。正如前面提到的,這一觀點有時給人的印象幾乎與所有規范性規章完全相同。然而,柯林斯批判的特點是,他再一次以批判對象失敗的方法、不正確的解釋、不連貫、誤導和“模糊”的預測為基礎。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第二根支柱的共產主義,只有在完全符合第一種科學方法的情況下才能存在。
納入和排除標準[2] :①所有患者神經功能損害體征持續時間超過1 h,NIHSS評分≥4分,顱腦CT檢查發現患者雙側基底節區多發性腔隙性腦梗死;②排除3個月內有卒中史和重大顱腦外傷史、可疑蛛網膜下腔出血、顱內出血既往史、顱內腫瘤、及型出血傾向、活動性內出血、血壓異常升高(收縮壓超過180 mmHg或舒張壓超過100 mmHg)、不符合溶栓治療適應征的患者。
然而,我們有可能切斷這兩個論題之間的聯系,而不用過多擔心是否仍能將一種理論定性為馬克思主義。這樣,共產主義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愿景,或者是烏托邦,是對我們周圍所有那些創造統治、剝削和苦難事物的否定。我們在結論中再次簡要地回到這一點,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能會說,任何對預言的渴望都必須隨著特權方法論一起消失。
(二)綜合:正義的矛盾
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概念可以給我們一個尺度,以衡量當今法律關系的各個方面,并指導我們努力改善目前的狀況。這一尺度可能有助于我們評估正義的概念。我們評論的第二本書——艾倫·布坎南的《馬克思與正義》(8)Allen E. Buchanan, Marx and Justice: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 London: Methuen, 1982.在本節中,未歸屬的頁面引用是針對此作品的。——分析了一個正義的概念。布坎南聲稱,這個概念可以從馬克思的著作中汲取。布坎南的貢獻必須置于對馬克思、正義和道德的持續的、生動的爭論之中。這場爭論的中心問題是馬克思在處理規范性問題、批判和辯護時一個難以克服的矛盾。這部作品充滿了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苦難、貧困、壓迫和不自由的道德譴責。正如E.P.湯普森生動描述的那樣:“馬克思在憤怒和同情中,每一筆都是道德家的筆觸。”(9)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8, at 363.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又聲稱自己是一門社會科學,而不是一種道德信仰。
布坎南在這個問題上深思熟慮的嘗試,是以兩個目的來審視馬克思著作中的正義主題。這就是對馬克思正義觀的重構和批判,并將其與當代最好的正義理論——羅爾斯的正義觀進行比較。布坎南第一個任務是在三個主要層面上進行的。在仔細閱讀經典著作和最近的正義爭論的基礎上,他論證了資本主義剝削是不公正的,這是根據唯一現存和適用的標準,即資本主義的正義概念。資產階級的正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等價物的自由交換的基礎上的。但正如上文簡要指出的,馬克思的分析表明,在勞動合同中,盡管有法律上的外觀,但沒有交換等價物,雇主得到的比雇員多。根據資本主義本身的司法正義原則,資本主義是不公正的。然而,根據布坎南的觀點,馬克思除了對資產階級辯護者的這種轉向之外,并沒有提出任何非相對論的正義原則。事實上,他不僅沒有從更高的正義原則的角度來批判資本主義有缺陷的對等原則,而且堅持認為這種法律和道德觀念在共產主義中沒有任何作用。“共產主義的優越性在于,它使分配正義的整個問題變得毫無意義。”(見書第59頁)在布坎南看來,馬克思相當奇特的推理是這樣的:正義概念的需要是在正義的要求無法得到滿足的情況下產生的。資本主義為分配正義和法律權利概念的出現創造了所有充分條件。它延長了稀缺性,再加上資產階級特有的利己主義,引起對資源的矛盾訴求和對道德與法律保護的要求。但這對正義的追求是徒勞的。只要階級分化還存在,任何再分配的措施,任何正義的原則,都不會使工人自由,也不能使之與資本家平等。真正的人類解放只能通過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來實現,從而廢除社會的階級劃分,把生產資料置于整個社會的民主控制之下。但是,生產關系的這種根本變化將立即移除實現正義與權利的充分條件。
那么,根據布坎南的觀點,馬克思將正義作為一個相對主義的概念,相當隨意地加以運用。正義被賦予一種邊際的、策略性的功能,上面所指出的矛盾轉化為一種次要的矛盾:對正義概念的需要恰是正義無法實現的標志。布坎南認為,這一矛盾中的悖論抓住了馬克思立場的復雜性,這表明馬克思的立場并不是不一致的。事實上,布坎南認為他的解決方案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是對道德和政治哲學公認教條所能想象到的最激進的挑戰。
布坎南認為正義理論的第二個必要層面,源于對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型的某種形式的動機理論的要求。布坎南解釋了馬克思不喜歡“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道德說教。工人階級不需要這樣的勸告來完成革命任務,只需要對現實和自身利益有清楚的認識。革命的科學家的作用是向工人階級提供這種理解,并幫助他們聯合起來完成預定的任務。但布坎南認為,馬克思的否認使其理論留下一個重大缺陷。如果沒有一個成熟的正義理論,工人就不可能有足夠動力采取必要步驟來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此外,一個關于利己動機的科學理論,在沒有一系列道德原則的情況下,將不得不訴諸暴力,以使工人認識到他們的“自身利益”。社會主義的歷史再次證明了另一個矛盾,即強迫人民獲得自由。
第三個層面與馬克思的未來社會,即共產主義有關。我們看到,在布坎南的解讀中,隨著司法環境的變遷,正義和其他司法概念都將變得無用。但布坎南表示反對,認為即使在一個和諧的社會中,與階級無關的沖突也會持續存在。完美的利他主義者對共同利益的概念或實現共同利益的方法可能仍然存在差異。馬克思的理論摒棄了正義和權利的原則,但除了虔誠和令人難以信服的保證之外,沒有提供任何其他的社會調整手段。
為什么大家對馬克思的正義觀如此感興趣?畢竟無論馬克思是什么,他都不是一個道德哲學家,也沒有對這個話題投入任何持續的關注。那么,為什么要爭論呢?這些原因似乎與試圖重新構建“基礎-上層建筑”隱喻的復雜嘗試背后的原因相似。這一主題正被用作馬克思主義理論、革命實踐與現實有著密切關聯的論斷的試金石。讓我們來看看這場爭論的主要替代結論。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1)馬克思主義有令人滿意的正義理論;(2)馬克思主義沒有這樣的理論,但它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不需要這樣的理論;(3)正義是社會關系的核心概念,但馬克思主義沒有為其留有空間;因此,馬克思主義是一個不令人滿意的理論。
這三種立場的背后都有一個共同前提。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系統的、全球性的理論,因此對社會組織的所有重要方面都有或應該有令人滿意的解釋。另一方面,系統論述的第一個優點是內在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必須在文本矛盾的表面下或在文本不一致的情況下,在作者的意識下被發現。因此,正義的爭論,不論其結果如何,都變成對馬克思主義系統性和封閉性的肯定。
我們認為,這次辯論提供了扭轉這種前提的極好機會。讓我們回到布坎南的論述。他認為,馬克思的弱點在于沒有注意到一個已發展的正義理論的重要性,并利用這一弱點來批判整個理論。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布坎南并沒有發現弱點,而是在馬克思的體系中打開一個創造性的契機。這場爭論表明,雖然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正義概念的相關性,而且有時將其斥為危險錯覺的集合,認為它是邊緣的、派生的和偶然的,但正義卻在文本中浮現出來,就像一具被馬克思認為是釘在棺材里的尸體出現一樣。布坎南后來發現了一個不斷蠶食馬克思大廈的概念。正是由于正義在馬克思理論中所扮演角色的尷尬和難以捉摸的本質,才揭示了體系內部的可能性。馬克思主義理論也許更傾向于這種人為意義的封閉。馬克思主義后來轉變為國家和運動的官方意識形態,導致更大的封閉性和意義的終結。但這些衍生的、邊緣的、偶然的因素不斷回溯和破壞著那些決定性的、核心的、歷史性的規定。外圍的因素也在協助否定馬克思主義體系本身的概念。
正義作為一個批判性的概念是出了名的開放的。它可以在各種各樣甚至相互矛盾的政治項目和反對統治、剝削和苦難的斗爭中被闡明,從而表明社會空間的開放性。如果正義的問題和概念不能如人們所期望那樣消失,那么從對立的角度看,正義的概念是其烏托邦理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那時,馬克思主義可能會被批評為未能發展其烏托邦主義,未能帶來“解放的、突破性的視角以處理當下棘手的問題”(10)Steven Lukes, Marxism and Mor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at 46.。那么,道德、烏托邦、正義這些直至今日還淪落邊緣的東西,可能要立刻搬到中心去。
三
我們認為法律體系增加了人類所有痛苦的總和。這并不是說,我們認為已知法律關系的所有方面都必然會增加壓迫負擔。這樣的觀點是愚蠢的。但概括而言,我們認為現代法律關系滋生了一種有害的觀念,即對于某些人來說,權力是任何復雜社會的必要組成部分,而對其他人來說,權力的缺失也是必然的。我們得到的是一種病態的冷漠與絕望的混合物,而不是創造力。如果社會關系確實是預先設定好、不可改變的,那么冷漠和絕望一樣,都是對我們周圍丑陋事物的一種可能的反應。相反,如果歷史發展被看作是偶然的,并且有可能被人類有意識的活動所改變,那么人們就不會太過天真,而會試圖去思考更好地社會關系形式。正是在這里,在明顯封閉的思想體系中顯示出學術著作的開放潛力,這一點非常重要;無論法律研究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都是如此。
如果你認為這種觀點聽起來含糊、理想主義、不切實際和過于浪漫,你或許是對的。但我們對于法律觀念的調查正是由此開始。讓我們重新回到批判法律研究的論述。如果批判法律研究是英美法理學的新東西,那么它在兩個層面上是新的。簡言之,這場運動對法律推理的批判比它的前輩們,尤其是現實主義者,提出了更深刻的批評。當然,我們在此無法對這一觀點進行拓展。但是,批判法律研究將現實主義者甩在身后的地方并不在于法律推理的尖銳性,而是在于他們的政治立場。通過揭露法律神廟的脆弱性,批判法律研究讓政治議程變得比其他方式更加開放。
馬克思確實為許多形式的思想提供了一個起點,這些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與既定的秩序形式“對立”。這鼓勵我們在地方、國家,甚至是國際層面去尋找一種新的社會安排形式。它的缺陷幫助那些有“感覺”的人,去進一步調查為什么在一個明顯能夠減輕痛苦的世界中有如此多的痛苦。這將導致與另一種觀點直接對抗。這種觀點認為,我們試圖減輕痛苦所能做的一切不過是陷入更多相同的模式中,用波普爾的術語來說,就是陷入更多嘗試過的、檢驗過但又失敗了的社會民主政治理念中。這種“感覺”并不比盧埃林的“普通常識”更具確實性,它對此也不多加掩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