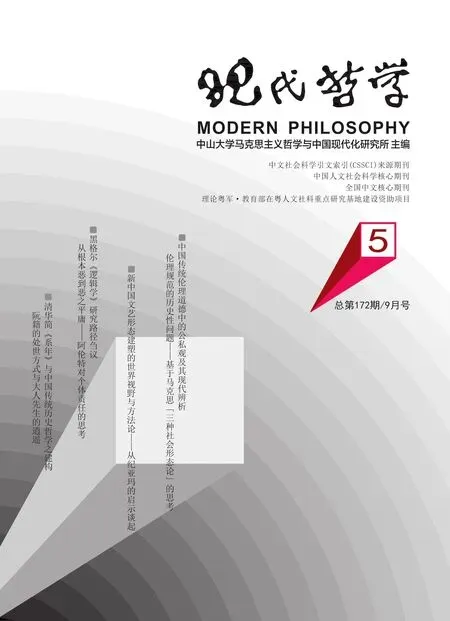黑格爾《邏輯學》研究路徑芻議
莊振華
《邏輯學》是黑格爾最核心的著作。當前國內外學界的黑格爾研究大有復興之勢,人們對這部著作(1)本文中的“《邏輯學》”泛指《小邏輯》(即《哲學科學全書綱要》第一部分)和《大邏輯》(即單行本《邏輯學》)。的興趣也有增無減(2)這里僅舉一例。已故美國哲學家羅森(Stanley Rosen)素重古代哲學,在其生前最后一年(2014年)卻出版了一部厚重的《邏輯學》研究著作(《黑格爾邏輯學的理念》),堪稱一個標志性事件。。它又是黑格爾最難懂的著作,雖名為“邏輯學”,但并非要創立一套與形式邏輯、數理邏輯等類似的工具邏輯,反而更接近于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和柏拉圖的辯證法,實際上探討的是世界本身的可理解性,或者說世界自我構造的邏輯基礎,更關注的是世界本身的真理,而不是人類現成化地把握事物的主觀概念框架(3)正如羅森所說,黑格爾并非要用辯證邏輯代替傳統邏輯學,他關注的是如何揭示那些涉及世界的可理解性結構的預設。See S. Rosen, The Idea of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 242.。如果在這個意義上閱讀《邏輯學》,我們的近現代哲學研究或許會打開更廣闊的前景。在此之前,我們需要找到進入《邏輯學》的適當路徑。本文打算就此略陳己見,在該書的起點與進展方式兩方面進行初步探討,并在此基礎上簡單談談該書與其他體系著作之間的互文關聯。
一、起點:概念與事情本身的同一
與引導讀者直接從自然意識入手,并一步步開拓視界、放棄成見、進入事情本身(4)黑格爾的“事情本身”既不同于康德那里不可理解的物自體,也不是主體意識從自身出發進行的表象,它在根本上指能為人所理解的意義世界本身。參見莊振華:《〈精神現象學〉義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509—521頁。的《精神現象學》不同,《邏輯學》并不是一部容易“上手”的書。閱讀此書時,首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是否找到了進入它的門徑?黑格爾在《大邏輯》“導論”開篇就說:“沒有一門科學比邏輯科學更為強烈地感受到一種需要,即在不作出任何先行的反思的情況下,以事情本身為開端。”(5)[德]黑格爾:《邏輯學I》,先剛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1頁;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I, Frankfurt a. M.: Suhrkamp Verlag, 1969, S. 35。本文所引用的黑格爾原文均依據德文原文校正,個別術語與注釋中所列中譯本或有出入。為節省篇幅,在每一部書首次出現時,同時列出中、德文本出處,其他地方只列出中譯本頁碼出處,略去德文本出處(譯文修改較多的個別地方除外)。引文中的黑體字為原文所有。其他各處同此,不一一說明。這意味著,任何外在反思不管是像意識哲學那樣與事情本身保持謹慎的距離,還是像唯理論那樣追求直接進入事情本身,實質上都只能看到它們各自想看到的東西,而沒有真正觸及事情本身及其邏輯。關鍵不在于意識與理性,而在于事情本身。話雖如此,黑格爾自己指明的這個門徑并不輕易向人開放,人們必須走過類似于《精神現象學》中那種異常艱難的旅程才能抵達它那里(6)同上,第26—27頁。。如若不然,不管人們從意識的種種形態(如該書前五章所示)出發,還是從到浪漫派為止的西方精神史的種種精神形態(如該書第六章所示)出發,都會落入與事情本身隔絕的困境。
我們不妨從《精神現象學》結尾與《邏輯學》開篇這兩個關鍵部位的若干論述,看看究竟如何進入《邏輯學》。黑格爾稱絕對知識為“概念性知識”(das begreifende Wissen)(7)或譯“進行概念性把握的知識”。黑格爾亦稱之為“在‘精神’的形態下認知著它自己的精神”(der sich in Geistsgestalt wissende Geist),即自知其為精神的精神。參見[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先剛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6頁。。在“絕對知識”章,黑格爾先是交待了作為此前的西方精神史之頂點的道德世界觀與優美靈魂如何向科學體系過渡,然后直接將包括《邏輯學》在內的科學體系與整個《精神現象學》進行對比,以此預示科學體系處于何種知識形態。他指出,當優美靈魂不再排斥外部世界并局限于自身之內,那么它自身作為概念就“獲得了普遍性形式,而保留下來的,則是自我意識的真實的概念,或者說是一個已經實現了的概念。概念便在它的真理中,亦即在與它的外化的統一中了”(8)同上,第493—494頁;Hegel, 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88, S. 521.。表面看來,這話似乎不難理解:只要我們在外部事物中把握到它可被我們理解的一面,那我們的知識不就贏得它的“實現”和“外化”了嗎?然而,這種流俗的理解是行不通的,它就與黑格爾接下來的描述相沖突:上述知識形態是“以純粹知識為對象的知識,知道純粹知識不是諸如義務之類的抽象本質,而是另外一個本質,這個本質是這一個知識,是這一個純粹的自我意識,因此同時也是一個真實的對象,而這個對象是一個自為存在著的自主體(Selbst)”(9)同上,第494頁。。這表明絕對知識不是關于道德世界觀或優美靈魂急欲排斥卻又離不開的任何“身外之物”的知識,因為任何身外之物都只是“抽象本質”,而不是真正的“本質”與“真實的對象”。可見,要理解絕對知識以及與這知識同一的事情本身,從主體及其意識、理性出發看待它身外之物的種種方式在這里都是不合適的,那樣永遠只能得到“抽象本質”,因為那種人為追求來的統一其實仍然以主體與其對象的分裂為前提。
擴大到《精神現象學》的整個歷程,黑格爾這樣闡明現象學與科學體系之間的區別:“如果說在精神現象學里面,每一個環節都意味著知識與真理之間的一個差別,都是這個差別揚棄自身的運動,那么反過來,科學并未包含著這種差別及其揚棄,毋寧說,由于環節已經具有概念的形式,所以它把‘真理’和‘認知著的自主體’之類客觀的形式結合為一個直接的統一體。環節并不是顯現為一個在意識或表象與自我意識之間來回往復的運動,毋寧說,環節的純粹形態(這個形態已經擺脫了它在意識中的現象),亦即純粹概念及其前進運動,完全依賴于環節的純粹規定性。”(10)同上,第501頁。這就是說,科學體系根本不再像現象學中那樣,關注人能知道和能做些什么,以及人如何處理其自身(“自我意識”)與他所建構出來的事物形象(“意識或表象”)之間的關系;而是在“概念”的層面上,即在了解到知識本質上是事物自身的自我認識,而不是主體的構想的基礎上,將事情本身的一些對象性表現(“真理與認知著的自身的對象性形式”)——在尚未達到“概念”層面時人以為只是他自身的行動成果的那些知識——真正視作事情本身運動的成果(“結合為直接的統一體”),即真正立足于事情本身并以事情本身的視角來看問題。但是,人們絲毫不必因為黑格爾談論“純粹規定性”和“純粹概念”便擔心科學只是空洞的概念游戲,因為它的內容與外延正是歷史上出現過的種種精神形態,分毫不少:“反之,對于科學的每一個抽象環節而言,總是有一個顯現出來的精神的形態與之相對應。正如現實存在著的精神并不比科學更豐富,這精神在其內容方面也并不比科學更貧乏。”(11)[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第501頁。這意味著科學體系與《精神現象學》同樣廣闊與豐富,只不過它是在真正的概念層次上探討《精神現象學》探討過的同一個世界。那么,科學體系將如何探討這個世界?“科學的本質,亦即那個在科學里通過自己的單純中介活動而被設定為思維的概念,把這個中介活動的各個環節分拆開,并按照一個內在的對立把自己呈現出來。”(12)同上,第501頁。這意味著,表面看來科學的本質仿佛是思維在對一堆概念進行相互中介,仿佛是主觀的事情,實際上是事情本身(或概念)在思維中進行自我分解并將其自身呈現出來。
上文的梳理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三個結論:(1)以《邏輯學》為核心的科學體系,整個地是概念與事情本身相同一的,或者說是事情本身的自我認識,而不是人從自身出發對事情本身進行的任何操作;(2)科學體系并非主觀觀念的抽象游戲,也不探討什么超越之物,它只是在上述同一性的基礎上探討我們生活于其中的這個世界;(3)這個探討當然必須借助思維來進行,但思維在概念上的推進所透顯出來的,卻是事情本身借此進行的越來越深的自我呈現。
如果說《精神現象學》的“絕對知識”章還站在體系的門檻,對于概念與事情本身的同一性結構的預示還略顯“外在”,那么《邏輯學》開篇則引我們登堂入室,使我們窺見其內部結構。黑格爾首先再次確認,在《邏輯學》及其引領的哲學科學中,概念與事情本身(即存在)是同一的。在邏輯學中,“一個主觀地自為存在著的東西和第二個存在者、一個客觀東西在意識中的對立,被意識到是已經克服了的,而‘存在’被意識到是自在的純粹概念自身,純粹概念也被意識到是真正意義上的存在”,雖然在這里純粹概念和存在也被當成可以分別談論的“兩個環節”,但“這兩個環節現在卻被意識到是不可分割地存在著的”(13)[德]黑格爾:《邏輯學I》,第38頁;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I, S. 57.。這就意味著《邏輯學》的讀者必須達到“純粹概念”與“存在”的同一性的層次,才算具備閱讀的基本條件。與此相應,“純粹科學以擺脫意識的對立為前提”,即以《精神現象學》中意識對真理的整個探索歷程及其全部成果為前提,不再以意識的經歷為主題,也不再從意識出發看問題。由此看來,“純粹科學所包含的思想同樣也是自在的事情本身,換言之,純粹科學所包含的自在的事情本身同樣也是純粹的思想”(14)同上,第27頁。。換句話說,哲學科學立足于事情本身,呈現事情本身的自我運動。為表明邏輯學并非脫離質料與現實事物的那種純主觀形式,黑格爾還稱這種與事情本身合一的思想為“客觀的思維”和“純粹的思想”,它是合質料與形式為一的(15)同上,第27頁。。這意味著《邏輯學》中的全部范疇,無論看起來是“偏主觀的”還是“偏客觀的”,都既是概念(人對事情本身的某個環節或階段的理解),也是事情本身(世界之可理解的客觀結構的某個環節或階段)。
這個切入點能為我們把握此書提供極大便利。由此望去,《邏輯學》的整體結構便一目了然,它談論的都是上述同一性不斷深化自身的過程。“存在論”談到的“存在”只是“自在的概念”,即“實在性或存在的概念”,而“概念論”談到的純粹概念才是“概念本身”,或“自為地存在著的概念”,邏輯學就是從研究前者的邏輯(“作為存在的概念”的邏輯或存在論,屬于“客觀邏輯”)向研究后者的邏輯(“作為概念的概念”的邏輯或概念論,即“主觀邏輯”)的進展(16)同上,第39頁。。而居于這二者之間的是反思二者關系的邏輯,即研究“作為反思規定的體系的那種概念”的邏輯。在這種邏輯中,存在已經“向著概念的內化存在(Insichsein)過渡”,開始具有內外二分的結構,但與外在的直接存在還有千絲萬縷的關聯,畢竟還算不上“自為地存在著的概念”。這個居間的邏輯即為本質論,而本質論與存在論統稱為“客觀邏輯”(17)[德]黑格爾:《邏輯學I》,第39頁。。
由此可見,概念與事情本身的同一實為《邏輯學》一書的入門法要。這種同一性極端重要,它既是《精神現象學》的終點,又是《邏輯學》的起點,因此絕不能輕輕放過。目前的問題在于,黑格爾在《邏輯學》的開篇預設讀者已經通透掌握了《精神現象學》的整個歷程,因而并未對這種同一性著墨太多,使初學者對于一些關鍵問題不明就里:它是其來有自,還是黑格爾獨創的?是現成對象的事后統一,還是事情本有的深層特質?是一成不變因而可以一蹴而就的,還是逐步展露因而需要艱苦勞作的?以下試分別論之。(1)黑格爾所謂概念與事情本身的同一性,絕非空穴來風,而是源自巴門尼德以來西方古老的“思有同一”傳統(18)黑格爾明確將自己的邏輯學溯源到古代哲學的邏各斯,以及阿那克薩戈拉、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參見[德]黑格爾:《邏輯學I》,第17、28、11頁。。后者并非僅見于巴門尼德、笛卡爾、德國觀念論者等少數明確探討過這一現象的思想家,而是西方哲學一以貫之的一個傳統。從深層次看,它是西方形式觀的一種表現。而西方形式觀由畢達哥拉斯、巴門尼德、赫拉克利特最初提出,由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決定性地奠基,進而通過中世紀哲學、近代理性觀影響至今。這種形式觀深刻洞察到事物的本質不是在物質中生成的,而是與物質同等原初并將事物內在凝聚起來的規定性秩序,它既是僅由人類理智才能把握到的知識性要素,又是事物的存在本身所仰賴的客觀結構,思維和存在均以這秩序為旨歸,它也標志著思(思維)與有(存在)的根本同一性。(2)只要我們不在現成的意義上將思維與存在分別等同于人隨意的“念頭”與事物的“屬性”,并在此基礎上思考二者如何勉強“統一”起來,而是反過來追索思維與存在這二者的條件,就必定會洞察二者在根本上具有同一個形式結構。具體到德國古典哲學內部,黑格爾所理解的概念與事情本身的同一以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開啟的既先于主、客體而又成為二者共同結構的先驗要素為先驅,又不像康德那樣始終沒有擺脫主體意識的立場。他不再糾纏于表象與對象的關系問題,而是基于謝林開拓的事情本身的觀念東西與實在東西的同一性的新格局之上看問題(19)莊振華:《略論謝林自然哲學的開端》,《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3)但這并不意味著思維在《邏輯學》中一開始就達到最完善的思有同一,后者要通過對歷史上各種概念、范疇艱苦卓絕的“純化”與系統化工作,在《邏輯學》結尾部分才能達到。具體到《邏輯學》內部而言,黑格爾從思維最初認為最直接也最確定,實際上最抽象也最膚淺的“純存在”出發,通過以三種方式分別在三個層面進行的概念演進,使事情本身越來越深入、廣闊地展露自身。
以此觀之,黑格爾的著述歷程將顯示出更深刻的歷史意義。《精神現象學》在意識體驗與精神史的層面上系統梳理了近代理性的危機:它看似一往無前、開疆拓土,實際上無往而不在自身編織的“合理性”之網中,因而總是自外于事情本身(尤見于“理性”章全章);它看似以理性眼光一統天下,實際上繼承了中世紀教化格局下的分裂困境,陷入“優美靈魂”式的偽善而不自知(尤見于“精神”章第三節)。在這個背景下,《邏輯學》將上述同一性作為起點,實際上延續了《精神現象學》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系統地克服了近代理性的分裂困境(20)莊振華:《〈精神現象學〉義解》,第357—373、509—521頁。。它遠非提出一套學院理論那么簡單,實際上蘊含著拯救西方形而上學乃至校正西方文明的“大事因緣”(21)本文雖然擷取《精神現象學》《邏輯學》的若干論述表明,閱讀后書應以對前書的通透理解為前提,但這些論述背后的問題意識(化解近代理性的分裂困境)才是這種前提關系的根本原因。See Rosen, The Idea of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p. 233; M. Quante, “Die Lehre vom Wesen. Erster Abschnitt. Das Wesen als Reflexion in ihm selbst”, in ders. (et. al. hrsg.), Kommentar zu 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 Felix Meiner Verlag, 2018, S. 278.。
二、展開方式:思維與事情本身的雙重進展
抓住《邏輯學》的邏輯起點(概念與事情本身的同一)之后,緊接下來我們面臨的任務便是理解它的進展方式。《邏輯學》以事情本身的徹底展露為目標,為了達成這一目標,立于起點的純粹思維還需要經歷性質截然不同的三個層面,而這三個層面又各有切入點與演進方式。掌握《邏輯學》在總體與細部兩方面的演進方式,才能真正進入這部書的堂奧。以下試按這兩方面分別論之。
當人們對《邏輯學》繁復而又嚴謹的結構贊嘆不已時,往往容易隨之生出一種誤會,認為它是黑格爾這位高超的哲學家絞盡腦汁炮制出來的一部杰作,書中那些概念的進展路線完全是黑格爾自己構想和補綴而成,普通人只能瞠乎其后、無法復制。這種想法在將黑格爾神秘化的同時,也堵塞了真正理解這部書的道路。實際上,黑格爾本人并不認為《邏輯學》純粹是他個人頭腦風暴的產物,他認為自己只是忠實記錄了他所見的事情本身具有嚴格必然性的演進過程。具體而言,這個演進過程表現為思維的進展(“前行”)與事情本身的深化(“回歸”)兩條路線相伴相生、相得益彰的奇妙結構。黑格爾明確指出:“人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很本質的觀察——它在邏輯學中會更詳盡地展現出來——,即前行(Vorwürtsgehen)乃是回歸到根據,是向原初東西(Ursprünglichen)和真實東西(Wahrhaften)的回歸(Rückgang)。”(22)[德]黑格爾:《邏輯學I》,第49頁。
這里尚需對上述演進結構的必要性作一申論。在《邏輯學》中,雖然所有范疇都具備概念與事情本身相同一的特質,但這些范疇在性質、深淺上均有所不同。簡言之,這些范疇內部仍有偏重于抽象概念還是偏重于純粹概念(23)抽象概念即主觀概念,因而屬于客觀邏輯;純粹概念即事情本身的內核,因而屬于主觀邏輯。《邏輯學》中“客觀邏輯”與“主觀邏輯”的區分當然不是從人的意識出發,而是從事情本身出發作出的,抽象且表面的、反映事情本身的自在存在的是客觀邏輯,具體且深入的、反映事情本身的自為存在的是主觀邏輯。參見[德]黑格爾:《邏輯學I》,第39頁。的區別(24)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整個區別都發生于事情本身內部,而不發生在常識意義上的現成事物層面,因而不可誤認為《邏輯學》的演進是從主觀觀念向客觀事物的進展。為此,黑格爾在《大邏輯》第二版序言中專門強調,《邏輯學》的對象不是常識意義上的事物(Dinge),而是那與概念同一的事情(Sache)。參見[德]黑格爾:《邏輯學I》,第17頁。。這便是黑格爾反復強調的概念進展與事情本身自我展現的共生關系,兩者不可偏廢。事實上,在概念不斷“生成”的這條“明線”背后,隱藏著事情本身越來越深地自我展現的“暗線”,后者往往不為論者所提及、但其實更重要,它是真正的動力之源(25)所謂“明線”,是指人們往往只見書中許多概念依次出現,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下往往容易認為每個概念僅僅是從先前的概念中“生成”的。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其背后隱藏著事情本身從最表面、最抽象的直接性“存在”層次向最深刻、最具體的思辨性“概念”層次逐步展現自身的過程,后者由于容易為人忽視,故稱為“暗線”。。
在最一般的意義上可以說,《邏輯學》所有三元結構都有一個大致類似的特征,即它內部的三元分別是直接存在的環節(自在的環節)、反思性的環節(自為的環節)和思辨性的環節(自在且自為的環節)(26)正如上節末尾提到的,在這種表面看似僵硬的三分背后,隱藏著黑格爾克服近代理性的分裂困境的現實考慮。從邏輯學的“存在論”“本質論”“概念論”的三分到各部分內部的種種三分都是如此。但三分本身并非絕對必然的,只要能體現上述進展,二分或四分也是可以的,比如“概念論”的“認識的理念”就是二分的,他的其他著作也有四分的情形(如《自然哲學》的“特殊個體性的物理學”、《歷史哲學》的歷史分期等)。。但“三論”(27)指“存在論”“本質論”“概念論”,下同。在體現這種格局時又各有側重,分別自成一體。黑格爾曾在《小邏輯》第161節及其“附釋”中將“三論”的進展方式分別概括為過渡(übergehen)、映現(Scheinen)和發展(Entwicklung)(28)[德]黑格爾:《邏輯學——百科全書·第一部分》,梁志學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5頁;Hegel, Enzyklop?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Erster Teil. Die Wissenschaft der Logik, Frankfurt a. M.: Suhrkamp Verlag, 1970, S. 308.。(1)在“存在”層面,事物都直接存在,且僅僅呈現其“存在著”這一點,事物與事物之間也缺乏深層次關聯,相互之間除離散的“并存”外并無其他任何關系,因而思維總是只能從一個事物或一種規定性直接轉向另一個事物或另一個規定性(“過渡”)。這種直接過渡帶來的認識只不過是“有……,又有……”這種外在的并列,因此便有“量”這種典型的外在化格局。(2)在“本質”的層面,每個事物內部以及相互之間都呈現出深層次的本質,是為“反思規定”。整個世界呈現為深淺有別的一個立體結構,任何事物的定義、活動與關聯都必須在這個立體結構中進行。在這個結構中,所謂的“內在”(本質)與“外在”(現象)實際上是相互賦予意義的,任何一方在缺了另一方的情況下都沒有意義(“映現”)。(3)在“概念”層面,事情本身突破“本質論”無限繁復的反思結構并為之奠基的那種根本統一性才是一切的關鍵,而以往的所有范疇不過是這種統一性深淺不同的種種體現形式,都是它的自我展現(“發展”)(29)[德]黑格爾:《邏輯學I》,第17頁。。
上述三種進展方式,在“三論”中分別最典型地體現在“存在”“反思”“推論”三個范疇上,而這三個范疇又分別對“三論”有全盤輻射之功效(30)“輻射功效”指的是,從這三個“切口”入手會很容易發現“三論”的構造方式,因為它們可以分別看作與這三個范疇類似的一系列直接的存在、反思性判斷、思辨性推論。但嚴格來說,這種功效可能并非這三個范疇所獨具的,本文只是以它們作為典型例子,提出一條由簡入繁地進入《邏輯學》的可能路徑。。抓住了這三個范疇,“三論”便不難理解。
第一,在“存在論”中,黑格爾開門見山地介紹了“存在”范疇,后者展開為“存在-虛無-變易”這個三元結構。事物最初向人直接顯現為“存在著”,思維對事物的了解僅限于“它存在著”;這種肯定其實直接蘊藏著否定在內,因為存在之所以直接成其為存在而毫無其他中介,恰恰是由于它的無規定性即其否定性;但這里的否定又不是徹底的虛無,而是與肯定相關聯的否定,世界上永遠只有從有到無的過渡(消失)和從無到有的過渡(生成),二者合起來即為“變易”。這個三元結構的總體特征是:相對于在前的環節,在后的環節雖然在思辨性上有所推進,但只是以最直接、最抽象的方式在推進,它們中的每個都不具備“本質論”與“概念論”的那種深度。
“存在”范疇展示的這種直接過渡的演進方式體現在整個“存在論”中。(1)第一部分名為“規定性(質)”,是因為這一部分的整個論述僅僅涉及事物的最表面規定(“存在著”)。“存在”范疇作為第一章,揭示出最直接的存在總已經具有否定性,但目前的這種揭示本身還是最抽象的。換言之,“存在”的三元結構并沒有完全自足的存在,只能體現在具體事物中,這便直接從“存在”過渡到“定在”。具體事物之為具體事物,是因為它總是“某物”,即某個特定的事物或者說有限度的事物。這種限度之為限度,本身就意味著在它之外還有它的否定物,或者說意味著超越該限度的可能性。任何事物都是在限度與對限度的超越這兩種規定性的交互規定下維持其獨立存在的,后者就是“自為存在”。但各個事物的獨立存在還遠遠不能代表事情的全部,因為無論一事物還是它的種種規定性,其獨立存在都不能單純依靠堅守自身并排斥他物,而是需要在世界上所有同類事物或同類規定性構成的序列中占據特定位置,這種相對而言的位置便是大小(量)。(2)由此進入第二部分,即“大小(量)”。一切大小都是就事物相互對比而言的,因此量雖然乍看起來就像事物自身的性質,但本質上只能表明事物與事物之間的外在比較。量的范疇起點是獨立存在(自為存在)所具有的一個根本特征即連續性,而本部分第一章(“量”)是在抽象意義上討論量,僅能顯示出事物的這種連續性“具有大小”這一點,此外無他。這意味著從外部考察事物的連續性的范圍及界限,而沒有進入這種連續性內部進行分疏。一切現實的連續體都是有界限的,這樣的連續體就其自身而言是連續的(kontinuierlich),就它們相互之間而言則是離散的(diskret)。最終我們看到的是量本身的限定,即量的數值(“數”)。第二章(“定量”)討論的是帶有數值的量,開始進入量的內部,看待它的各單元之間的關系。此時對外、對內分別出現的不再是上一章中連續的量與離散的量,而是外延的量與內涵的量。需要注意的是,定量內部各單元之間被設定為相同的,所有單元都只是具有一定數值的眾單元“之一”;這種考察方式看似只針對定量內部在進行細化,實際上同步設定了數值無限進展的可能性,即設定了具有其他數值的定量與這一定量進行比照的可能性。這便是第三章(“量的比例”)要探討的內容。比例的本質在于兩個或多個事物靜態或動態的相互關系,而不在于現成化理解下的除法算式的結果,比如誤認為2:1的“結果”為2。比例概念處理動態關系的極致便是探討無窮趨近關系的微分學。(3)第三部分名為“尺度”,討論的不再是“量”這種外在的相互關系,而是具有規定性(質)的量。這是整個“存在論”中最具思辨性和深度的一部分,也是最接近于“本質論”中里那種內外二分格局的一部分。在思維還不懂得像“本質論”那樣通過設定“內在本質”來解釋事物的情況下,它要解釋事物“何以存在”時,最多只能看到并描述“事物各以一定的節奏、尺度存在”,如某種候鳥幾月才南飛、某種樹木長到多高就由盛轉衰等,但并不知其所以然。這當然算不得對事物存在的“理由”的說明,但總比僅僅宣布事物“存在著”顯得更“深刻”一些。這一部分依然從抽象化看待事物的“度”入手(第一章),令讀者看到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以“特殊化的尺度”為標志的;進而通過這樣的各種獨立尺度之間的比例關系來說明事物與事物之間的復雜關聯(第二章);最后探討這樣的比例關系如何過渡到“本質論”中的二分格局(第三章)。
第二,“反思”范疇對于“本質論”具有同樣的定向作用。黑格爾將反思分為進行設定的反思、外在的反思和進行規定的反思。進行設定的反思直接且固執地認定在現象的背后必有本質,而且依靠后者、貶低前者,但它是一種不對自身進行反思的反思,因而它拒絕承認上述認定有何局限。外在的反思則開始進行這種反思:它發現前一種反思僅僅是一種進行“設定”的反思,但設定(Setzen)必有其預設(Voraussetzung),即“存在論”結尾那種被揚棄了的存在;它還發現現象與本質其實是相互依賴的,二者只有相互比照才有意義。但這不是事情的全部,因為到目前為止現象與本質依然是相互外在的。反思至此終于發現,到目前為止的這種相互外在的狀態其實是事情本身的一種比較淺層的表現形式,或者說只是事情本身在某些階段的表現。這就是說,真正起決定作用的并不是與現象相對而言的本質,而是事情本身的自我設定,而現象與本質都是這種自我設定的產物。至此,反思成為進行規定的反思。進行規定的反思既未失去對“本質”的追求,也不拋棄現實事物,而是兼具這兩種性格,它實際上是對前兩種反思的成全(31)[德]黑格爾:《邏輯學》下卷,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16—26頁;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II, Frankfurt a. M.: Suhrkamp Verlag, 1969, S. 25-35.。
相對于“存在論”,“本質論”面對的雖然是同一個世界、討論的是同樣的事物,但事物在這一部分處處都具有內在本質與外在現象二分的反思性結構,思維也總以這種二分的方式來看待事物。(1)在“本質論”第一部分(“作為自內反思的本質”)中,本質性東西與非本質性東西既相互對照又并非相互外在的,而是互為對方的條件。這一部分的缺陷在于,它對這種“自內反思”的了解畢竟還很抽象。思維只是外在地比較事物的種種規定的同一、區別與矛盾,直至最終認定任何事物都有其內在根據,但并不真正了解那根據是如何內在地起作用的。這導致各種規定相互之間終究還是外在的關系。(2)第二部分雖名曰“現象”(Erscheinung),探討的是作為自在之物(Ding-an-sich)或自在存在的世界(die an sich seiende Welt)之顯現(Erscheinen)的現象,即本質與現象更加內在融合之后的整體,而非僅僅討論與本質抽象對立的現象。這一部分從“實存”(Existenz)開始,表明思維在對根據有充分信心的基礎上,發現了事物的外部實存便是根據的“落實”之處,開始重視這種實存。在這一部分,實存與其根據之間的內在關系開始系統呈現出來。這就是說,思維在現象世界中發現事物內部及其相互關系中大有乾坤,那就是規律。規律思維關于現象與現象背后的“真相”二分的格局的設想,實際上無法長久撐持,因為思維終歸會發現對偶然的規則性現象的歸納并不能代替真理本身(32)莊振華:《黑格爾論規律》,《哲學動態》2017年第2期。。于是到了第三章,思維只得承認前此為止達到的種種二分格局,其實只是事情本身的呈現方式,只具有有限的意義。(3)“本質論”第三部分(“現實”)可以視為連接“客觀邏輯”與“主觀邏輯”的核心樞紐,蘊藏著使黑格爾不同于過往所有思想家的關鍵特征。經過書中“存在論”和“本質論”的漫長跋涉之后,思維認識到絕對者并不是一種與現實相對立的東西,而是就在現實中且成為現實的核心。“絕對者”章在抽象反思的意義上闡述絕對者在現實中何以可能。“現實”章不再局限于對現實中的絕對者的抽象描述,而是致力于展示現實事物的一切規定究竟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實際上,我們并不能抽象地斷定現實事物的偶然性或必然性,偶然和必然都是相對于事情本身的展露程度而言的。所謂必然,便意味著人認識到事物展現了其與絕對者的深度相互內在。但僅僅了解絕對者與現實事物的相互內在還不夠,還必須明了這種相互內在的究竟,這便有了“絕對關系”章。這一章談論是作為絕對者的自我表現的實體性、因果性和交互作用:實體性代表體現了絕對者的現實事物的持存性,因果性代表它們的關系格局的堅實性,而交互作用則代表這些事物都由里及外地徹底實現絕對者的臨在。
第三,黑格爾向來認為真正適合于表達思辨思想的方式不是概念和判斷,而是推論。因為就本質性功能而言,概念直接言說普遍性(Allgemeinheit),判斷只能顯示個別性(Einzelnheit)向普遍性的單向過渡,只有推論才能展現個別性通過特殊性(Besonderheit)這個中項與普遍性動態地結合的情形,即展現出普遍性不在個別性之外、而就在個別性內部,或者說展現出個別性與普遍性之間的往復運動。這樣看來,只有推論才能展現出“本質論”的最高范疇“現實”的內部結構。因而,“概念論”中各組三一體的演進方式在本質上都是推論。
雖然“概念論”整個被黑格爾稱作“主觀邏輯”,它的第一部分也徑直名為“主觀性”,但正如上文表明的,這里所謂的“主觀”指的根本不是個人主觀觀念,而是世界在抽象意義上的可理解性,即單純抽象意義上談論的“如何理解具有統一性的世界”。與此相應,第二部分(“客觀性”)也并未討論常識意義上的“客觀”,而是可以視作黑格爾對于“思維應該對客觀性采取何種態度”這個問題(33)可比較[德]黑格爾:《邏輯學——百科全書·第一部分》,§. 26—§. 78。的回答:他認為既不能像康德與經驗論者那樣懷疑思維具有客觀意義,或抽象地設定一個彼岸的“物自體”;也不能像雅可比那樣迂回到反思性規定的背面,抽象地崇奉直覺;而是主張一條間接的知識之路,即在信任思維規定具有客觀性的同時,主張將思維的反思規定推進到思辨的認識,在思辨的認識中把握事情本身。第三部分(“理念”)談論的是在世界上實現了的絕對者本身,或者說世界萬物的絕對統一性本身。(1)在“主觀性”部分,黑格爾關注的并不是作為思維工具的形式邏輯,而是處處打破這種抽象的工具性,著意于尋找思辨的突破口,即尋求在個體事物中理解絕對者的最佳途徑。當然,這并非什么主觀任意的尋求,它具有事情本身的必然性。概念作為直接的共相,在表達個體事物的情形方面是有局限的。不同于后來的分析哲學家通過直接劃分專名與摹狀詞來巧妙回避追問概念之本性的做法,黑格爾直面這個問題。概念的局限性在根本上是由于概念這種直接的思考方式不能觸及一個間接且思辨的事實,即個別事物以超出它自身之外的統一性為根據。判斷也有其局限,因為它雖然能展示概念之間的過渡與相互關聯,也能展示個體事物與共相之間的反思性關聯,但僅止于此,它終究會使思維陷入諸種反思規定之中而看不到超出這些規定的真正統一性。推論表面看似判斷的疊加,但它的獨特性恰恰在于,判斷與判斷之間的內在運動不能被肢解為相互分離的個別判斷,而這種內在運動正是絕對者在種種反思規定中的體現方式。由此,思維才具備真正理解客觀性的條件。(2)如前所述,黑格爾對“客觀性”的看法迥異于前人。機械性是外在的觀察方式,也是事物外在的呈現方式。這種外在方式本身并沒有什么“錯誤”,只是比較膚淺,只能通過越來越深地劃分“內-外”結構的方式,在事物那里達到一種不斷“深入”的假象。但這種“深入”的最深刻成果不過是規律,而如前所述,規律在本質上只是經驗的外在歸納,并未真正抓住事物的內在本質。如果在事情本身自我呈現的意義上看,機械性其實是邁向事物反思性的內在結構的一個必要步驟,后者便是化學性。化學性令人看到事物本就發生了內在融合,事物的存在本身就要以化學反應過程為條件。但僅僅停留在化學性層面還不夠,這個層面說到底還是預設了化學性與事物的兩分。只有承認“事物自身就以內在融合為真正的存在方式”即承認目的性,才達到客觀性的頂點,這便跨入生命領域的前門。(3)“理念”部分討論的是實現于世界上的概念,或者說世界上現實的統一性。理念首先表現為生命,后者既體現出個體的統一性,又在類的意義上將各種個體統一起來,但生命畢竟是最直接、最抽象的理念,還沒有達到自覺的反思,更沒有達到對世界的根本統一性的思辨。第二章表明在理念層面而非在人的理論活動與實踐活動的層面(后者屬于反思的層面)來看,真與善不是基于人的立場分別進行靜觀與行動所達到的極致狀態,而是世界萬物的內在生命分別通過靜觀與行動達到的對自身本質的反思。到最后一章,在絕對理念的高度來看,真與善兩種理念終歸于一,由此達到世界的絕對統一性和絕對可理解性。這種統一性與可理解性之所以是絕對的,是因為它其大無外,是世界的終極根據,其本身再無任何條件。
三、余論:互文關聯問題
研究《邏輯學》,除了必須從適當的起點出發和遵循該書特定的進展方式之外,還需留意該書與黑格爾其他著作之間的關聯。一方面,這種關聯是黑格爾本人加以肯定的,如果完全置之不顧,在閱讀黑格爾其他著作時就會迷失方向。黑格爾自耶拿時期開始,就常常在課程預告和手稿中以“邏輯學與實在哲學”概括自己的體系規劃(34)如1805-1806年體系草稿《自然哲學與精神哲學》的副標題便是“實在哲學講演錄手稿”,遵循了黑格爾本人的意圖,也就是將這兩門哲學合而言之,與邏輯學形成對照。。總的來說,黑格爾基本上是用“客觀邏輯”(“存在論”和“本質論”)代替傳統的本體論(或曰“存在論”)和形而上學(35)[德]黑格爾:《邏輯學I》,第41頁。,并補充了前人所沒有的“主觀邏輯”(“概念論”)。這樣形成的整部《邏輯學》當然對作為部門哲學的其他體系著作(《自然哲學》《精神哲學》以及各種講演錄)具有指導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將其他體系著作視作《邏輯學》的某種“應用”。在《大邏輯》中,黑格爾還曾說這書展示的是“上帝在他的永恒本質之內、在創造自然界和某種有限精神之先,呈現出來的樣子”(36)同上,第28頁。。這就更強化了《邏輯學》作為其他體系著作的“先行規劃”的地位,令人更難忽略雙方之間的深層關聯。另一方面,如果過分執著于這種關聯,以致誤認為《邏輯學》與其他體系著作之間,甚至與《邏輯學》之前的著作之間存在僵硬的對應,就會出現如亨利克斯(J. Heinrichs)的那種頗顯滑稽的做法,即逐章逐節地把《精神現象學》與《邏輯學》對應起來(37)J. Heinrichs, Die Logik der 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Bonn: Bouvier Verlag Herbert Grundmann, 1974.,實乃圓鑿方枘,捍格難入。那么,在這個問題上應該如何掌握合適的尺度?筆者以為,兩類著作之間的橫向關系的研究,必須建立在充分尊重各著作內部獨有的縱向結構的基礎上。我們應該更重視雙方的“神似”之處,而非“形似”之處,在比較閱讀時應該有所“節制”。倘若如此,我們會發現兩類著作在總體框架與細部概念上完全可以形成良性的互鏡關系(38)互鏡關系指兩類著作在閱讀中形成互為鏡鑒、相互啟發的關系,如下文在整體和細部所舉的兩例。,而不致陷入“概念推演”的表面比附,甚至由此制造出一些本不該存在的偽問題。比如,在總體框架上,如果不了解《邏輯學》“三論”之間的邏輯關系,《自然哲學》《精神哲學》《法哲學原理》各自內部的三大部分之間的關系就無法理解到位。甚至《精神現象學》中的許多問題(比如自我意識的本質、精神與理性的關系等),也要從《邏輯學》反觀才能得到通透的理解。在細部上,這類互鏡關系更是比比皆是。
正如德國古典哲學的所有經典文本的情形一樣,對《邏輯學》的閱讀與研究始終在路上,是一個無盡的過程。本文只是就《邏輯學》研究的起步、推進和效應這三個問題,提出了一些最初步的看法,希望拋磚引玉,就教于學界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