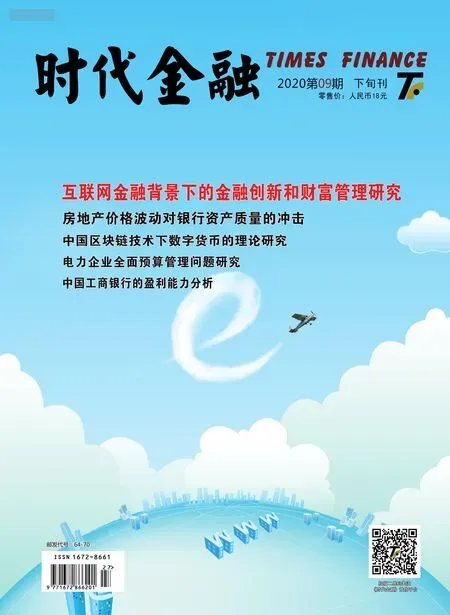高鐵、信息化水平對金融產業集聚的實證研究
郭文杰


摘要:本文采用長三角地區26個城市2009-2017年的面板數據,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實證分析了高鐵開通和信息化水平對地區金融產業集聚程度的影響,并采用二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對模型進行了內生性檢驗。通過本文的實證結果可以得出高鐵開通和信息化水平對地區金融產業集聚具有顯著性的正效應。通過高鐵建設和信息基礎建設的回歸系數可知,信息基礎建設對金融產業集聚的正向效應遠遠大于高鐵建設對金融產業集聚的正向效應。
關鍵詞:信息基礎建設 高鐵建設 金融集聚 內生性檢驗 穩健性檢驗
一、引言
自20世紀開始,倫敦、紐約、東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在全球的影響力日趨加深,同時隨著經濟水平的發展,世界各國金融產業集聚現象越來越明顯,金融產業集聚問題越來越成為經濟學研究的熱點。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我國金融產業集聚現象日益顯著,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出現了以上海陸家嘴和北京金融街為代表的金融中心。近年來,我國各大城市都在積極建設地方金融中心,因此研究金融產業集聚的影響因素對于地方建設金融中心具有一定的意義。綜合國內外文獻來看,大多數學者從經濟發展水平、地理位置、政府干預程度、對外開放程度、產業結構等角度來研究對金融產業集聚的影響,本文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上,特別是近年來我國高鐵建設如火如荼,高鐵因其時空壓縮效應顯著縮短了地理距離,促進了人流、信息流的流動,同時伴隨著5G時代的到來,信息基礎建設和通信技術水平的提高,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產業集聚,因此本文從高鐵建設和信息基礎建設的角度來實證分析兩個因素對金融產業集聚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分析
(一)金融產業集聚
金融產業集聚是金融產業空間動態演進的結果。國內外學者的實證結果表明金融產業集聚已成為金融業發展的趨勢,金融產業集聚能夠促進金融發展和金融效率提高(Taylor 等,2003;Christophers,2012),金融產業集聚逐漸成為區域經濟競爭力的中堅力量。
其中以戴維斯(Davis,1988,1990)、泰勒(Taylor,2003)、潘英利(2003)等從區位選擇理論分析了金融產業集聚的動因,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 ,1974)、黃解宇和楊再斌(2006)等從規模經濟理論探究了金融產業集聚的影響因素,格里克(Gehrig,1998)、馬丁(Martin R L.,1999)等運用金融地理學理論從信息的角度對金融產業集聚的成因進行闡釋。
(二)高鐵建設與金融產業集聚
近年來,我國高速鐵路建設飛速發展,“高鐵”效應成為學者們研究的熱點問題。已有學者研究高鐵對相關產業的影響,如汪德根等(2012)、丁金學(2014)、嵇昊威等(2015)覃成林(2016)、鄧濤濤等(2017)等。高鐵對產業集聚的理論基礎來自于新經濟地理學,高鐵對產業集聚的影響源于高鐵開通帶來的交通運輸成本的降低,而交通運輸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促成產業集聚。高鐵顯著提高了人流、信息流、資金流等在運輸過程中的時效性,同時提升了交通可達性。交通可達性的提升對產業集聚有著重要的影響力,同樣,可達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區域的競爭力和城市的吸引力。
通過對已有學者們的研究發現,高鐵建設對相關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具有顯著地促進作用,同時結合學者們對金融產業集聚影響因素的分析,發現并沒有學者細化高鐵建設對金融產業集聚的影響,因此本文以長三角地區26個城市群為例,實證分析了高鐵對金融產業集聚的影響。
(三)信息基礎建設與金融產業集聚
由于金融產業信息的不對稱性,因此必然需要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從而達到信息共享。Porteous(1999)和王坦(2006)等強調信息流在金融產業集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對已有學者的研究發現,學者們已經在信息對金融產業集聚的重要影響上達成了共識,因此本文進一步探討信息基礎建設對金融產業集聚的影響機制。首先,信息基礎設施是信息有效流轉的基本物質條件,是影響信息流的重要因素,能降低交易成本;其次,信息基礎建設能夠縮短企業之間的信息傳遞的地理距離,提高信息傳遞的實效性,降低信息傳遞的成本,隨著互聯網信息時代的到來,即使企業相距甚遠,也能隨時傳遞信息,從而導致產業產生“虛擬集聚”。
三、實證分析
(一)變量說明
被解釋變量。本文選擇金融產業區位熵(FLQ)測算我國金融產業區域集聚程度。區位熵是衡量產業集中度的重要指標,可充分比較不同地區金融集聚程度,確定該地區金融產業集中程度在全國所處的位置。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Lij指地區i內產業j的就業人數,Li指地區i內的總就業人數,Lj指全國內產業j的總就業人數,L指全國的總就業人數。區位熵的值越大,該區域的金融集聚程度越高。一般認為,如果FLQij大于1,意味著金融產業在區域比較重要。
解釋變量。本文將金融集聚的影響因素分為核心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兩組。
本文核心解釋變量有兩個,一個是高鐵開通時間虛擬變量(ot),本文以2010年作為基期,2010年開通高鐵的城市取值為1,2010年未開通高鐵的城市取值為0。另一個是信息化水平(ict),本文參考梁琳(2016)的信息基礎設施指標選取方法來反映各城市的信息化水平。
控制變量包括以下4個變量:
一是經濟發展水平(dec),本文以各城市人均GDP與全國人均GDP的比值來反映各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
二是創新能力水平(ivon),本文以各城市專利授權量的對數來反映各城市創新能力水平。
三是通信水平(ptr),本文以各城市郵電業務量與全國郵電業務總量的比值來反映各城市的通信水平。
四是全社會用電量(ec)。本文以各城市全社會用電量反映各城市能源消耗情況,該指標能夠反映出各城市經濟活躍程度和社會活躍程度。
(二)模型設定與數據來源
根據以上理論假說及變量的選擇,本文的線性模型形式設定如下:
式中,β為待估計參數,下標i和t分別代表第i個城市和第t年,εit為隨機誤差項。
本文數據包括長三角地區1個直轄市和25個地級市2009-2017年的統計數據,數據來源于上海市統計年鑒(2010-2018)及各省、市統計年鑒(2010-2018)。
(三)模型估計
本文利用軟件stata14.0對面板模型進行估計,定量分析核心解釋變量以及控制變量對金融產業集聚程度(FLQ)的影響。首先混合回歸,由于混合回歸的基本假設是不存在個體效應,對于這個假設必須進行統計檢驗,由于個體效應以兩種不同的形態存在(即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因此本文分別進行固定效應模型估計和隨機效應模型估計。然后通過 Hausman 設定檢驗判斷使用固定效應模型或者隨機效應模型,根據hausman檢驗結果,由于p值為0.1336,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設,因此應該使用隨機效應模型,而不是固定效應模型。
考慮到面板數據模型的內生性問題,因此使用信息化水平的滯后一期(L.ict)和城鎮化率的滯后一期(L.urban)作為信息化水平(ict)的工具變量,使用二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對模型進行檢驗。工具變量的選擇考慮到慣性因素因此將信息化水平的滯后一期作為信息化水平的工具變量,另外由于城鎮化率的提高對地區信息化水平的影響,因此將城鎮化率的滯后一期作為信息化水平的工具變量。同時,通過stata14.0軟件得出城鎮化率的滯后一期(L.urban)和信息化水平的滯后一期(L.ict)與信息化水平(ict)有較強的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分別為0.6656和1.0000,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1中給出了固定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和二階段最小二乘法的回歸結果。從表1(2)和表1(3)的回歸結果看,兩個核心解釋變量對地區金融產業的集聚程度水平分別在1%和10%的水平上具有顯著性影響,且回歸系數都為正。
四、結論與對策
通過實證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結論:第一,高鐵建設顯著縮短了空間距離,提高了人力資本和信息的流動,對金融產業的集聚起到了顯著性的促進作用;第二,信息基礎建設水平的提高通過影響信息化水平顯著的促進的信息穩定流動和信息流轉的時效性,從而對金融產業集聚起到了顯著的正向效應。
根據本文得出的結論可以得到如下啟示:第一,根據國家《鐵路“十三五”發展規劃》的目標,我國2020年鐵路總里程要達到15萬公里,高鐵營運里程要達3萬公里,從該文件中可以看出,高鐵建設已成為國家戰略,同時在該文件中強調要發揮高鐵的經濟效應,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因此各地方應依托鐵路“十三五”規劃戰略,積極建設高鐵,從而提升金融產業集聚水平,促進城市金融中心的發展,為地區經濟發展提供強大助力。第二,信息基礎建設水平已經成為影響當今金融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信息技術的提高改變了傳統金融業的生存方式,5G時代的到來更會為金融業的進一步發展帶來機遇,因此各地方應加強信息基礎建設,提高信息化水平,為地方金融產業集聚發展提供關鍵支撐。
參考文獻:
[1]李小建.金融地理學理論視角及中國金融地理研究[J].經濟地理,2006,(5):721-725,730.
[2]寧鐘,楊紹輝.金融服務產業集群動因及其演進研究[J].商業經濟與管理2006,(8):38-44,66.
[3]潘英麗.論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觀基礎——金融機構的空間聚集[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3(2):50-57.
[4]陳建軍,陳國亮,黃潔.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來自中國222個城市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09(04):83-95.
[5]梁琳.信息腹地、空間溢出和金融服務業集聚關系研究[J].商業經濟研究 2016(10),171-173.
[6]覃成林,楊晴晴.髙速鐵路發展與城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J].經濟經緯,2016,33(03):1-6.
[7]任英華,徐玲,游萬海.金融集聚影響因素空間計量模型及其應用[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0(05):104-116.
作者單位:天津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