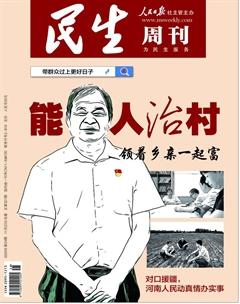浴火十年,林家兄弟圓了建盞夢
盧夢醒
火焰呈紅800℃、呈白1200℃、刺眼熾白1300℃,周期30天,工序13道,任何細小的差池都可能導致“全軍覆沒”。每次的爐前等待都像是等待一次審判,期望和恐懼疊加反復,一次又一次折磨,
這一切,原本和遠在上海經商的林子爐、林子照兄弟并無關聯。然而,在上海一次陶瓷展覽會上,他們被幾只宋代建盞深深吸引。多年以來,建盞成了林家兄弟生活的全部——夢想、困惑、徘徊、成功,建盞完全改變了他們的生活,他們的人生,也在復興建盞藝術的過程中不斷升華。
迷上建盞
上世紀70年代,韓國新安海域打撈出水一艘元代沉船。船艙中發現117件黑瓷茶碗,將人們的視線聚焦到日本博物館,其中,靜嘉堂館藏的“天目曜變”,被奉為天下第一碗。
據16世紀日本《君臺觀左右帳記》記載:曜變萬匹絹,油滴5000絹,兔毫3000絹。而當時,一人一年勞作所得僅兩匹絹。這些價值連城的作品是我國制瓷文化的代表之作,是璀璨的制瓷文明又一物證,是先人匠心獨運下爐火與瓷土相熔偶得天成的稀世佳器。
可惜,這一燒制技藝,早在800年前就失傳了。如果不是考古成果喚醒了沉睡淹沒的歷史秘辛,建盞藝術,不知何時才能走出歷史蒼穹,走進人們的生活。
隨著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中日間經濟文化交流活躍,國內一批陶瓷團隊埋頭鉆研,歷時兩年成功復燒出日本博物館藏有的建盞器型,而且,作品的水平完全可以和800年前媲美,有些作品還有時代創新,接續復興了一個時代的輝煌。
建盞制瓷藝術的復興,推動了社會上建盞熱的興起,一個行業也因此蓬勃興旺起來。
一大批燒制隊伍,活躍在建盞行業,制瓷大師級人物、藝術名家、精品力作大量涌現,其中就有林子爐、林子照兄弟。
碗中乾坤
2010年,林家兄弟放棄在上海經營多年的生意,舉家搬遷到建盞發源地——福建建陽水吉鎮。他們這一舉動,在親戚朋友看來是“瘋了”。
學習建盞燒制藝術,是一場艱苦備嘗的修行。歷時700多個日夜,在燒掉了100萬元之后,他們終于掌握了燒制建盞的全部秘密。
“曾經想過放棄,但偶爾有幾只盞出彩,就像長長黑夜里看到了一點點亮光。”這點亮光指引激勵著林家兄弟,堅持、堅持再堅持。他們用無數次失敗,終于做出了美輪美奐的建盞,呈現給世人。
林氏“黑曜銀斑”,與宋代留存展品放在一起,幾可亂真。宋代存世的“一盞萬色”,其胎土是建陽水吉鎮獨有的高含鐵瓷土,經高溫氧化結晶后,黑呈玄黑,被稱作一切顏色的原色,厚重沉穩,深邃大氣,在不同角度的光照耀下,又變化萬千,故名“一盞萬色”。
有宋一代特別是南宋,對黑釉茶盞的鐘愛是既潮又雅的事。鼎盛時期,大名鼎鼎的龍泉窯、吉州窯、景德鎮窯都在燒制黑釉茶盞,唯有建盞黑瓷最受青睞,尤其受到宋徽宗的鐘愛。
林氏龍鱗彩金系列,金斑紋包裹盞面,層次分明,如魚鱗狀呈片排列,盞壁立體如同陽雕。盞內幽深內蘊,仿若星河,號稱“碗中乾坤”。林氏鷓鴣斑系列,具有古傳的鷓鴣斑特征,在此基礎上創新派生的黃山松鷓鴣斑和綠鷓鴣斑系列,前者釉面華麗、釉汁肥厚,后者施釉較滿、胎骨致密。
油滴建盞的燒制比兔毫更難,因為,釉流動性大的情況下,需要晶體保持住斑點而不流成條紋,需要更加苛刻的條件。即使現代手段也難以企及,油滴是燒制兔毫時偶然出現的產物。
其實,稀世珍品“天目曜變”又何嘗不是偶得天成?傳說,此品為電閃雷鳴龍窯塌陷時,不能存而存之的“妖變之物”。
可遇而不可求,也許正是建盞匠人的追求吧。
人生超越
如今,林家兄弟的建盞作品已獲得國家、省、市多項榮譽,國內各大博物館陸續收藏了他們的作品,各類大師頭銜亦接踵而至。從生意人到一個傳承建盞文化的工藝大師,在歷經窯火浴化后,他們的人生也實現了超越。
建盞之所以美,在于造型釉和胎骨的完美融合,在這一融合中,展現了內斂、淡泊的人生意趣,有一種不靠裝飾干擾視線的美,是千錘百煉、千辛萬苦而得的美。
這樣的美是獨有的,用福建建陽水吉鎮的胎釉土礦才能燒出。隨著水吉建盞胎礦的大量開采,資源越來越少,建盞正面臨文化遺產傳承和接續的資源困境。林家兄弟以及眾多建盞大師,在用自己的作品弘揚建盞文化的同時,也熱切期盼有關方面保護好建盞文化獨有的自然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