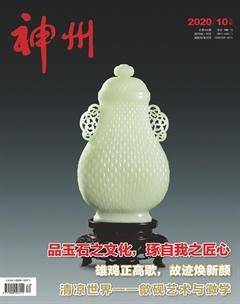“不能勝任工作”的解雇制度研究
萬昌豪
摘要:我國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對如何認定“不能勝任工作”未作出明確的解釋,只將舉證責任分配給用人單位,“不能勝任工作”的解雇制度在實踐中暴露出諸多問題,亟需從細化標準、確認合同效力以及擴大認定主體等方面進行完善。
關鍵詞:不能勝任工作;末位淘汰;解雇保護
一、我國“不能勝任工作”解雇制度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一)“不能勝任”的認定準則含糊
從“不能勝任”的法律條文來看,《勞動合同法》概括性的規定使得司法實踐中態度不一。在對勞動者主觀問題上。從法律規則的行為模式上看,《勞動合同法》將用人單位的調崗、培訓定性為必須履行的前置義務,有些法院將“不能勝任”的案例歸屬于前置程序糾紛,即勞動者拒絕單位的調崗或培訓的處理或衍生出的調崗后拒絕到崗而以曠工解雇的糾紛,法院在勞動者拒絕調崗態度上有所不同,有的將過錯歸屬于企業,有的則認為勞動者有過錯,這些都對“不能勝任工作”的認定標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不能勝任”的認定主體單一
現行勞動法將“不能勝任”的舉證責任只分配給用人單位,一方面提高了雇主濫用舉證權利的危險性,另一方面為了克服企業濫用權力規定了嚴格的證明條件,相關案件中企業敗訴的比例要遠大于勝訴;對于勞動者而言,法律剝奪了勞方的舉證權利,也增加了勞動者的維權成本,只能通過事后救濟,“用人單位的認定裁量沒有同步的平行抑制,勞動者的權益保護只能通過仲裁或訴訟完成”。
(三)解雇保護程序不完善
與境外有關“不能勝任”解雇的勞工法律規定相比,我國的法律規范較為嚴苛,但具體細節規定很少明確,主要表現在缺乏完善的解雇的民主程序和救濟程序。為了避免企業濫用解雇權,法律規定了解雇“不勝任工作”員工的前置性條件——變更工作崗位或者培訓,但是,何種情況下選用何種提高勞動能力的方式更為合適、如何變更崗位才能得當、如何培訓才能合理、變更工作崗位以及培訓的時間范圍如何,法律尚未明晰,而伴隨著調崗調薪著是更為棘手的問題。
二、“不能勝任工作”解雇規則的反思與完善
(一)細化“不能勝任”認定標準
司法裁判作為保護弱者和司法公平的最后屏障,應該承擔解釋法律規定的責任,可以通過司法解釋明確認定“不能勝任”的裁判要旨、發布指導性案例或者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等方式,確定不同領域不同工種關于勝任崗位的裁判性指導標準,使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對不能勝任工作有統一的認定標準,真正實現息訟止爭。在認定“不能勝任”時,仲裁機構和法院應遵循《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則,根據勞動者本人所從事的工作內容、工作要求,汲取主觀兼客觀不能說的理論精華,考慮勞動者的主觀因素作出合理的說明,既保障勞動者的利益,又保護企業解雇權的行使。
(二)確認勞動合同和規章制度認定效力
用人單位千差萬別,對于“不能勝任工作”的認定,目前法律無法適用統一標準界定每一種基本情形,只能規定用人單位解雇權獲得的基本情形。因此允許用人單位合理構建績效考核制度,根據勞動者的具體職業、工種,結合工作的內容,利用勞動合同、集體合同和企業內部規章制度等對勞動者的工作職責進行具體說明或解釋,以便雙方發生糾紛時作為佐證,幫助后期對不勝任工作的科學認定。用人單位能在規章制度中細致描述、詳細列舉不勝任崗位的表現情況,如果合理合法也應該得到司法認可。比如:連續六個月或者一年內有十次不能在規定的期限內完成最低工作任務,不能達到崗位要求的;一年內被客戶投訴超過三次,并在工作中確有過錯的;多次違反企業的第幾項到第幾項規章制度等等。也可以借鑒優化性裁員中的做法,比如“標準線淘汰制度”,即企業設定一個員工不能勝任崗位的標準,如果員工達不到這種標準,就能認定員工不能勝任崗位,從而可以對不符合標準線員工啟動調崗降薪程序。這樣不僅能夠體現用人單位的經營管理權,優化人力資源結構,滿足用人單位的經濟效益訴求,也可以最大限度的尊重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三)擴大認定主體范圍
在“不能勝任”的認定主體上,筆者認為可以發揮工會和職工在認定勞動者“不能勝任工作”中的作用。工會是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溝通和利益平衡的重要紐帶和橋梁,世界上勞工法建立和實施比較齊備的國家,比如瑞典、德國都非常重視工會,德國勞工法賦予雇員代表組織認定不勝任工作的權利,用人單位只有在企業委員會對“不勝任工作”員工提起訴訟得到司法判決后才可以解雇,否則,將被視為不當解雇,實踐證明這有利于緩和勞資矛盾、穩定社會關系。因此,筆者建議明確工會在考核制度的制定上的參與權和建議權,增強認定標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確保事前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在“不能勝任工作”的認定方面,保障其工會對用人單位的用工自主權進行監督,突破認定主體單一局限,也有利于完善解雇程序。相對于工會,企業的員工彼此之間了解更詳細,引入職工自評和互評機制,可以避免企業濫用權利,增強了員工工作能力認定的可信度,為企業認定勞動者“不能勝任工作”提供有力的證據。另外,通過將舉證責任分配給勞資雙方,既保障了員工自我救濟的權利,也有利于對企業一方的證據進行衡量和取舍,平衡了勞資雙方敗訴風險。
參考文獻:
[1]黃越欽.勞動法新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157.
[2]黃程貫.勞動法[M].臺北:臺北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70-79.
[3]郭玲惠.終止勞動契約——兼論德國之制度[J].中興法學,1994,37(5):34.
[4]林更盛.作為解雇事由之“勞工確不能勝任工作”——評最高法院相關見解[J].中原財經法學,2002(4):93-110.
[5]尹建國.行政法中的不確定法律概念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37.
[6]鄭尚元.勞動合同法的制度與理念[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