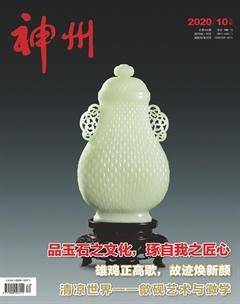人工智能時代下新聞傳播的變革與反思
摘要:人工智能的理念早在1956年達特茅斯學會上便已提出,是指運用機器人代替人類實現認知、識別、分析、決策等功能,其本質是對人的意識和思維過程的模擬。將人工智能運用于新聞研究領域,衍生出了數據新聞、機器人新聞、傳感器新聞等一系列新聞形式,為新聞傳播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而與此同時,以“工具理性”為核心理念的機器思維也為傳統的新聞價值觀帶來了一系列解構。
關鍵詞:人工智能;新聞傳播;變革與反思
一、人工智能對新聞傳播的變革發展
(一)理念創新:以“人”為核心的用戶場景思維的確立
在傳統新聞業時代,信息流動多是從傳播者角度出發的單向灌輸,缺少用戶思維。而在人工智能時代,新聞工作者可依靠傳感器設備,可運用GPS、大數據等技術實現對人體狀態的全面感知,當越來越多的智能物體存在于人的身體上(如智能手機、可穿戴設備以及其他的傳感器等)以及人的生活環境中(如智能家居物品),各種與人相關的物體的數據,便成為人的行為、需求及狀態等的一種外化或映射。物可以提高人的“可量化度”與“可跟蹤性”。[1]從而以用戶所處場景、實時狀態出發,實現數字孿生、精準匹配高觸達率信息。
(二)學科困境:交叉發展帶來理論與實踐困境
無論新聞學與傳播學如何變遷,始終離不開"傳播者""媒介"與"內容"這三個基本要素,而技術革命改變了這三大要素的內涵和外延:傳播主體正在經歷著從專業化到精英化,再到泛眾化加智能化的改變;傳播媒介經歷著從物理介質到關系介質,再到算法介質的改變;內容生產正在經歷著從作為資訊傳播的內容到作為關系表達的內容、再到作為媒介價值的內容價值擴容。[2]新聞傳播業與掌握技術資源的行業不斷交融重疊,在學科交叉發展的背景下,新聞傳播學科的研究不僅會在實踐上更依賴技術,在理論觀念上也有可能引進與人文社科有一定沖突的自然學科價值取向。
(三)產業結構:多元力量的參與延伸媒體觸角
技術的應用研發需要技術驅動型公司的“硬件”支持,海量的數據也需要掌握數據資源的企業提供。人工智能時代下的新聞業不斷與其他企業通力合作,拓展自身新聞邊界、提高社會資源利用率,多元主體共同生產出高質量的“智慧新聞”,如央視與億贊普數據公司合作的《數說命運共同體》,便是打破資源壁壘,跨界互補、協同發展的先例。人工智能時代下的新聞與傳播呈現出一種新型媒介生態,即“共享”新聞資源,“共產”新聞文本,“共繪”媒介圖景的“共同主體”時代。
(四)新聞生產:生產、呈現、反饋等一系列結構變革
在信息生產方面,機器人新聞、傳感器新聞、無人機新聞等都是智能時代下衍生的新型新聞生產方式,在一些程式化強的新聞題材中,如財經新聞、體育報道等,MGC(機器生產內容)具有更高的產出效率與數據挖掘能力;在信息呈現方面,VR/AR/MR虛擬現實技術的運用,通過虛擬場景的再現提高用戶的沉浸感與在場感,獲得更好閱讀體驗;在信息反饋方面,除點贊、評論、轉發等顯性反饋,用戶瀏覽路線、視覺停留時長等多種深層反饋得以接收,有利于傳播行為的調整。
二、人工智能給新聞傳播帶來的隱患
(一)第三方企業介入生產,挑戰新聞業的獨立性
新聞行業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盈利企業,尤其是社會主義的新聞傳播事業,更是具有傳播意識形態、履行社會監督職能的社會公器,只有保持其行業自身的獨立性,才能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人工智能時代,掌握著數據資源和算法優勢的技術公司,逐漸從分發端向新聞生產的核心領域滲透,新聞業有被資本裹挾的危險,如谷歌的新聞實驗室、今日頭條的媒體實驗室等,逐漸從新聞的分發向新聞生產的核心技術領地滲透,將逐漸在新聞生產領域掌握話語權。
(二)工具理性泛濫,新聞公共性的缺失
工具理性由馬克思.韋伯提出,指個人對于目標利益的追求勝過一切方式和手段。在人工智能時代下,一切信息均以“量化”的形式存儲于機器中,新聞價值的標準異化為簡單的點贊量、轉發量,量化的算法動搖了新聞的價值坐標。流量利益驅使下的商業邏輯使更符合大眾社會化過程的“公共利益”被忽視,新聞的社會公器職能缺失。
(三)算法歧視帶來更為隱蔽的權力中心
威廉斯提出“文化唯物主義”,認為不能孤立地對媒介產品做文本分析,而應將其同特定的社會歷史相聯系,同社會制度、文化管理和科技發明的社會意向相關聯。人工智能時代,擁有技術優勢的發達國家可以在世界話語體系中占據更高話語權,通過操縱技術背后的算法程序,提高發展中國家負面信息的算法權重或大力弘揚自身國家的“普世價值”,通過技術操縱帶來更為隱蔽的權力中心。
(四)機進人退,人工智能沖擊新聞工作者
在新聞采集的效度與廣度上、新聞生產的效率上與新聞分發的精準度上,人工智能較人類新聞工作者更勝一籌。新聞生產自動化在為新聞記者“松綁”的同時,也引發了新聞領域從業者關于“智能寫作機器人未來要終結人類記者”的危機感。美國移動新聞服務運營商News public,一家基于個性化定制的、世界上第一家無記者的新聞媒體,與全球超過1650家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智能時代下的新聞工作者應努力探尋自身角色的變與不變,無論未來技術的發展如何,對人的關照仍然會成為我們追尋的方向。
三、結語
海德格爾曾言:“技術是時代的座駕,然而能夠駕馭技術從而影響時代進程的,永遠是具有主體意識的人。”新聞的發展總是與技術的革新緊密聯系在一起,而技術的發展也總在促進著新聞界對于自身理論的守正與創新。突破管理困境、完善認知結構、推進融合進程、夯實人才梯隊對解決這些倫理問題,以及深入推進人工智能產業和新聞傳播產業的創新協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3]在人工智能時代,堅守新聞傳播業的公共性,奉行客觀、中立的新聞專業理念,探尋技術發展與人文價值的平衡是新型新聞工作者的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1]彭蘭.未來傳媒生態:消失的邊界與重構的版圖[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7,39(01):8-14+29.
[2]喻國明.技術革命主導下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學科重構與未來方向[J].新聞與寫作,2020(07):15-21.
[3]李暉,劉茂錦.人工智能在新聞傳播中的倫理失范與對策選擇[J].新媒體與社會,2020(01):67-81.
作者簡介:龐鈞芳(1999.1.5)遼寧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2017級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