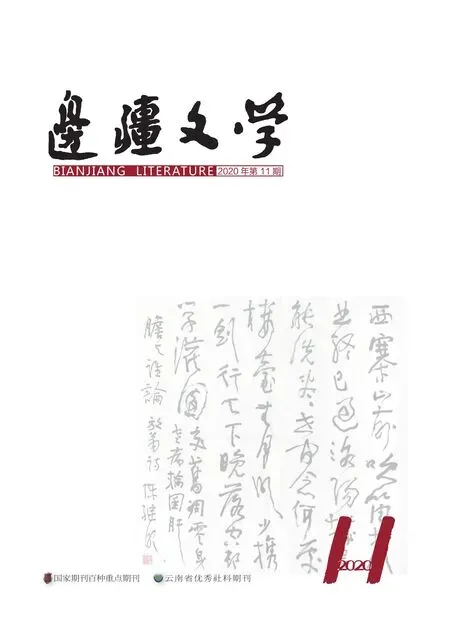世間的水,人間的霧,山中的人
2020-12-01 06:49:00嚴(yán)瓊麗
邊疆文學(xué)
2020年11期
嚴(yán)瓊麗
一
世間的水,有一刻是極暖的;而世間的霧,也有一刻是極清晰的。
竹筏漂在多依河上,漫天的青霧,鎖在羅平與貴州交接的山梁上。
岸邊的老柳樹下,甄子里騰起一層薄薄的水汽,水汽在甄子上方打了一個轉(zhuǎn),就朝著低的地方,攜裹著多依河中奔流的小浪聲,順著河水一道遠(yuǎn)去。甄子旁邊的小爐子上,寸長的,被串在一根長竹簽上,月光色的小肥魚,陳列在幾根鐵絲鉤成的簾子上,一分一秒地趨向金黃。一個架在小爐子的鍋里,像散碎的月光片一樣的,成捧的小魚和小蝦兒嘁嘁喳喳的,失去了水分,變成了一股股在深山老林里,綠水旁奔流的野香味。我站在古樹根下的樓梯上,不上也不下,就死死盯著簾子上的那幾條魚,觀察它們白色的肚子,癟下去,再焦黃。沒帶眼鏡,總是模模糊糊的,站了一兩分鐘,只看了顏色和輪廓,看不清楚魚的形態(tài),干脆挪到攤子側(cè)邊,頭裹深色方巾的布依族阿嬢問我要來一條嗎,我扁桃體發(fā)炎,搖搖頭,也不離去,就那樣癡癡地站著。一道同來的警察叔叔,從我斜對面的歪樹旁走過來,遞給那個布依族阿嬢十元,拿了兩條魚,遞了一條給我,我邊答謝邊接,一點兒也不覺得不好意思。沖著他笑笑,就開始將那條魚最柔軟的肚子送到我的嘴邊,小心翼翼地撕咬下一塊兒肉之后,就往里挪了一步,右手握著魚,躬下身子,“嬢,這個魚,就是旁邊這個河的嗎?”我邊問,邊指著那條穩(wěn)穩(wěn)向下鋪的河。
阿嬢抬起頭,高原紅在她棕黃的皮膚上,已失去了光澤,暗沉的額頭上,縱著幾條不深不淺的皺紋。……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