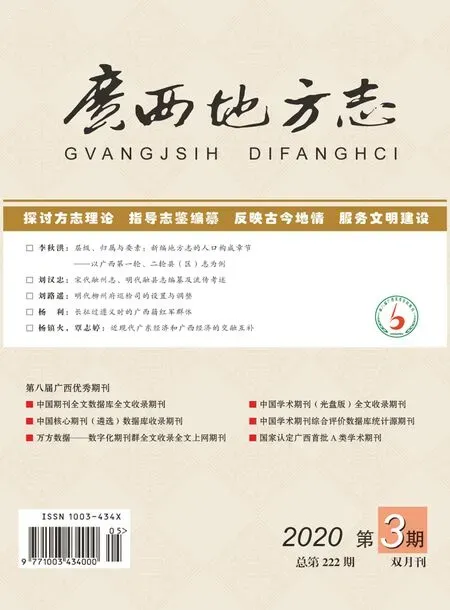層級、歸屬與要素:新編地方志的人口構成章節
——以廣西第一輪、二輪縣(區)志為例
李秋洪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廣西南寧530201)
人口資料是地方志記載的重要地情資料,有重要的資政價值和科研價值。對于社會學、人口學、民族學、歷史學等學科研究而言,地方志中人口資料的價值毋需多言。在海量篇幅的新編地方志中,人口部分,尤其是其中的人口構成所占篇幅一般都不多,但認真深究則可發現其中依然存在若干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些問題直接關系到地方志的質量及其存史、資政和科研價值。本文以已經出版的新編第一輪和第二輪廣西縣(區)志(第一輪共90部,第二輪共107部,至2020年5月已出版76部,至5月底已看到樣書43部)為分析對象,從記述層級、記述歸屬、記述要素和記述篇幅四個方面分析這些已經出版的縣志對人口構成的記述所存在的問題。
一、人口構成章節的層級
廣西第一、二輪縣志對人口構成的記述存在的第一個問題是同一內容卻置于不同層級。
跟志書其他特色內容不一樣的是,人口是每部志書都必記的內容,有人據此認為人口資料不具有地方特色,收集若干數據,加以簡略記述即可。這就大謬不然了。盡管人口是每個行政地域都有的社會要素,但每個地域的人口構成各有特點。各有特點的文化族群人口是地方歷史的承載主體,從而才形成了各地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人文特色。因此,在志書的框架結構中,人口內容特別是人口構成的內容要有適當的位置,應該置于合適的層級。層級過高或過低,都不利于恰如其分地、準確地體現人口內容的重要性和特色。
從志書的篇目框架層面或篇章設置層級看,兩輪共160多部廣西縣級地方志將人口內容分別設置為專志、篇、章、節四個層級。除第一輪馬山縣、三江侗族自治縣、蒙山縣、靈山縣、南丹縣、憑祥市等6部縣(市)志將人口設為專志(人口志,其篇幅相當于篇),第一輪上林縣、南寧市江南區、第二輪柳州市柳北區和北海市鐵山港區等4部縣(區)志將人口設為一節外,絕大多數縣志將人口與計劃生育合設為一篇(或編、章),這是具有時代色彩的設置,體現了第一輪記述時限的后期和第二輪時限內(20世紀80年代至2005年)各地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工作的密切關系。第二輪縣志中,按大篇體布局的縣志多將人口、計劃生育和居民生活合編為一篇(章),按中篇體布局的則多將人口與計劃生育合為一篇(章)。
在這些志書的人口篇章中,人口構成的內容大多分別設為節和目2個層級,從全志篇幅和框架看,這是比較恰當的層級設置。但也有少數縣志設為章,或設為子目層級,個別縣志甚至不設子目。
多數縣區志因為設置了人口章,故順理成章地將其下的人口構成設為節這一層級。但也有部分縣志因為設人口篇或人口志,故將人口構成設為一章,如第一輪隆安、魚峰、柳江、象州、融水、三江、全州、永福、恭城、岑溪、蒼梧、藤縣、蒙山、欽州、浦北、靈山、桂平、貴港、北流、容縣、玉林、凌云、百色、平果、田林、巴馬、都安、南丹、河池、賀州等30部縣(市、區)志都設置了人口構成章。
還有少部分縣志將人口構成設為一個目,例如第二輪的南寧市江南區志、柳州市城中區志和魚峰區志、桂林資源縣志、北海市鐵山港區志等5部縣(區)志。可見,無論是人口部類還是其中的人口構成內容,在縣志框架中的層級設置差異很大,人口構成的設置有章、節、目甚至子目4種層級。據分析,造成志書篇目層級設置上如此大差異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各地人口情況數量、密度和構成等有多大差別,而是編纂者對人口資料的主觀理解和運用差異所導致。
有極少數的縣志將人口內容降至節,人口構成則根本未設置節或目,在全志篇目框架上查無蹤影。例如第一輪柳州市城中區志、柳南區志和魚峰區志都未設置人口構成節或目。第二輪荔浦縣志的人口計劃生育章人口節,也沒有設人口構成目,不僅篇目層級過低,要素也嚴重不齊。這種設置層級過低的情況對完整系統記述人口構成資料,以及對閱讀者查詢和使用有關人口構成資料都造成諸多不便。
二、人口構成章節的歸屬
縣志對人口構成的記述存在的第二個問題是同一內容卻被歸屬于不同篇、章或節,甚至歸屬不同部類。
據對第一、二輪縣志的篇目框架分析,大多數縣志都將人口篇章歸屬于社會部類,篇章設置情況大體有4種:單獨設篇/章;跟居民生活合為一篇;或與民族、宗教等社會部類內容合為一篇;此外有少數縣志將人口歸屬于綜合或資源部類,與自然資源并列為地方資源篇章。
就其屬性而言,人口既是一個地方變遷發展的資源(勞動力、專業人才等),同時人口的各種數量和構成指標也體現了這個地方變遷發展的結果(如分布密度、受教育程度、職業分布等等),故從屬性考慮,將人口篇章歸為社會部類或資源部類均無不可。但若從記述的邏輯性或閱讀的便利性考慮,將人口(包括人口構成)內容置于自然資源篇章之后,作為社會資源的一部分加以記述,更有利于讀者完整理解一個地方的資源概貌。讀者首先了解其自然資源和社會人口資源,為此后逐次了解經濟社會文化各個領域的情況提供了具體的參照系。比如,先了解一地的人口構成中年齡構成和文化構成(受教育程度)數據,隨后在閱讀有關教育、勞動人事和科技等篇章時,就便于讀者評估當地的文化教育事業發展水平和勞動力素質。少數縣志將人口內容歸于社會部類,這種歸類亦屬可行,但是有的縣志將人口篇章內容置于全志篇目框架中過于靠后的位置,這樣讀者在閱讀此前各篇內容時,由于沒有人口資源資料作為參照系,往往感到不容易比對和理解有關內容。
三、人口構成章節的要素
縣志對人口構成記述存在的第三個問題是同一內容記述要素不全且不一致。人口構成包括自然要素和社會要素,故其下還可細分為自然構成(性別、年齡)和社會構成(民族、文化程度/受教育程度、職業/行業、婚姻、家庭規模、姓氏、城鄉、農業/非農等)。一部完整的縣志應該至少記述本地人口的性別、年齡、民族、文化程度/受教育程度、職業/行業、姓氏等基本構成情況,或者說應當包括這些基本要素。
要素不全是兩輪縣志人口篇章中對人口構成的記述較為突出的問題。第一輪柳州市柳南區志的人口構成只記了民族和姓氏兩項要素,魚峰區志則只記民族和文化程度兩項要素,城中區志只在民族節中有民族構成資料,其余人口構成要素一概闕如。荔浦縣志不設人口構成節/目,且對人口構成的記述只有人口分布、民族構成和性別構成三項要素。賓陽縣志只有性別、民族和姓氏三個要素的資料。除了這幾個極端例子外,絕大多數縣志對人口構成的自然要素(性別和年齡)一般都有記載,但往往忽略對人口的社會構成要素(民族、文化程度、職業、城鄉/農/非農、姓氏、家庭戶類型等)的記述或記述不全,這是第一、二輪縣志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民族構成是多民族雜居地區重要的社會資料,也是分析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制定民族經濟和教育發展政策的關鍵依據;文化程度/受教育程度和年齡等資料則是了解人口特別是勞動力素質和發展趨勢的基本數據。人口的這些構成要素內容應是不可或缺的。對記述時限內所經歷的歷次人口普查數據也有部分縣志沒有收錄記載。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輪縣志有1/2即45部將姓氏也列為人口構成要素或在其他章節中加以記述,如賓陽縣志、柳江縣志、臨桂縣志、蒼梧縣志、合浦縣志、欽州市志、桂平縣志、容縣志、那坡縣志、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賀州市志、忻城縣志、來賓縣志、龍州縣志等。河池市10個縣中就有7個縣的縣志記載了姓氏內容。不過有部分縣志(如上林、博白、那坡、天峨、宜州、羅城、東蘭、龍州等)并未將姓氏內容置于人口篇章,而是置于民族、婚姻家庭或方言姓氏篇(章)記述。
相比之下,已看到樣書的43部第二輪縣志中,只有武鳴縣志、邕寧縣志、隆安縣志、桂林市雁山區志、興安縣志、平樂縣志、梧州市郊區志、浦北縣志、陸川縣志、隆林各族自治縣志、南丹縣志、河池市志、崇左縣志等13部記載有姓氏內容,不足1/3,遠低于第一輪的1/2的比例。其余縣志的姓氏資料則均付之闕如。在記載了姓氏資料的第二輪縣志中,除浦北縣志外,均將姓氏數量、構成和分布等內容置于民族民俗篇章而不是人口篇章加以記述。這表明第二輪縣志的大多數編纂者們更看重的是姓氏群體的民俗文化屬性而不是其人口資源屬性。
姓氏是中國傳統宗族觀念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姓氏文化、家譜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國譜牒學,不但有重要的歷史學、經濟學、教育學和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研究價值,在生命科學如生物學、遺傳學中也有重要的研究應用價值。正如文化部辦公廳的一份通知指出的那樣,作為姓氏文化的家譜是一種特殊的歷史文獻,是記載同宗同祖的血緣集團、世系人物和事跡等方面情況的歷史圖譜,它與方志、正史構成了中華民族歷史大廈的三大支柱,是中國珍貴文化遺產的一部分[1]。通過對姓氏人口資料進行大數據統計分析研究,可以通過各種姓氏在不同人群中分布,探討人群的遺傳結構、不同群體間的親緣關系以及人群遷移等。有的遺傳學者根據對宋代、明代和當代姓氏分布的分析比較,認為中國人姓氏在歷史上傳遞是連續的和穩定的。它揭示了姓氏血緣文化的痕跡與生命遺傳物質,尤其是Y染色體(父系遺傳物質)的進化具有基本相同的和平行的表現。常見姓氏的分布是反映各地人群遺傳組成的主要因素,決定著中國歷史上人口遷移和地域人群間親緣關系的程度。中國人姓氏和同姓人群分布規律的研究有可能成為探討中國人起源和Y染色體進化的一條新途徑和科學依據,為探索與遺傳病有關的高發易感人群的分布規律提供有價值的線索。[2]可見,在中國這樣重視家族血緣和家族文脈傳承的社會,地方姓氏資料具有不可取代的獨特的人文價值和科研價值,姓氏資料的遺憾缺失無疑會削弱縣志的人文品位和學術研究價值。這應該是第二輪縣志在人文品位上的不足之一。
四、人口構成章節的篇幅
縣志對人口構成的記述第四個問題是同一內容篇幅相差懸殊。粗略統計,每一部縣志對人口構成的記述篇幅,多則12000余字,少則不足1000字,相差12倍之多。例如,第一輪柳州市城中、柳南和魚峰三部區志的人口構成資料均不足3000字,賓陽縣志分散在三節中的人口構成資料約為1500字。第二輪金秀瑤族自治縣志對人口構成的記述約為6300字,陸川縣志為6200字,鐘山縣志為6000字,恭城、靈川、全州和永福4縣(自治縣)則均在3200-5500字之間,邕寧縣志約為2500字,平樂縣志約為1600字,寧明縣志約為1500字,大新縣志則僅有800字,等等。各部縣志記述篇幅的差距體現的是編纂者對人口資料的搜集功夫、運用程度和理解水平的差異。
對一部100萬字左右的縣志而言,用約5000-8000字左右的篇幅記述當地人口構成及其變化,應該是比較合適的。而且應當以文字記述若干關鍵年份(包括縣志記述的上限年份、下限年份以及重要轉折點如開始改革開放的年份、21世紀第一年等)的人口構成資料,其余年份的資料可列表記述。篇幅過少不足以系統完整記載當地人口各方面構成的資料,過多則有擠占其他內容空間之虞。部分縣志對人口構成的記述篇幅過少,往往只有一兩千字甚至更少,因而所記資料不完整、不系統,于是出現僅以個別年份的資料代替整個記述時限的資料及其變化,或者未記述重要的人口構成要素等現象,使讀者難以了解有關人口構成整體概貌、在記述時限內人口構成的狀況和變化軌跡。
綜上所述,縣志對人口特別是人口構成的記述內容,應當盡力做到層級合適、歸屬得體、要素齊全和篇幅得當,只有按照這4個方面的要求去編纂和修改,才能使縣志對人口構成的記述成為具備存史價值、富有資政和研究意義、體現人文情懷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