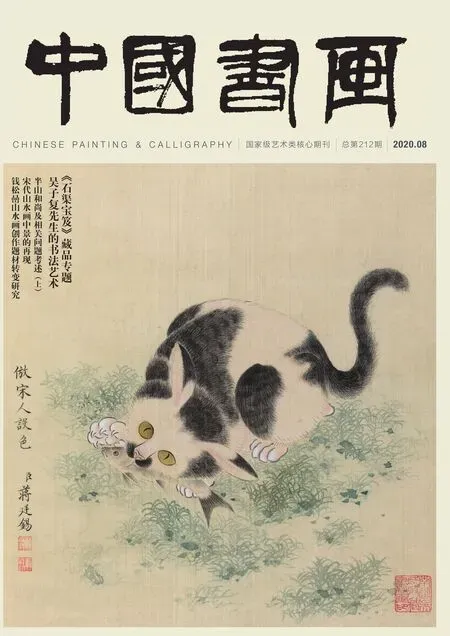古法寫生與內發性演進之路
——以20世紀20—40年代黃賓虹寫生為例
◇ 韓立朝
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中國畫傳統形式已不復有表現畫家情感和社會現實的意義。中西文化的交匯促使更多畫家思考傳統中國畫存在的價值和變革的可能,由此中西融合、傳統再發掘構成了多重景象的交織轉換,一時間樣式豐富,流派紛呈。“五四以后,民族國家的獨立意識普遍高漲,它伴隨著現代化的種種努力,伴隨著許多非主流的邊緣化因素。尤其是中國的民間文化意識上升,以自身的活力消解自身傳統文化的惰性,又以此為基礎重新認識外來的西方文化和西方的傳統主流文化,企圖通過這三方對話的方式,建立t 中國式 的新文化,形成文化t 西化 運動之后的t 中國化 運動。”〔1〕在這種情境下,面對自然或現實的寫生遂成為各派力量比較一致的看法。這正是20世紀山水畫變革與演化的邏輯起點之一。

黃賓虹 山水寫生畫稿 紙本墨筆

黃賓虹 武夷山寫生 紙本墨筆
一、此時期山水畫寫生的語境與方法
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中國畫革新在紛 繁復雜的社會語境下展開,山水畫既處于拯救民族危亡的社會變革之中,又處于西方文化價值觀的沖擊之下,其變革伴隨著對傳統的批判性繼承和對西方藝術的揚棄性吸收而展開,在中國與西方、造化與心源、現實考量和精神表現之間尋求平衡是山水畫家思考的問題。縱覽此時的山水畫,寫生已經成為推進變革的主要方法。此時期學習西方與傳統再發現的兩股力量正由對抗轉入合流,其間有一部分人站在民族本位的立場,從傳統內部尋求中國畫變革的方法和路徑,故而未形成對傳統進行解構的“西化”局面。這一點從當時對中國畫散點透視的認識上便可窺一斑。在改革論者以透視或明暗之有無詰難中國畫之“不合理”時,很快發現其論點并不能經受檢驗,因為有理論家從中國早期論畫文字中發現對定點透視相當的認識,只不過“中國的畫家卻始終不取這種透視法,而是有意識地要自那t 目有所極,故所見不周 的狹隘視野中解放出來,以游移式的視點來畫出一種t 無窮的空間和充塞這空間的生命(道) 。這種論點在1930年代的中國文化界中相當流行”〔2〕。這是傳統中國畫合理合法性的一個旁證,在傳統派畫家看來,西方手法在傳統中國畫里都能找到類似或相近的,不是沒有,只是不用,因為中國畫有本民族適用的方法足以應對變革的需要。即使如此,不得不承認此時山水畫家對西法已有所參照,雖然只是少數畫家用西法寫生,卻影響到了山水畫家的審美取向、方式方法以及形態建構。相對于以往斤斤于必尊古法的老派畫家,此時的畫家們對于中西寫生方法有了一個比較寬松的認知,寫生由此也獲得了更大的伸縮空間,至少改變了傳統中國畫托口寫生而仍一味遵循程式的窘境,逐漸地中國化、內化了西式寫生的某種機械與刻板的做法,并在西法寫生與古法寫生之間尋找到較為恰當的契合點,從而使山水畫寫生具有了改變中國畫陳陳相因局面的作用,這使畫家從寫生中獲得了創新山水畫新的視角和自信。尤其古法寫生的推行,既能改變山水畫日益空疏和僵化的程式,又使之成為保持民族特色、與西方平等對話的某種慰藉,且在當時文化語境中有承繼傳統文脈的本位主義考量。這種策略性因符合托古改制、借古開今的傳統演化模式而容易推行,所以在實際的山水畫寫生中,西法寫生大都經過“中國化”之后被部分地融入中國畫傳統寫生方法和框架之中,其中既有傳統慣性和技術材料的局限性使然,更有畫家思想觀念的深層介入與支配。
無論藝術主張如何,山水畫家都開始對傳統進行反思、追問并求以新變,從面對傳統程式的縱向關系轉變為面對客觀對象的橫向關系,將從文本到文本轉變為從對象到畫面,被畫對象的諸多特征(如地域性、現場性因素)與具體畫法的變革(如筆墨關系的重組)在寫生中被強調出來,隨著情感取向的多元,題材內容的拓展及技術方法的新變,山水畫形態面貌與價值原則隨之而變。
此時山水畫之變可以從客體、主體與本體三個方面加以考辨。相對于人物畫而言,山水畫介入社會現實的能力似乎差強人意。20世紀40年代,徐悲鴻、蔣兆和相繼創作出《愚公移山》《流民圖》,這兩幅鴻篇巨制被認為是中國畫朝向科學寫實主義變革的實踐成果,可謂家喻戶曉。相比之下,山水畫對于變革浪潮則反應遲緩。如果把此時的中國畫變革比作一場地震,人物畫處于震中,那么山水畫則離震中要遠很多,因此受到的波及自然會小。不得不承認山水畫有其自身的規定性,“科學主義”的西式寫生不可能立竿見影于山水畫,換言之,山水畫不像人物畫那樣快速見效。山水畫寫生的主體和客體都有其特定的屬性和慣性,從理論主張到實踐兌現,其間所需要的協調與跟進總需要足夠時間加以落實與充盈。從客體看,人物、花鳥、靜物等題材內容皆目力能及,且能涵蓋全部,山水之“宏大”“遠闊”和“紛繁”遠遠超出靜物、人物等畫科,古人云:“山水之為物,稟造化之秀,陰陽晦暝,晴雨寒暑,朝昏晝夜,隨形改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汪洋洋,如萬頃波,未易摹寫。”〔3〕從本體語言觀之,即使最寫實的山水繪畫如陶冷月的月景山水,也不能在“寫實”意義上與人物畫一較高下,其造型、筆墨、層次、空間、意境等諸多問題繁雜難解,且傳統山水畫語言體系完備精熟,山水畫家舍近求遠不但尚需時日,更為重要的是,融合、化現西方方法技術就像培育新品種一樣頗多難度。從山水畫寫生主體看,傳統派畫家占據了多半,他們不像徐悲鴻等融合派畫家那樣強烈主張引入西法,盡管山水畫家變革山水畫現狀的訴求日益增加,但他們更多地期望從傳統脈絡里尋找方法和路徑。由此觀之,山水畫寫生之客體、本體、主體三個方面都有其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既來自山水畫自身,也同時受了藝術語境的規約作用。
二、古法寫生與內發性演進之路
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很多有識之士希望通過方法與觀念的轉化改變傳統中國畫“逸筆草草,聊寫胸中意氣耳”的自娛與空疏,賦予藝術表達現實事物與情感的品格。寫生,作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之一端被再次強調出來,是不同流派與群體畫家窺見到了寫生所特有的屬性與意義,但具體到寫生方法則見出了分歧。“本來,這是復歸t 師造化 的傳統,不應該受到畫界的抵制,但因為特定的歷史原因,使這一問題復雜化而遇到了不小的阻力。”〔4〕阻力來自哪里?來自傳統派與融合派在創作觀念與變革思路方面的不同認知以及由此形成的寫生方法之爭。在一些畫家心中,師法造化寫生雖然取向相當,但具體操作執行中寫生方法卻存有不同。這一時期,山水畫家面對的主要問題是在以寫生造境為主旨的同時如何保持中國畫固有特質。“五四新文化運動為引進西方寫實主義,在批判摹古傾向的同時,還大力提倡寫生,這一方面促進了引西入中派的西式寫生,另一方面也推動了借古開今派的t 古法寫生 與t 師造化 傳統的回歸。”“基于此,t 五四 之后不但出現了既面向自然又不脫離民族繪畫特點的t 古法寫生 論,也喚起了更多畫家為發揮創造精神對t 師造化 的回歸。”〔5〕“師造化”比寫生有著更為寬泛的意義指向。除了寫生認識上的改變,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是:“許多山水畫家尤其是年輕的畫家,因此獲得了涉獵傳統資源更為開闊的眼界和更趨自由的選擇意識。而故宮博物院的開放,現代印刷業的普及,以及現代傳媒、現代教育、現代藝術社團的興盛,又從諸多層面上支持和豐富了人們的選擇。于是,從20年代開始,沖破四王藩籬乃至明清規格而上溯宋元傳統的多樣化山水畫追求漸成氣候。”〔6〕這一社會文化語境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古法寫生的推行。
提出“古法寫生”論的畫家是胡佩衡。他主張“用古法寫生,由寫生而創作”。在《中國山水畫氣韻的研究》中胡佩衡提出寫生三法:“第一要知道畫理。古人的山水,無不從寫生中得來。所以樹石人物的遠近距離,形式態度,出處都有研究,都有取法。作出畫來,處處都合乎情理。自然會生動,自然會有氣韻。第二要多臨古畫。古人的畫,不管是從天分來的或是從功夫來的,既然可以傳世,必然有幾十年的心得,他的氣味總不會壞的。我們臨摹久了,他們的氣韻自然與我們的筆墨化合。第三要常游名勝。既然曉得畫理,又得了古人的筆墨,就可以實行寫生。寫生不只寫景,大凡四時寒暑,晴雨晦明的真象,必然身歷其境,才能領略得確實,心地越開拓,筆墨必然越瀟灑。”〔7〕在他看來,寫生必須以通曉畫理為前提和基礎,因為畫理也來自前人寫生,由寫生研究整理而來,臨摹的意義在于把握古人畫中氣韻,畫理、臨摹都與氣韻大有關聯,故值得信賴和依靠,那么為何不徑直寫生?胡佩衡雖然沒有談及,但能夠想象出,不先臨摹而徑直寫生則面臨傳統氣韻缺失的危險。在接受層面作出上述判斷可能是一種必然,即使說“我的畫50年后會被認可”的黃賓虹也無意中道出了其中奧義,他的古法寫生實踐更是有力的證明。一方面臨摹是站在前人肩膀上,一方面通過寫生使之創新推進,其遞進關系又必須落實于傳統演化的邏輯鏈條上。此種寫生在此成為統一古法和創新之間矛盾的有效方法。在《中國山水畫寫生的問題》一文中胡佩衡指出:“中國山水畫在唐朝和宋朝為最盛。當時擅山水的名人,都是具有創造的能力,去繪畫天然的好風景,開了后世畫山水的門徑。可惜后世學畫的人,只在他們的皮毛上用功,不知道在根本上去講求,將t 師古人不如師造化 的解說,全都拋開。所以,美術的前途,也就一天退步一天了目下教育部立了一處美術研究會,為的是參酌西洋的美術,改良中國的舊美術,并不是把外洋的尊為神圣把自己的說的一錢不值。所以我們愿意改良中國山水,當注重寫生。”〔8〕
此時期,因為梁啟超歐游歸來反思西方科學,科學主義不再像之前那樣的靈光,人們重新認識自身傳統藝術的價值與意義。“20年代至40年代南北山水畫壇的復古開新潮流,既有從四王風規溯流而上者,又有從四僧逸軌輾轉騰挪而來者,但無論是依照正統派的邏輯追溯發展還是從野逸派的風格中切換而出,憑借上古名跡的散播民間,皆殊途同歸地突破了自南北分宗數百年來的森嚴壁壘,上探更為高古豐厚的繪畫傳統,重新整合山水畫的傳統資源,堪稱是繼元代趙孟頫以還山水畫史上規模最大、程度最深入的以古開新的潮流”〔9〕古法寫生是在對科學不再一味尊崇而又植入了科學精神的語境中提出的,因而影響較大。古法寫生是與西式寫生相對應的一種提法,具有特定的時代性征。古法寫生與中國畫的特有形式連接緊密,可以說方法與形態相互匹配統一,因此在推行上頗多便利。質言之,古法寫生是從傳統內部發生的回歸工夫或者說是造型、寫實的取向,更富于實際操作上的優勢。

三、黃賓虹的古法寫生

黃賓虹 黃山諸峰如削成圖軸 135cm×68cm 紙本設色 1938年 安徽省博物館藏

黃賓虹 山水圖軸 78cm×33cm 紙本設色 1946年 香港緣山堂藏
山水畫古法寫生以黃賓虹為最重要的代表。黃賓虹是20世紀成就最大的山水畫家,畫學修養極為豐厚,精于鑒賞,留下了很多著述,其中有不少關于寫生問題的獨到見解。他說:“作畫當以大自然為師。若胸有丘壑,運筆便自如暢達矣!”“名畫大家,師古人尤貴師造化,純從真山水面目中寫出性靈,不落尋常蹊徑,是為極品。”〔10〕他認為對景寫生易得山水的骨體,師造化才能理解大自然的內在精神。黃賓虹注重臨摹,但他的臨摹方法與眾不同,他更多的是意臨,臨摹提供給畫家一個基本的圖像框架和表達方法,“游黃山,可以想到石濤與梅瞿山的畫,畫黃山,心中不可先存石濤的畫法。王石谷、王原祁心中無刻不存大癡的畫法,故所畫一山一水,便是大癡的畫,并非自己的面貌。但作畫也得有傳統的畫法,否則如狩獵田野,不帶一點武器,徒有氣,力依然獲益不大”。當寫生時,畫家一方面獲得更豐富的細節,于是就逸出既定框架,從而使原有的形態發生變化,同時這種變化受到造化與心源的雙重影響。兩相比較,從古法寫生入者,心源影響略大些,從西式寫生入者,造化的影響更大些,但都不離對心與物的雙向觀照。他又進一步說明:“寫生法,須先明白各家皴法,如見某山類似某家皴法,即以其法寫之。蓋習中國畫與西洋畫不同,西畫之初學者,間用鏡攝影物質入門,中國畫則貴神似,不必拘于形樣,須運用筆墨自然入妙,故必明各家筆墨及皴法,方可寫生。”〔11〕黃賓虹寫生的著力點不是物象,而是筆墨的現實依據。“其所依據的思維基點,也同樣取決于形式自律與象征寓意之間的悖論。然而不容忽視的是,非但筆墨和抽象都已超越單純的形式意義,體現著形式與內容的整合特征,而且筆墨要比抽象富于更明確的內容蘊含,更具體的文化和歷史的規定性。中國文人畫之所以通過對筆墨的闡發以建構自己的專利圖式,就因為筆墨那種觀念化和功能性的潛在素質本身便與傳統文人的處世態度互為因果。”〔12〕如此而言,就決定了黃賓虹的寫生方式,同時也決定了他的作品基本是重復著同一個司空見慣的圖式其上一律留著白凈的天頭,其下是搬前挪后、大同小異的云水樹石。這說明,黃賓虹的寫生內容并未變異,而在形式的反復探索中獲取某種恒久的共性,以通古今之變,而且他是站在中國畫發展的歷史性高度來把握寫生問題。理論家稱其山水作品“傳統文人畫筆墨世界中帶有隱喻性質的人格美,被還原成單純、直接的富于抒情性質的自然美”〔13〕,顯然這不是寫生所能夠獨自完成的,但寫生使畫家從自然中獲得的筆墨內美以及內在的節律似乎與自然形成的同構、同感效應卻足以說明對黃賓虹的啟示作用。傅雷對于好友黃賓虹獨特的“師造化”的方法有一段論述:“t 藝人何寫?寫意境。實物云云,引子而已,寄托而已。古人有言:攝景于煙霞之表,發興于深山之顛。掇景也,發興也,表也,巔也,解此便可省畫,便可悟畫人不以寫實為目的之理即師法造化一語,亦未可以詞害意,誤為寫實,其要旨固非貌其嶂巒開合,狀其迂回曲折已也。學習初期,誠不免以自然為粉本(猶如以古人為師),小至山執紋理,樹態云影,無不就景體驗,所以習狀寫形也;大至山崗起伏,泉石安排,盡量勾取輪廓,所以學經營位置也。然師法造化之真意,尤須更進一步:覽宇宙之寶藏,窮天地之常理,窺自然之和諧,悟萬物之生機;飽游飫看,冥思遐想,窮年累月,胸中自具神奇,造化自為我有。 ”〔14〕傅雷從黃賓虹畫里看到了中國畫傳統深處的精神境界。經過一系列寫生,黃賓虹從古人粉本中脫化而出,以真山水為范本,開始了面貌上的蛻化與變異。寫生面對著真實具體、生動可感的自然形象,地域性、地貌性差異都是畫家建構個人風格的契機與引導。他于此頗有心得:“學習那家作法,固然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發,但那家的那法都有實際的自然作根據的,古代畫家往往寫生他的家鄉山水,因而形成了他自己獨到的風格和技巧。”〔15〕1928年,黃賓虹首次游歷廣西、廣東等地,其后往雁蕩、黃山、浙東、川、粵、桂等地,遍游名山大川,一路寫生,畫了大量鉛筆速寫和墨筆默記,畫稿累積萬余幅。鉛筆稿多為巴掌大小,單筆勾畫,山脈津梁輪廓都有所標注,突出了現場性,筆法靈活多樣,極為鮮活可觀。墨筆寫生稿,可能是游歷中的記錄或默記,其意圖在于通過寫生與造化和古人畫法兩相印證,以參造化之功。“這種堅持山水寫生、積累畫稿作為創作的基礎的做法,在當時不少堅持傳統的中國畫家看來是t 莫不駭余之勤勞,而嗤其迂陋 ,難以獲得認同。”〔16〕此時期他多次表達寫生的意義和方法。可見當時人們對寫生方法的爭論較為普遍。值得注意的是,黃賓虹山水畫的參照資源并不限于傳統中國畫,他對西方印象派的評價和部分借鑒也說明曾受到西方藝術的啟發,這并不否定他在古法寫生上的身體力行與所取得的成就。黃賓虹能夠敏銳地看到寫生的某種局限,并以“心源”作為補充和完善寫生的必經之途,恰恰說明了“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古訓的不二之處以及古法寫生的意義。“寫生只能得山川之骨,欲得山川之氣,還得閉目沉思,非領略其精神不可。余游雁蕩過甌江時,正值深秋,對景寫生,雖得圖甚多,也只是甌江之骨耳。”〔17〕看得出,如想獲取其精神就要脫開寫生狀態,因為在中國畫審美判斷里,接續傳統,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得意忘形、疏離現實才具有超越性。“對中國人而言,至高真理的發掘,必得訴諸過去的文化,傳統以及高潔心性所顯露出的氣質,而無法求之于眼前的現實即景。”〔18〕因此,高明的畫家雖然都強調臨摹和寫生,但他們更善于捕捉方法背后的氣質、格調、精神等形而上特征。元代以后,對畫面品性的過分追求已經消弱了對山水實體的關注,由此的結果則是“在這個階段里,他們山水畫中的實體感趨于薄弱自然并未被否定,而是被變形了”〔19〕。自然被變形究竟意味著什么?這恰是20世紀初“美術革命”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西式寫生方法的介入則具有此方面的針對性,20世紀山水畫經過寫生后還原的山水實體的一面,由虛靈轉入沉實,即是山水畫努力的方向。黃賓虹尋求筆墨“鏤空”效果,既有在多重層次架構中的空靈之美,又有豐富筆墨構建的渾厚華滋,比起前代山水畫,還是充盈、厚重、雄健多了,這些風格化特征正是寫生效果最有力的證據。在寫生中黃賓虹發現良多,比如“皴法變法極多,打點亦可作皴,古人未有 此說,余于寫生時悟得之”〔20〕,并進一步說明這種“沿皴作點法”得之于20世紀30年代在蜀川山水寫生時悟得。黃賓虹《蜀游雜詠》詩中有句:“潑墨山前遠近峰,米家難點萬千重,青城坐雨乾坤大,入蜀方知畫意濃。”“沿途作點三千點,點到山頭氣韻來,七十客中知此事,嘉江東下不虛回。”〔21〕“入蜀方知畫意濃”與“嘉江東下不虛回”都道出當時黃賓虹入川寫生收獲豐厚的事實。黃賓虹在寫生過程中不離對傳統與造化、古人與今人的融會貫通。
盡管黃賓虹有場景性的山水寫生,但其寫生目的不在具體山形與地域的顯現,而著眼于從造化中獲得新奇的、深刻的畫理依據,以此尋求筆墨內美的超越性表達,強調對山水精神的把握。他的筆墨雖不離樹、石、煙、水等物象,但更著意于筆墨的層次、結構等抽象關系,由此便解構了現實性、物理性的秩序,使觀者更多地關注其筆墨自身和藝術世界的美感。從此處看,黃賓虹上承董其昌以降筆墨自律的圭臬,下啟后世雄健俊朗、繁茂渾厚的藝術風尚。
結語
寫生方法并不限定在某一種,寫生的寬泛與彈性一定程度上彌合了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不同見解的畫家群體。雖然他們對寫生的理解以及各自的寫生方式不盡相同或相去甚遠,但大部分畫家堅持著民族藝術的本位立場,無論是西法寫生,還是古法寫生,寫生的意義更多地顯現于寫生的共性,即寫生夾雜著過去經驗模式與現場感覺的抵牾與融匯,在傳統與西方、心源與造化之間得到一種印證并由此超越套路并捕捉豐富、新鮮的感受,進而建構出新的山水畫形態與風格。另外,寫生不是一個使人趨同的方法,寫生正是糅合了太多的寫生之外的因素,我們不能給寫生附帶更多的思想內容,而應該還原它本有的承載。
注釋:
〔1〕 鄭工《演進與運動中國美術的現代化(1875 1976)》,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02 年版,第90 頁。
〔2〕 石守謙《對中國美術史研究中再現論述模式的省思》,《朵云》第67 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 年版,第197 頁。
〔3〕 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年版,第690 頁。
〔4〕 邵大箴《寫生與20 世紀山水畫以李可染為例》,《二十世紀山水畫研究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年版,第428 頁。
〔5〕 薛永年《百年山水畫之變論綱》,《二十世紀山水畫研究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 年版,第7 頁。
〔6〕 盧輔圣、湯哲明《二十世紀山水畫研究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 年版,第2 頁。
〔7〕 胡佩衡《中國山水畫氣韻的研究》,郎紹君、水天中《二十世紀中國美術文選(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 年版,第107 108 頁。
〔8〕 胡佩衡《中國山水畫寫生的問題》,《繪學雜志(3)》,北京大學發行,1921 年11 月。
〔9〕 郎紹君《二十世紀山水畫的“承”與“變”》,《二十世紀山水畫研究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 年版,第4 5 頁。
〔10〕 王伯敏《黃賓虹畫語錄》,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1年版,第10 頁。
〔11〕 郎紹君《現代中國畫論集》,廣西美術出版社1999 年版,第183 頁。
〔12〕 〔13〕 盧輔圣《黃賓虹抉微畫集·序》,浙江省博物館編纂《黃賓虹抉微畫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年版。
〔14〕 〔15〕 湯哲明《多元化的啟導》,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 年版,第284 285 頁。
〔16〕 陳瑞林《中國現代美術史教程》,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9 年版,第218 頁。
〔17〕 前揭《黃賓虹畫語錄》,第48 頁。
〔18〕 〔19〕 高居翰《氣勢撼人十七世紀中國繪畫中的自然與風格》,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 年版,第93 頁。
〔20〕 朱金樓《兼金并涵,探賾鉤奧黃賓虹先生的人品、學養及其山水畫的師承淵源和風格特色》,見王魯湘《中國名畫家全集黃賓虹》,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8 頁。
〔21〕 《黃賓虹畫集·畫論輯要》,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