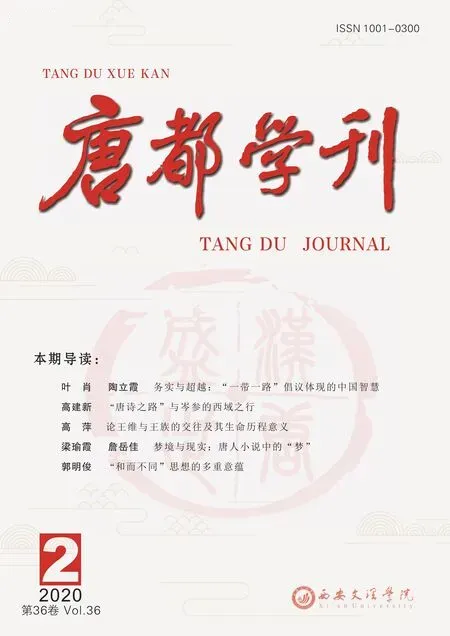論卡特時期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首次推延中的美國因素
薛鵬程
(復旦大學 歷史學系,上海 200433)
1976年11月,卡特總統上臺后在正常化決策時便面臨著延續前兩任政府對華政策及壓制“建交大辯論”中反對中美建交社會輿論的雙重壓力,而在那時國會爭奪外交領導權與新任總統構筑的“集體-競爭型”外交決策機制的共同作用下,美國政府就當前中美關系展開了初步評估。評估結果顯示,近期推進中美關系正常化給美國帶來的戰略與經濟利益微乎其微,而執行“蘇中等距離”政策卻便于美國在“美中蘇大三角”關系中獲取最大收益。這一系列考慮加上卡特總統的個人執政偏好等因素,最終促使美國在卡特執政初期做出了延緩正常化的決策,并造成了美國國務卿萬斯訪華前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的首次推延。當前,國內外學界對正常化首次推延的原因、經過及其影響因素等已有一定著墨(1)當前國內外學界研究萬斯訪華前美國對華關系正常化進程遲緩的主要成果有:陶文釗《中美關系史(1972-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4頁;羅伯特·S·羅斯《風云變幻的美中關系(1969-1989):在談判中合作》,叢鳳輝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138頁;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408頁;郝雨凡《白宮決策——從杜魯門到克林頓的對華政策內幕》,東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329頁;夏爾-菲利普·大衛《白宮的秘密:從杜魯門到克林頓的美國外交決策》,李旦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284頁。Harry Harding,A Fragile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2.pp.67-75;JamesH.Mann,About Face,A History of American’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from Nixon to Clinton,NewYork:Vintage Books,2000.pp.96-115等,這些成果基本涉及了卡特執政初期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遲緩的部分原因,但由于缺乏相關解密檔案的支撐,上述成果并未系統論述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首次推延中的美國因素。。但由于受解密檔案年限的限制,他們多依據雙方談判當事人的回憶錄或口頭文獻來進行宏觀層面上的探討,對美國制定推延正常化政策的原因、動機及相關政府決策的細節脈絡難免闡述得不夠充分。本文將依據美方解密檔案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對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首次推延中的美國因素進行較全面的梳理,以求助于方家。
一、政治遺產與“建交大辯論”塑造的決策背景因素
執政初期,美國總統卡特便決定沿襲前兩屆政府的對華承諾以保持對華政策的延續性。這與美國政界、學術界掀起的“建交大辯論”共同塑造了卡特推行延緩正常化政策的決策背景因素。
(一)尼克松、福特政府的政治遺產
首先,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對華正常化決策、承諾等政治遺產成為影響卡特政府制定“推延”而不是“放棄”正常化政策的重要政治因素。20世紀70年代初的基辛格和尼克松訪華作為中美關系的“破冰”與“融冰”之旅,開啟了兩國關系正常化的進程。而雙方發布的《上海聯合公報》則成為中美兩國在處理正常化問題時必須遵守的法律文件。為此,1977年3月8日,布熱津斯基提醒卡特,本屆政府需要遵守尼克松政府對華反復提及的“五點承諾”和兩點額外承諾。它們是:“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再支持臺灣獨立的任何行動;用美國的影響反對日本進入臺灣;美國尋求正常化,并盡可能在1976年實現正常化;在沒有事先協商的情況下不會參與任何有損中國利益的行動;在正常化進程中將逐步減少在臺灣的軍事安排”[1]49。除此之外,布熱津斯基還提醒卡特,尼克松的承諾既顯示了美國在處理正常化問題上的靈活性,也反映了中美兩國在應對蘇聯威脅戰略利益上的趨同性。在正常化前,這些承諾應嚴格保密,以防國內游說集團針對正常化發起的“政治風暴”。如果沒有這些承諾,中美關系不可能發展到現在的狀態,“反對它們將破壞《上海聯合公報》的精神”[1]50。卡特對此表示肯定,并愿意在遵循上述承諾的基礎上推進中美關系。
而“水門事件”余波下沒有經過民主選舉的福特總統為謀求連任,更不敢在對華關系正常化方面有所突破。盡管如此,福特還是讓基辛格留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兼國務卿,以延續尼克松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毛澤東主席去世后,福特在悼念電文中向中國新任主席華國鋒表示:“本人重申美國對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決心”[2]957。但由于受到國會游說集團和國內選舉的干擾,這一日期不得不推遲到1977年3月1日[2]979。而后的福特訪華沒有發表聯合公報,也沒有任何能顯示加強中美關系的成果,使得中國對美方的訪華動機產生嚴重懷疑。而美方為其減小政治風險,通過縮短福特訪華時間和調整訪問計劃來降低此次訪華意義的做法更使得中方大為惱火。為了平息中國的不滿情緒,“福特做出了他所能夠做出的最大奉獻——即他個人承諾下一任期爭取實現美中關系的正常化”[3]296。雖然撤軍計劃和對華承諾最終因福特沒有當選總統而不了了之,但其在任期末展開的涉及中國政局、反蘇共同利益和雙邊關系及對華貿易政策等問題的對華情報分析,也為后來卡特評估對華政策起了一定的參考作用。很難想象,如果卡特不考慮政策連續性和延續前兩任政府的對華承諾,正常化極有可能因當時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而夭折。
(二)“建交大辯論”影響社會輿論
1974—1977年在美國政界、學術界和社會領域展開了是否應同中國建交的大辯論。首先,在戰略利益方面,鮑大可、費正清、哈里·哈丁和艾倫·懷廷等堅決支持對華關系正常化。他們認為,中美建交可以極大地加強中美戰略關系,可以維持東亞的實力均衡,又可防止蘇聯的擴張和滲透,對美國在東亞的利益十分有利。此外,中美建交還可以使中國在諸如朝鮮半島、國際裁軍等一些敏感問題上與美國合作。反對派則認為,目前與中國建交弊大于利。因為美國同中國當前的合作,明顯是戰術上的權宜之計。且美國與中國建交中能得到的好處具有不確定性,但弊端則是美國將失去蔣氏政權這么一個長期而忠實的“盟友”,并失去對地處戰略要沖臺灣的使用權。除此之外,美國的撤出會在該地區的盟友中間產生極為不良的影響,會使日本等國家對美國承諾的可信性產生嚴重懷疑。與此同時,福特時期的國防部長施萊辛格和國務卿基辛格也針對是否要與中國建交并建立軍事關系展開辯論。施萊辛格認為,與蘇聯打交道是一個軍事問題,“緩和”并沒有限制住蘇聯的擴張,反而幫助蘇聯加快了戰略武器和常規武器的發展,因此應加快發展與中國的戰略關系。而基辛格則認為,“緩和”本質上是一個外交問題,不主張立刻同中國建立軍事關系,而應通過調整中美蘇關系和全球政治來約束蘇聯[4]259。
此外,美國國內在廣泛討論是否與中國建交的同時,也開始討論應以何種方式建交。其分歧的實質是能否找到一種模式,既對美國利益有利,同時又能被中國政府所接受。一種極端模式是“德國模式”,即美國可以在海峽兩岸同時保持“大使館”,如東、西德政府在1990年以前那樣。另一種極端是“日本模式”,即美國接受中國的“斷交”“廢約”“撤軍”建交三原則,通過非官方的方式與臺灣保持經濟和文化上的民間往來。此外,有的學者還提出了“維持現狀”和“美國單方面發表聲明”等正常化方案。但不管是哪種解決方案,絕大多數中國問題專家都認為兩國應該盡快談判達成某種妥協,以便于在兩個極端中找到一個折衷點。應當說,壓制“建交大辯論”中反對中美建交的社會輿論成為卡特總統上臺后考慮對華政策和正常化方案時不得不考慮的另一重要因素。
二、國會爭權與決策機制交融下的國內政治因素
應當說,始于越南戰爭并在“水門事件”后變本加厲的美國國會爭奪外交政策領導權的情勢與新總統構筑的“集體-競爭型”決策機制共同構成了卡特推行延緩政策的兩大國內政治因素。
(一)國會與政府爭奪外交政策制定權
20世紀70年代,美國國會的歷史性爭權極大地影響了正常化發生的時間、內容和形式,成為卡特總統在做出正常化決策時必須考慮的一大制約因素。眾所周知,美國實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制度。但美國憲法在立法和行政兩大部門的權限留下了一大片“灰色地帶”,即沒有明確限定兩個機構的權力,這為兩個機構后來在外交權方面的爭執埋下了隱患。應當指出的是,權力分立只是憲法起草者的理想,許多政策領域畢竟還需要兩個部門的通力合作。于是美國政府中出現了國會和總統分享權力的情況,在外交領域尤為如此。20世紀30年代之前,除林肯和老羅斯福等強勢總統當政外,國會一直處于聯邦政治的中心。而從“新政”后大致到約翰遜時期的20世紀60年代末期,總統及其領導的行政部門基本取代國會成為美國政治的中心。因此,20世紀70年代前國會通常對行政當權的外交政策制定權起一種默認、合作的態度,并很少在外交領域與總統發生爭執。漸漸地,國會便扮演了一個僅將總統外交決策合法化并使其得以實施的角色(2)無論是艾森豪威爾時期的“福摩薩決議案”和“中東決議案”,還是肯尼迪屆內的“古巴決議案”和“柏林決議案”,國會都給予了總統自由決定如何處理外部沖突的權力。這一方面是由于國會缺乏足夠的外交信息和專業素養,另一方面則應該從地方議員缺乏全球性的視野來尋找原因。經歷了眾多案例,兩大部門的關系便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被固定下來,形成了一種“在全球遏制共產主義擴張斗爭中總統確定對策,然后尋求國會支持”的默契。參見郝雨凡《白宮決策——從杜魯門到克林頓的對華政策內幕》,東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507-509頁。。
但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國會對政府過多的海外卷入(越南戰爭)強烈不滿,再加上“水門事件”所產生的對行政當局制定外交政策的不信任感,導致國會對行政當局處理外交事務能力失去信心并決心在外交政策制定方面奪回自己應有的權力。部分議員認為,為保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國會不僅應該,且必須積極參與外交政策的制定。而用更為嚴厲的立法限制行政當局在外交領域的行動,被認為是國會分擔外交制定權力的最好方式。據相關資料顯示,在整個70年代,國會大概通過了150個立法限制和規定來約束總統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制定和貫徹執行,這使得福特總統在離任時發出了“強加和限制總統在處理法律和對外事務的束縛是不能容忍的枷鎖”的強烈感慨[5]。于是,自卡特上任伊始,便有國會領袖向其表達了要參與外交事務的意愿,并要求其在制定外交政策時尊重、征求國會的意見。考慮到行政當局在外交事務中的絕對權威和國會默認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卡特不得不同意國會的要求,答應在主要外交政策變化和做出重大外交決策時提前與國會磋商,以保證兩個部門的政策協調(3)正如萬斯在訪華時指出的那樣:“這屆美國政府與國會出現了新的制衡關系,有可能成為影響正常化的一大因素。”本屆政府的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平衡,制定外交政策的方法比過去更加公開和坦率。卡特政府上臺后最早的一件事便是與國會建立了一種新的關系,即政府在做出重大決策之前應該與國會有更密切的協商,力求與國會在形式與外交政策的執行方面成為伙伴。參見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77-1980,Volume XIII,China,2013,pp.142-143.。這也成為卡特在推進正常化的進程中必須經常考慮國會制衡因素、在正常化問題上畏首畏尾的重要原因。推進正常化進程和撤銷美國對中華民國的外交承認,恰好發生在行政當局外交政策權限受立法機關攻擊和批評、國會權力急劇上升并強力爭奪外交領導權之時,并成為卡特總統在做出對華正常化決策時必須考慮的另一國內政治因素。
(二)美國外交決策機制出現的新變化
卡特時期,美國外交決策機制出現的新變化也構成影響正常化進程的另一制約因素。自正常化進程開啟以來,尼克松政府在外交決策方面的集權作風和抵制行政部門的傾向所向披靡。其外交決策的特點可以歸結為“沒有真正的爭論”和“行政機構參與的假象”——其他部門在外交領域方面的參與在總統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面前“最終只能起一個象征作用”[6]215。在與自我標榜為“我即外交”的基辛格的配合下,其實現正常化的外交目標和與中國達成政策共識的決心尤為堅決。福特接任總統后,受“水門事件”的影響其外交勢頭趨漸溫和、善于妥協,并且“喜歡意見統一,害怕出現對立”[6]231。基辛格的留任也使本屆政府大體延續了尼克松時期的決策機制,推進對華關系正常化的政策得以在穩定中存續。但1977年卡特政府上臺后,美國對華外交決策機制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卡特傾向于認為明智的決策不應該被一個封閉的、形式化的機構所囿,決定摒棄前任過多的“馬基雅維里式”的外交風格,采取一種“多方辯護”式的“集體-競爭型”決策模式。卡特渴望政府內部富有集體主義色彩,“希望我的七八個合作者能夠直接向我提出建議,我一直認為一小組決策中聚在一起,平等地討論問題是最有效的方式”[6]259。
很明顯,卡特總統正是想以這種方式從顧問那里集思廣益,避免因任何機構和程序的意見流失影響他對某一個問題的理解和估計,從而做出錯誤的決策。但這種被詹姆斯·法洛斯無情地批判為“能同時相信所有原則的唯一規律性事物”導致了卡特政府在對華決策過程中陷入了“多方辯護”的陷阱,并造成了其外交決策認識和目標上的混亂。除此之外,卡特在其決策機制的范圍內沒能避免布熱津斯基和萬斯在對華關系正常化決策過程中的肆意競爭。卡特總統本來的意圖是想在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間制造一個合理的“平衡”,即通過一套正式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程序和一個以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和以國務卿為基礎的非正式顧問程序來管理美國的對華政策。簡單來說,就是“以萬斯為外交家,以布熱津斯基為智囊,以自己為最終的決策者”。但企圖既當“偵探”又當“法官”的卡特自始至終也沒有明確過這兩位顧問各自的職責,結果只能是導致官僚之間日益激烈的爭斗。畢竟雙方都想盡力爭奪外交政策的領導權和控制權,并使自己的組織成為引導和管理決策程序的中心[7]。這種含糊不清并帶有內部斗爭痕跡的管理風格極大地影響了卡特班子內部合作,也影響了美國對華關系正常化工作目標的協調。最終,二者分別主導的國務院與國家安全委員會間的分歧間接成為正常化首次推延的第二個重要的國內政治因素。
三、對蘇政策與個人執政偏好構筑的戰略決策因素
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評估促使卡特得出了正常化在戰略與經濟上帶來的利益微乎其微的結論,無形中為其制定延緩政策提供了理由。而基于對蘇緩和戰略制定的“蘇中等距離政策”則與卡特總統的個人執政偏好一道,成為影響正常化進程的另外兩個戰略決策因素。
(一)“蘇中等距離”政策成為正常化的政治阻礙
卡特上臺不久,萬斯便向其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主要結論為:美國必須繼續保持美蘇關系間脆弱的平衡,并讓中國明白中美關系并非“一元化”——即中美緩和不是為了針對蘇聯,美國會繼續維持對蘇關系。美國擔心蘇聯與日本的可能反應使得建立美中安全關系變得十分危險,尤其是在未與中國實現關系正常化的情況下[1]80。“因為對蘇聯來說,沒有比發展美中安全關系更充滿敵意的了。”[4]333因此,萬斯向卡特建議道:“就正常化本身而言,不應該賦予正常化太大的壓力……也不應該把美國置于人為的最后期限之下。”[1]80萬斯的報告無疑影響了卡特的對華決策,使得暫緩與中國實現關系正常化在卡特的通盤考慮下占據上風。雖然布熱津斯基極力主張加速與中國建交,以共同對付蘇聯的擴張勢頭,但在這個時期,卡特偏向于支持國務院的評估,而5月24日布熱津斯基通過評估前兩屆政府會議記錄得出的“美中關系目前的狀況相當不穩定”的結論更是在無形中強化了卡特支持萬斯暫緩實現對華關系正常化的觀點[1]85。
應該指出的是,萬斯的“對蘇緩和第一”和對華、對蘇關系“二元平衡”的觀點對卡特的對華決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使卡特從原先利用中國向蘇聯施壓的想法中退卻,其政策向延緩正常化和改善美蘇關系傾斜,并使卡特在初步評估中國后謀求對蘇對華“等距離”政策的想法更加堅定。畢竟,為避免二者中任何一個利用美國來對付對方,美國應該謹慎地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尋求平衡[8]。這樣的政策在1977年5月迅速鋪開并予以執行。面對蘇聯,美國打算推行緩和政策以緩解緊張的國際形勢。在一次演講中,卡特強調美國的政策不能繼續建立在遏制蘇聯擴張的基礎上,而應考慮制定新政策以面對一個新世界的挑戰。這一政策應該基于美國歷史觀中的道德價值和樂觀主義,而這要求美蘇關系的緩和。“我相信緩和……它意味著通向和平的進步”[9],畢竟“(美國)已經擺脫了對共產主義的過分擔心,同蘇聯發生沖突的威脅已經不那么尖銳,美國與蘇聯要擴大合作面而縮小競爭面”[10]。而面對中國,“等距離政策”則反映在軍事技術的購買上。蘇聯對美國向中國轉移一些有關的軍事設備和技術反應激烈。于是,為了避免對華軍售激怒蘇聯,進而危害到美國利益,卡特從福特政府向中國轉讓高技術和武器的政策上退卻,拒絕了先前布朗向中國轉移與軍事有關的技術的提議,并向蘇聯保證不會同中國建立軍事關系。同時,卡特逐漸降低了批評蘇聯人權政策的格調,并開始從第二輪裁減戰略武器會談的強硬立場中后退,與蘇聯就限制戰略武器達成初步協議。卡特還決定采取一些單方面措施,如停止生產B1轟炸機、“民兵-Ⅲ”和MX導彈以取悅蘇聯[4]335。就這樣,“蘇中等距離”政策被執行下來,成為阻礙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的一大政治因素。
(二)輕視中國的執政偏好影響正常化進程
卡特本人的政治、戰略考慮和對華政策選擇所構成的執政偏好,也成為正常化進程的一大影響因素。作為當選前從未有過任何外交經驗的總統,卡特在執政初期的種種做法顯示出其“對中國戰略地位的輕視和對加快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的冷淡”[11]135。1977年1月,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們第一次開會并按照重要性列出美國亟待解決的16個問題中居然沒有提到中美關系(4)在第一次總統會議備忘錄上,大多數學者提到上面記錄了15個下一步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新近解密檔案顯示,其實上面總共列出了16個問題。參見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Brown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rzezinski)February 9, 1977, FRUS,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2013, p.26;楊賢《特殊機構:美國駐華聯絡處揭密》,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頁;陶文釗《中美關系史(1972-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頁。。為此,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中國問題專家奧克森伯格向布熱津斯基提出了主動靠近中國的建議[1]14,其認為卡特總統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做什么來表達對中美關系的個人興趣,而且在這個問題上卡特通過“不作為”來制定外交政策,導致美蘇關系受到關注并向前發展,中美關系正失去活力[1]15。因此,美方有必要發展一個長遠的策略來建立同中國的外交關系以避免中美關系出現“消極信號”,并表明總統打算優先解決與中國的關系問題。但卡特此時醉心于推行對蘇對華一碗水端平,以便從雙方撈取好處的政策。因為在卡特看來,“如果不考慮中蘇關系,僅就經濟和軍事因素而言,中國并非一支重要的戰略力量,沒有必要急于去實現正常化”[11]135。最后,1977年初中國戰略環境的急劇惡化也助長了卡特做出延緩正常化的決策。當時的中蘇關系在毛澤東去世和蘇聯對中國新領導的意圖進行短暫的試探過后持續惡化。蘇越接近、越南加入經互會以及隨之而來的中越關系惡化,使得卡特自以為樂觀地意識到“在正常化問題上可以慢慢來,因為中國已經不可能興風作浪了”[3]301。
盡管輕視中國的戰略地位,但為了使對華政策從屬于對蘇政策并在兩者之間創造一種聯動的“齒輪效應”[1]325,卡特還是多次傳遞本屆政府重視中美關系,表示愿意履行前兩屆政府對中國的承諾[1]51。即便后來卡特已經做出暫緩與中國實現正常化的決策,但他還是發表演講稱“美中關系是美國全球政策中的一個中心要素……我們也希望能找到一種方式來彌合把我們分開的那種分歧”[9]961。為了表明其對美中關系保持關注,卡特還宣布萬斯將于1977年8月訪問北京。應該指出的是,卡特行政當局雖多次宣揚穩固中美關系的重要性,但此時的對華政策實際上遠不及對蘇政策重要,其目的只是為了在對中對蘇政策中營造一種“一碗水端平”的錯覺,便于其在美中蘇大三角關系中獲取最大利益。最終,正常化進程在卡特輕視中國戰略偏好的影響下被“蘇中等距離”政策所左右,并造成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首次推延。
綜上所述,卡特總統自上臺伊始,在正常化問題上就深受美國政治、社會輿論與戰略決策等因素的影響。首先,正常化自《上海聯合公報》出臺到卡特總統上臺,已經走過了近5個年頭,在尼克松與福特任期內雙方達成的一系列協議、共識等政治遺產及“建交大辯論”影響下的社會輿論是卡特總統在考慮正常化不可忽略的兩大決策背景因素。其次,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改變了以往國會作為總統制定外交政策“合法性工具”的慣例,議員們紛紛決定加大國會在外交事務上的卷入程度,以奪回憲法賦予國會的對外政策制定權。于是,“國會爭奪外交領導權”的歷史情勢便給卡特政府推進正常化進程帶來了一種無形的決策壓力。再次,此時的美國外交決策過程較前任發生了較大改變,卡特一心倡導的集體式的競爭型決策機制在政府內部官僚政治斗爭的影響下反而造成了許多無謂的內部損耗,并成為美國推進正常化進程的重要阻力。為此,執政初期卡特政府被上述影響正常化的美國因素束縛住了手腳,不敢在正常化方面尋求重大突破。在萬斯“對蘇緩和第一”和對華對蘇“二元平衡”觀點的影響下,對中國暫無迫切需求的卡特遵從個人執政偏好并決定暫緩正常化,以便借中蘇分裂的機會在美中蘇三角關系中分別從雙方撈取好處。最終,“蘇中等距離”政策被貫徹下來,并造成了卡特執政初期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首次推延。據此,筆者得出以下結論:雖然正常化進程的遲緩與蘇聯因素[12]、“文革”余波下中國政局的動蕩、社會矛盾尖銳和經濟發展滯后的整體狀況有所關聯,但由卡特執政初期的國內政治因素、社會輿論因素與戰略決策因素所共同交織并起決定性作用的美國因素才最應該為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首次推延負主要責任。好在應對蘇聯威脅及構建中美“反霸共同體”的戰略考慮此時恰好成為中美兩國維護國家安全的共同選擇。最終,在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故的情況下,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逐漸迎來了互相試探對方建交“底線”的萬斯訪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