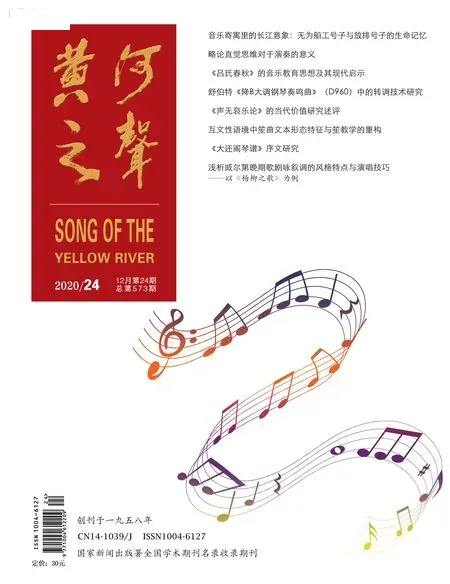“左權民歌”中無伴奏合唱“語言”的運用
陳 希
新時代針對“左權民歌”進行研究具有如下價值:其一,傳承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左權民歌”自成脈絡、獨樹一幟、意境新穎,從人民生活環境、人文歷史及地理環境等角度出發加以研究能傳承傳統文化;其二,助推民歌藝術穩健發展。從“左權民歌”大腔、雜曲、小調、開花調等藝術表演形式中學習進取,同時推動本土音樂文化與時俱進。基于此,為在守正創新前提下推動民族民間歌曲穩健發展,探析“左權民歌”中無伴奏合唱“語言”運用方略顯得尤為重要。
一、“左權民歌”闡釋
(一)“左權民歌”的起源
古代遼州即左權縣,至今約有四千年的歷史,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革命軍左權將軍在此殉國,為紀念民族英雄將當地命名為左權縣,位于山西晉中市,在太行山西側,屬于溫帶大陸氣候,降水較多,四季分明,農業生產為主,以黃土地為依托“左權民歌”誕生,成為世代傳承的民歌藝術表現形式,反應當地人們的生活生產狀態,是思想情感輸出載體。“左權民歌”就地歌唱,在發展之初無歌譜、無伴奏,人們口口相傳,具有發展性、包容性、即興性及活態流動性。在漫長的發展進程中左權縣文化、經濟等環境不斷改變,藝術創作能力有所提升,在填詞、記譜、創新基礎上賦予民歌生機,使“左權民歌”成為當地人們精神文化。在上古時期“左權民歌”萌芽,在《漢書·五行志》、《史記·楚世家》等著作中均有記載,作為祭祀活動的重要表現形式借助“左權民歌”抒發人們對先輩、自然、國家的情感,在吟唱中祈禱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左權民歌”在宋元時期朝著體系化方向發展,在明清時期表現形式、藝術風格逐漸明確,為今后民歌發展奠定基礎,使“左權民歌”成為山西本土獨特民歌文化藝術表現形式。建國后“左權民歌”變得雅俗共賞,走出本土面向全國,使之有了質的飛越,各級政府重視發展“左權民歌”,展開基層整理、挖掘、傳承、推廣工作,文化工作者前來采風,帶著“左權民歌”走出去,同時加大基層歌手培育力度,使民族民間音樂藝術表演更加成熟,理論基礎更加扎實。新時代“左權民歌”孕育生機,散發獨特藝術魅力,《開花調》、《筑路哥哥》等藝術作品蜚聲海外。
(二)“左權民歌”的分類
第一,大腔。大腔具有形式完整、結構嚴謹、曲調優雅、虛詞拖腔多、跳躍性大等特點,由蒜疙瘩(序曲)、劈破玉(正曲)、打岔(尾聲)三部分構成,其中尾聲、序曲不做改變,正曲可根據演唱者思想感情、生活體悟隨意調整,具有靈活性、發展性。大腔唱詞故事情節完整且唱法獨特,代表作品有《大小姐下秀樓》、《奇怪》等;第二,雜曲。雜曲即山歌,在田間地頭隨時可以表演,與勞動場景密不可分,屬于短歌的一種,曲調形式單一,格律相對自由,適合即興編唱,地方特點鮮明,內容囊括打夯歌、牧童歌、丑秧歌、倒秧歌等,代表作有《呆笨呆》等;第三,小調。作為“左權民歌”主要部分,小調是在人們輕松愉悅的狀態下哼唱的歌曲,小調易學易唱、內容簡短、唱詞豐富,可自行改添歌詞,代表作有《洗衣裳》、《禁洋煙》等;第四,開花調。20世紀前期在小調基礎上衍生出獨特演唱形式,即“開花調”,以“XX 開花”作為上句興起,下句則點明主題,曲式結構平行對稱,旋律明快、曲調簡短、擅長抒情,玻璃、窗簾、笤帚、石頭等均可出現在歌詞里并作為人們抒情的載體,代表作品有《苦相思》、《不想走了你返回來》、《有了心思慢慢來》等。
二、無伴奏合唱
西方教堂音樂在16 世紀誕生無伴奏合唱表演形式,適應早期教堂樂器使用少,表演形式單一大環境,用人聲替代樂器伴奏使音樂表現力增強。無伴奏合唱以純律為主,弦、音階動機及主音關聯在純音程基礎上靈活調整,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形式為奧爾加農。宗教音樂固有旋律線朝著“復音”方向發展,通過“復音”疊加使和弦聲音更加純正,以自然泛音列組理論為依托,增強和聲縱向沖擊力。無伴奏合唱對表演者聲音的把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確保演唱者在音域、自然音區中的音色既純凈又獨特,還需有極強的節奏感及聲音辨識度。無伴奏合唱流派主要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第一,理發店派。在19 世紀后期理發店派萌芽,在1940 年興盛,作為社交聚集地理發店為無伴奏合唱提供場地,主要分為男中音、主音、男高音、低音等聲部,主音聲部樂曲旋律變化多樣,其余聲部主要為和音,構成主音織體,形成該派別鮮明特點;第二,古典派。這一派別歌曲涉獵范圍較廣,以“美聲唱法”為主,根據樂譜演唱,鮮少即興創作;第三,當代流行。在20 世紀70 年代當代流行樂派興起并在90 年代興盛,通常情況下稱為“人聲樂隊”,標配人數為5 個,分別負責人聲敲擊、低音、內聲部、主音,原創是該派別特色;第四,街角派。以費城、紐約街頭藝術為依托發展而來,融入“R&B”風格,隨性表演能力較強且極具特色;第四,學院派。學院派率先在歐美大學校園興起,組合為10--20 人,每個聲部由2 人或以上人員演唱,營造合唱效果,表演時會走位或加入舞蹈,使視覺沖擊力更強。
三、“左權民歌”中的方言表現
(一)方言呈現出的多樣性
我國民族眾多且人口基數大,各民族之間呈現“大雜居、小聚居”生活生產狀態,客觀上為方言的誕生與發展奠定基礎。根據民族文化特征、地域特點可將方言分為閩方言、粵方言、吳方言、客家方言、贛方言、北方方言、湘方言等種類,基于生活習性、地域文化存在差異,區域方言與民族傳統文化息息相關,體現我國文化多樣性。音樂作品離不開語言的詮釋,合唱是語言匯總、凝結與再現的藝術載體,旨在傳遞合唱藝術作品思想感情及核心信息。為精準表達“左權民歌”中心思想,演唱者需妥善運用方言,基于方言文化背景加以處理,運用語言技術手段使歌唱藝術與生活化表達融合在一起,賦予音樂藝術作品民族性,從字頭字尾、咬字方式、腔調突出方言特色,配合運用發聲技術使方言在“左權民歌”中更具清晰性、人文性、穿透力,能增強民眾共鳴。“左權民歌”方言的應用扎根土地,多用潤腔、呼喊、甩腔并加入襯詞、虛詞、實詞,口語化特性突出,如“小親個呆”、“親疙蛋”等方言的運用,拉近受眾與民歌的距離。在個別歌詞中加上跳音、重音等音樂語匯,使音樂作品情感具有流動性,渲染歌詞意境,增強畫面感,反應群眾生活生產常態,將“左權民歌”視為人們情感輸出載體,體現作品價值觀念,使作品更加接地氣。
(二)演唱中的咬字與吐字
作為深植黃土地的民歌,“左權民歌”具有場景性、靈活性、發展性等特點,主要源于歌唱內容、方式與演唱者當時當刻的想法關系緊密,加之該民歌創造力強,可以多形式傳達思想觀念,達到藝術創作目的。“左權民歌”受方言影響咬字吐字存在一定特殊性,以《親疙蛋下河洗衣裳》為例,注意調整“韻母”、“聲母”比率,咬字更加清晰、飽滿,腔體打開突出字頭并靠前咬字,同時呼吸支點要穩定,舌面以上起音,使腔體變窄,顛倒前后鼻音,轉換平饒舌音,為使音樂藝術處理效果更優還會在個別字上做重音處理,使語氣更具多變性,音樂層級性表現效果優化,顯現出不同語氣,通過調節語調增加音樂作品地域色彩、民族色彩。在《親疙蛋下河洗衣裳》中“親”的處理字頭要加重,將其唱做“qing”,一方面受當地方言影響,另一方面體現演唱者真摯的情感,改變“裳”字咬字邏輯,突出其聲母并拉長尾音,從聽覺上給人們帶來音節向下之感,“石頭上”歌詞處理重音放在“頭”上,使歌曲畫面感更強,達到塑造生活場景目的。在此歌曲中還有“小愛愛”、“小親親”等詞匯,一方面能增強氣流摩擦,另一方面可突出后鼻音,賦予歌曲濃厚且真切的情感,在演唱“愛”時基于“ai”加入“e”的音,尾音向下且舌面抵住上額,凸顯“左權民歌”中心思想突出,情感表達直率特點。
(三)獨特的“潤腔”
潤腔是我國民族聲樂藝術經由長期發展逐漸形成且具有藝術表現力的演唱形式,這種唱腔具有潤色、裝飾、美化歌曲等功效,用情潤腔,以字行腔,用聲控腔,增強民間民族音樂藝術表現力,使歌曲回味無窮。潤腔以小轉彎、小抖音為表現形式滲透在歌曲表演進程中,通常情況下出現在基本音符附近,繼而凸顯其裝飾作用,即興表現力較強。在《親疙蛋下河洗衣裳》中重視潤腔的靈活運用,充分體現音樂特色,使音樂作品更具美感及抒情能力。以“親疙蛋下河洗衣裳,雙疙丁跪在石頭上,小親個呆”為例,通過對歌詞進行剖析可知其洋溢情愛及青春之感,完美刻畫愛人形象,在河畔有姑娘洗衣服,雙膝跪在石頭上,身姿優美,用“甩”、“搓”等動詞再現心愛的女孩洗衣服的情境,為抒發“哥哥”的思想感情奠定基礎。在表達戀人之間濃郁的愛意進程中運用獨特的“潤腔”,使作品情感更具感染力。
(四)富有民族性的“甩腔”
在“左權民歌”演唱進程中“甩腔”的運用能突出作品民族性,以特殊的人文、地理、經濟等環境為依托基于“對答”的形式詮釋作品,體現距離較遠兩人情感碰撞場景,借助山谷的回音使情感升華,為人物交流互動提供有力條件,在《親疙蛋下河洗衣裳》中哥哥聲音由山上傳下來,而后妹妹在山下用歌聲回復并唱給哥哥聽。“甩腔”賦予音樂作品流動性、交互性,使人物情感、形象更為鮮明,凸顯文化活態,基于音樂屬性合唱能增強“左權民歌”表演形式穩定性,在積極及有效的發聲位置完成表演任務,使角色塑造效果更優。
四、“左權民歌”無伴奏合唱的改編及發展對策
(一)無伴奏合唱的改編
“左權民歌”在無伴奏基礎上合唱,將當地民歌曲調視為改編主體,融入無伴奏多聲部藝術處理手段,其中五聲調式得以廣泛應用,曲式結構分為2 段體、3 段體,“ABA”形式較多,在引子、尾聲部分場景、地域特色鮮明,作品層次豐富。民歌曲調是旋律橫向表現主體,基于“左權民歌”固有元素加入同音,通過點綴使音樂表現性更強,在用句反復運用進程中3 度、6 度、7 度跳進形式較為常見。無伴奏合唱改編能增強主旋律,從縱向著手縮減和聲占比,加之復調寫作技法的應用,在2 聲部、3 聲部模仿演唱,賦予低聲部補充性、擴展性,使同聲部交替演繹主旋律,音樂角色更為靈活多變,在音程變化過程中增強“左權民歌”合唱表演戲劇沖突,有利于提升音樂作品感染力,為塑造人物性格,渲染歌曲氣氛給予支持。在節奏形態中凸顯民歌原本特色,其他聲部在主旋律演唱時恰當利用附點、切分、連線,音階模進在八分音符及十六分音符中廣泛運用,使“左權民歌”無伴奏合唱更具流動性,同時從力度、速度兩個角度出發增強音樂作品趣味性、戲劇性。
(二)“左權民歌”無伴奏合唱的發展對策
第一,針對音樂形態進行分析,剖析情境、對白、人物、情感等特點,明晰方言與無伴奏民歌合唱之間的緊密關聯,旨在突出民歌特殊性,保障曲式結構、咬字發音、聲部旋律等方面的處理科學到位,達到用方言詮釋民歌思想內涵目的;第二,賦予合唱與音場和諧性,在合唱指揮下落實二度創作目標,發揮演唱者主體能動性,確保配合默契,音色、唱法、音響三位一體,體現“左權民歌”無伴奏演唱傳承性,在借鑒西方傳統合唱演出經驗前提下以本民族音樂文化為載體強調方言特色,同時體現民族音樂傳統文化包容性、多樣性;第三,加強專業培訓,使演唱者能正確詮釋方言內涵,完成無伴奏合唱任務,通過呼吸訓練、聲音訓練、合唱隊形排練等途徑提升演唱者綜合素養,使之具備駕馭“左權民歌”演唱技巧的能力;第四,樹立研究意識,做好專項研究工作,將聲部職能、角色轉換、作品布局等視為研究基點,不斷搜集左權方言,通過針對性研究使人們對方言內涵的解讀更為深入,能保護方言,同時可妥善運用方言資源加大無伴奏合唱音樂藝術作品創新力度,運用方言背后的人文歷史使音樂作品更具價值,不僅符合新時代審美標準,還具有文化傳承積極意義,將民歌技術性與文化性融合在一起,賦予“左權民歌”生機與活力。
結 語
綜上所述,“左權民歌”在新時代的研究、傳承、發展具有推廣優秀傳統文化,從民間民族音樂藝術中汲取養分,助推無伴奏合唱藝術穩健發展必要性。這就需要人們在明晰“左權民歌”特點前提下靈活運用方言,賦予方言藝術表現形式多樣性,妥善處理咬字與發音,運用獨特的“甩腔”、“潤腔”,加大無伴奏合唱改編力度,同時針對音樂形態進行分析,賦予合唱與音場和諧性,加強專業訓練,樹立研究意識,使方言作為音樂語言的一種可以得到高效利用,繼而助推“左權民歌”無伴奏合唱藝術形式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