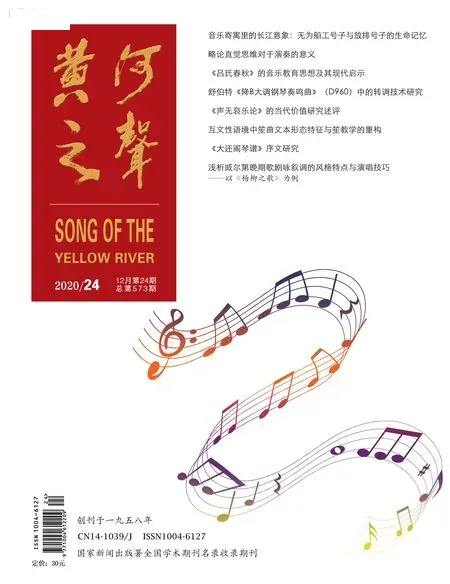互文性語境中笙曲文本形態特征與笙教學的重構
陳 碩
笙藝術的專業化發展已經走過了一個甲子的歷程,六十余年來,在眾多笙藝術家的共同努力下,使這件古老的民族樂器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在樂器改革、音樂創作、舞臺演奏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從器樂藝術繼承與發展的角度看,其最為根本的在于人才的培養,作為培養笙專業藝術人才的重要途徑,笙教學在整個笙藝術實踐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從當下笙專業教學的情況看,傳統的“傳授-接受-練習-解惑”仍然是課堂的主流模式,在教學內容方面,以“技術訓練”中心仍然是笙教學的本位思想,在這種傳統教學結構下,其弊端在于我們所培養的對象只是樂器技術的“操作熟練工”,而不是能夠駕馭舞臺、詮釋音樂、抒發情志的演奏家。因此出于這一思考,筆者引入了西方現代文藝中的互文性理論,從這一理論的語境中對笙曲的文本形態及其特征進行概念上的理解,在探求笙曲文本與教學元素的多位關系基礎上,對當下及未來的笙教學進行思考。
一、互文性與笙曲文本形態
“互文性”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由法國文藝理論家朱莉亞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一個學術概念,此概念最初在文學領域中運用,把作品以及構成作品的元素當作一種文本,其核心定義在于每一個文本或者與文本相關聯的元素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先前、現在的文本有著密切的聯系,即“語詞(或文本)是眾多詞語(和文本)的交匯,人們至少可以從中讀出另一個語詞(或文本)來”,之后法國文學評論家、符號學家羅蘭巴特對互文性及其文本又進行了更加通俗化的闡釋:“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個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種多少能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文本”,這就說明了對于一個文本(作品)的研究,不能僅把目光聚焦文本自身,而是要對其自身和產生自身的“外圍”、“他性”事物進行綜合化的探究,即在研究文學自身的同時,還需從多元化學科的角度進行觀照和比較,可以說互文性概念的提出,對于文藝作品的研究而言指明了一條新的道路,即把具體的文本置于一個已經架構好的“網絡”之中,從經度和緯度中探究要研究的問題。
互文性理論提出之后,最初運用于文學研究中,之后又被引用到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翻譯學等不同的學科領域,并取得了諸多的研究成果。從當前音樂學研究的視域看,也開始引用了互文性的相關理論,特別是在音樂美學的研究中運用的最為廣泛。就國內而言,主要的代表成果有謝嘉幸《音樂的語境-一種音樂解釋學視域》(《中國音樂》2005 年第一期)、黃漢華《音樂互文性問題之探討》(《音樂研究》2007 年第三期)、魏昇《互文性音樂創作音樂意義—對互文性視域中的音樂創作并及意義相關問題的探討》(《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1 年第一期)等。從以上文獻的研究成果看,對音樂互文性的研究已經從初步逐漸走向深入,而且多集中在美學和分析學等一般的音樂學理論范疇中,本文則是在引用互文性元理論和以上文獻成果觀點的基礎上,闡述笙曲文本的角度進行探討。
從互文性語境中看,我們稱與音樂相關的文本叫做“音樂文本”,基本上表述為兩種形態,一種是音響文本,指由聲音作為物質基礎的文本;第二種為非音響文本,指的是與文本相關的非音響特質的主客觀事物或者元素,如文本的主體元素(作曲家)、自然地理因素(與風格形成有關)、社會歷史因素(時代與文藝思潮)、演員修養(對音樂的理解和舞臺表現)等。因此從以上兩種文本形態上看,我們對作品的研究就不能僅局限于從音樂本體的角度,而是要將其置于更為廣泛的視野中進行綜合性的研究,并從時代發展的角度來看待笙曲文本,才能更好的在教學過程中實現對樂曲的詮釋。
在互文性概念的闡釋上,克里斯蒂娃認為“文字詞語之概念,不是一個固定的點,不具有一成不變的意義,而是文本空間的交匯,是若干文字的對話,即作家的、受述者的或(相關)人物的,現在或先前的文化語境中諸多文本的對話”,在這一概念中所涉及到的“先前”、“現在”等詞語,實際上說明的是與文本有關的共時性文本與歷時性文本這兩個維度,而且相互之間呈現出的都是互文本關系。首先,從歷時性文本的角度看,其互文關系為當前文本與先前文本有著承接及對應關系,當前文本在音響和非音響方面都與先前文本有著前后繼承與發展的關聯,如在笙教學中的很多練習曲目,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民間樂曲,通過主體的吸收、拼湊和改變被運用到教學中,諸如此類的樂曲有山東民間樂曲《尺字開門》、《朝天子》、《抬花轎》,山西民間樂曲《普庵咒》、《西方藏》等,以上樂曲原為民間的戲曲曲牌或者民歌小調、他類器樂曲牌,而在轉化為笙曲過程中,通過主體的移植和改編,樂曲雖然在音響方面有著共通之處,但是在價值和功能意義上又發生了變化,也由此形成了前后兩者的歷時互文關系。其次從共時性文本的角度看,其互文關系為當前文本與同時期文本有著借鑒和對應關系,體現出的是對同時代現象和本質的反映,其具體的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美學意義上的互文關系,指的是文本雖然不同,但是在音樂意義上有著密切關聯性,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創作的很多笙曲,體現出歌頌時代的美學價值,如《水庫引來金鳳凰》(王慶琛曲)、《林海新歌》(唐富曲)、《南海漁歌》(蘇安國、王慧然、胡天泉曲)等,這些樂曲都集中的反映出贊美社會主義制度、謳歌時代的共同審美趨向;二是風格意義上的互文關系,指的是文本雖然不同,但是在音樂風格上有著共同的民族性、地域性、時代性特點。單就地域性而言,產生于同一時代的笙曲,在地域風格上就形成了互文關系,如產生于五、六十年代的《鳳凰展翅》(董洪德、胡天泉曲)、《孔雀開屏》、《晉調》(均為閆海登曲)所呈現出的是山西風格特色,產生于七十年代末的《掛紅燈》(肖江、牟善平曲)、《織網歌》(牟善平、苗晶、肖江曲)等則表現出了是山東風格特色。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明顯的看出,在互文性語境中,音樂文本實際上包含了音響文本和非音響文本兩種類型,從兩者的時間維度上看,有具體包括歷時性和共時性兩種文本特點,而這兩種文本呈現出的是一種互文關系。由此可知,任何一個笙曲文本所包含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其外在與內在的表現、價值和意義足以能夠說明在笙藝術的各項實踐中都很有必要這種互文性的存在。
二、教學角色與笙曲文本的多維互文關系
在任何的教學活動中,無疑包含兩個最為核心的元素,一是教學內容,二是教學角色。在教學內容上,笙曲是最為直接的內容載體,因此在本文中不妨把笙曲文本定位為教學內容;而教學角色則是教師與學生,即傳授者和接受者。傳統教學語境中,教師和學生的關系為“傳授-接受”關系,而且這種關系自有教學活動始一直延續至今。通過以上對互文性理論的論述,把笙曲文本(內容)和教學角色(活動主體)置于互文語境中進行觀照,實際上又進一步形成了一種多維關系,進而“傳授-接受”的傳統教學模式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筆者認為,這種多維關系可以具體的表現為三個方面:
一是教學角色與笙曲音響文本之間的互文關系。在笙教學中,笙曲音響文本是貫穿于整個教學過程中,音響的呈現過程也是也是教學效果的實現過程。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在實現笙曲音響的過程中,都是經過代代傳承而來,而且都是從最初的模仿開始,逐漸形成自我認知的音響風格。特別是在當今講求風格多元化、音響豐富化的深刻時代背景下,同一笙曲文本在音響的呈現上會有所不同,這也就說明了一個問題,在教學角色中,學生在師承某一位教師時,是從音響“模仿”的角度開始的,然而這種“模仿”過程只是一個階段和過程,是暫時性的,在互文性的條件下,笙曲的音響文本也不會一成不變,也必將會在不同演奏者的理解中而呈現出不同的音響特點。這也說明在教學角色的師生繼承關系中,必然會從繼承走向發展,從守舊走向創新,即教學角色之間的繼承性造就了笙曲音響文本的發展性,其所呈現出的是音響文本的歷時性互文特征。
二是教學角色與笙曲非音響文本的互文關系。前文論述到,音樂中的非音響文本所包含的元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主體、自然地理因素、社會歷史因素、演員修養等。但就教學角色中的師生而言,由于在年齡、社會經驗、人生閱歷、音樂理解、藝術修養等方面的差異性,在對笙曲的認識和實踐上也是不同的,雖然他們在教學內容上都是針對同一對象,但是在笙曲的詮釋上仍然有著理解上的偏差。因此這就體現出互文關系中一個最為明顯的特征,即歷時與共時兩者所共同存在的差異性特點,這種差異性就存在于教學角色之間的差異上。在一定階段內,笙曲的某一非音響文本元素是不變的,如笙曲所反映出的時代印跡、美學特點、音樂風格等,可以視之為笙曲的“固化特質”,但是由于角色差異性的存在,在對笙曲的理解上往往出現偏差。如當下年輕一代的習笙者就很難理解五六十年代笙曲中所體現出的內涵,雖然有著駕馭演奏技術的能力,但是對笙曲所產生的時代背景、情感體驗與內涵有著認識上的不足。因此教學角色與笙曲非音響文本之間的有著互文上的差異性關系。
三是教學角色內部之間與笙曲文本的互文關系。從音樂實踐的角度看,包含創作、演奏(演唱)、欣賞三個環節。笙教學既屬于教學實踐范疇,也是一種音樂實踐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主要包含了演奏和欣賞兩個環節。這也就構成了師生角色的共通性,即兩者既是演奏者,也是欣賞者。兩者的聯結點就在于笙曲文本。無論是對于笙曲音響文本還是非音響文本,都是兩個角色所需要共同研習的,在這一層關系中,對于教師而言,所達到的要求和目的是做到“溫故而知新”,對于學生而言則是獲取新知,掌握更多的演奏技藝,即兩者在演奏和審美體驗的過程中達成了一種共識,一種對藝術追求的共鳴。而對于笙曲文本而言,通過角色之間的實踐活動,則是起到對笙曲文本的繼承與發展,對笙曲文本的創作起到了能動的反作用,使音樂實踐不斷的循環往復下去,表現出一個良性的發展趨勢。所以教學角色內部與笙曲文本之間則呈現出的是一種繼承與發展的互文關系。
由上述可知,在笙教學中,教學角色與笙曲文本之間的關系是具有多維特點,而且從笙曲文本的互文性特點角度又進一步推演出了教學角色與笙曲文本的互文關系。從中可以看出,笙教學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傳授-接受”過程,也不只是一個繼承過程,這里面既有著教學角色的差異性,也有著笙曲文本的發展創新性,其折射出的是笙藝術的時代發展和長久發展的命題。
三、互文性笙曲文本背景下笙教學的重構途徑
在這種多維互文關系的特點下,實際上又對當下笙專業教學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需要跳出傳統教學模式的框架,探求更加符合時代的教學新模式。笙曲文本的歷時性互文特點要求我們要善于對笙曲進行繼承和創新,而共時性的互文特點則要求我們要加強對笙曲風格以及相關元素的認識。因此從互文性語境下笙曲文本形態的角度看,當下和未來的笙專業教學應當努力把握好四個方向,也是對笙教學結構進行重構的四個方面:
一是對于傳統笙曲而言,要做到尊重與傳承相結合。從當前笙教學的內容看,無論是練習曲還是演奏曲,傳統笙曲仍然處于重要位置。筆者認為,傳統笙曲應當包含兩種文本形態,即民間樂曲和歷久彌新的經典創作笙曲。以上這兩種都是經過歷史傳承和價值認定的優秀笙曲文本,而且都富于民族審美傳統和時代意義。尊重傳統笙曲實際上就是要認識這些笙曲的價值,特別是在傳統笙的教學中,很多的技術練習以及對地域風格的學習都是民間樂曲作為文本載體,甚至很多的改編、創作笙曲也都是以這些民間樂曲作為素材;其次就是對于經典的創作笙曲而言,這些樂曲都集中的體現和反映出了時代特點,反映出了不同時期笙樂的美學特征。從傳承的角度看,主要針對笙曲中所體現出的民族精神、審美情趣,充分把笙樂中所體現出的“和”之思想進行傳承,即要傳承笙及其音樂的文化意義。
二是對于笙演奏技術而言,要做到創新與開拓相結合。從教學角色與笙曲文本的互文關系看,角色內部演奏與審美體驗的共同性特征對笙曲的創作產生了能動的反作用。同時對笙的演奏技術發展而言,也起到了創新與開拓的作用。在互文性語境下,師生關系表現出的是一種合作探究關系,在相互交流和碰撞過程中,也必然會擦出創新性的火花。笙教學既是傳承過程,也是探究創新過程,這就說明了,在笙教學過程中,不僅要注重對現有知識的傳承,對于師生而言,還應當成為笙演奏技術的探究者,從深層意義上看,正如前文說道。笙曲文本的互文性特征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各種實踐過程中逐漸發展的,因此笙演奏技術的發展更加需要在教學過程中實現創新與開拓。
三是從人才培養上看,要做到復合培養與自我培養相結合。從六十余年來笙藝術的發展趨勢可以看出,最為明顯的發展就是體裁的多元化,笙獨奏、笙重奏以及現代民族管弦樂隊中的笙聲部的發展和完善,以及各種型制笙的出現,要求習笙者要做到一專多能,在樂器上要駕馭不同型制的笙,而且在還要掌握不同的音樂體裁。因此在音樂院校的笙專業的設置上,需要更加的走向多元化,才能適應于時代發展的要求。而從笙曲文本的角度看,現在的文本結構已經呈現出“網狀”特點,各種體裁、題材、風格的文本已經不勝枚舉,而且各文本也都具有互文本的特點,在這種條件下,對于習笙者個人而言,在接受專業教育的同時,還需要加強自我的個人修養,包括文化修養、理論學習等,雖然演奏技術可以通過刻苦練習在短時間內可以掌握,但是文化理論的學習確實一個長時間甚至是終生的一個積累過程,沒有文化理論的鋪墊,如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只能實現技術化表現,而難于實現藝術化表達。
四是在舞臺表演上,要做到風格與情感的統一。笙教學的目的就是培養笙的復合性人才,舞臺表演作為人才展現和教學成果的實現過程,是全面鑒定一名笙演奏者是否能夠駕馭舞臺的重要途徑。非音響笙曲文本的互文性特點要求演奏者在演奏過程中要深入的把握好三個方面,即演奏者對笙曲文本的理解、演奏者對演奏技術的掌握、風格與情感的統一,這三者之中,風格與情感的統一可以說是居于核心位置,在風格的表現上,需要做到對笙曲中民族性、地域性、時代性風格的表現,同時還需要體現出演奏者個人的舞臺風范,在情感的表現上,則是對笙曲中所要表達的音樂內涵、音響意義通過與演奏者自身情感的共鳴來體現。對于演奏者而言,要實現舞臺表演中風格與情感的統一,需要建立在笙教學的基礎上。
結 語
綜上所述,從互文性理論的角度來審視當前的笙專業教學,可以說是存在著角度的不足之處,通過對笙曲文本形態的互文性研究以及與教學角色之間的關系可以看出,在笙教學以及人才培養方面要始終與時代的發展保持高度的一直,互文性語境中笙曲文本呈現出的是繼承與發展的趨勢,而要適應這一趨勢,就必須從根本上改善笙的教學結構,對教學角色要進行重塑,從教學角色和笙曲文本的關系看,其所呈現出的三種互文關系已經十分明確了教師、學生、笙曲三者之間的關聯性,從這三種互文關系角度出發,也相應的對笙教學進行重新的認識。因此從笙曲文本的互文性研究的角度看,實際上為笙教學指明了一條切實可行的發展道路,對笙藝術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動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