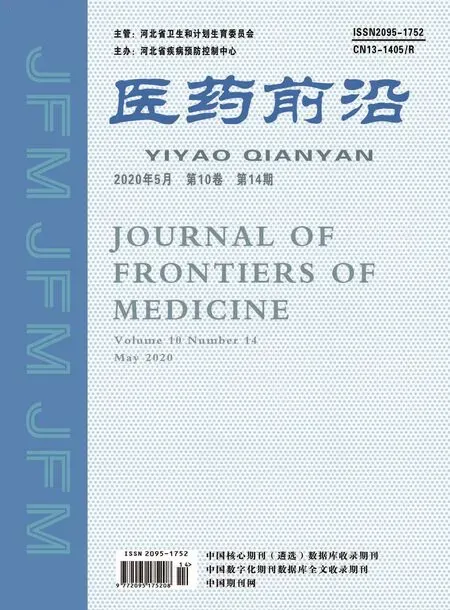兒童矮小癥發病原因及研究進展
陸毅
(百色市婦幼保健院 廣西 百色 533000)
矮小癥可因自身生長變異或疾病引起,導致患兒出現身體各個系統發育延遲或身材矮小等,通常無病理性病變。但年長發生矮小癥的患兒常伴有病理性疾病[1-2]。目前,臨床認為兒童矮小癥多因生長激素缺乏癥、營養不良、Turner 綜合征等[3-4]。介于此,筆者以近年來常見的矮小癥患兒的病因,作綜述如下。
1.正常生長變異
1.1 家族性矮小癥
最常見的正常變異就是家族性或遺傳性矮小癥,是因遺傳因素引起,其家庭成員或父母身材矮小(平均低于155cm),臨床表現為:出生時身材偏矮,生產速度正常,其生長曲線與正常兒童的曲線平行,但始終處于低限[5]。家族性矮小癥與病理性矮小癥相比,在整個生長發育過程中,患兒的生長速度降低;與體質性矮小癥相比,家族性矮小的骨齡延遲不顯著[6]。
1.2 體質性生長發育延遲
體質性生長發育延遲主要影響兒童時期身高,但不影響患兒的終身高。患者在剛出生時均為正常身高,但在3 ~4 歲時,身高增長速度降至正常最低值,除增長延緩外,還伴有青春發育延遲現象[7]。身高與同齡人身高存在差異,但經青春期后,身高會逐漸趕上正常。與家族性矮小相比,本病存在明顯的骨齡延遲。因為骨齡的延遲,增強了患兒的增長潛能,生長時間高于正常人,但成年身高是正常的。有研究表明[8],體質性生長發育延遲患兒在多數情況下,其父母雙方或一方存在青春發育延遲史。
1.3 特發性矮小
特發性矮小(idiopathic short stature,ISS),生長激素正常,不伴有潛在病理狀態的身材矮小,與正常兒童平均身高相比,其身高低于兩個標準差,生長緩慢,但患兒在分娩、嬰兒期正常,無生長緩慢現象[9]。其病因尚不明確,是兒童矮小常見原因[10]。學者連學剛[11]在研究中對62 例特發性矮小患兒,抽簽法分成對照組(采用葡萄糖酸鈣口服液治療)和觀察組(采用葡萄糖酸鈣口服液+生長激素治療),各31例。結果為:實驗組的生長速率、身高、IGF-1 測量值(生長速率:12.54±0.80cm/年;身高:126.97±9.10cm;IGF-1 測量值:448.33±8.20μg/L)均顯著高于對照組(生長速率:8.30±0.46cm/年;身高:114.20±8.21cm;IGF-1 測量值:385.20±7.51μg/L),差異顯著(P<0.05)。實驗組的不良反應發生率6.45%(2/31)明顯低于對照組25.81%(8/31),差異顯著(P<0.05)。實驗組患兒家屬的滿意度96.77%(30/31)高于對照組80.65%(25/31),差異顯著(P<0.05)。表明,對于特發性矮小癥患兒,應用生長激素治療,能夠有效提高患者身高,改善IGF-1 水平,降低不良反應發生率,安全性高。
1.4 小于胎齡兒
多數小于胎齡兒均會經歷追趕生長期(2 ~3 年),且多數身高處于正常偏低水平。而在追趕生長期的嬰兒階段,表現為:生長發育延遲,但在兒童期時,患兒與同齡兒的預測身高相似,均可使用家族身高進行預測[12]。小于胎齡兒受母體因素、胎盤因素的影響,導致出生后會經歷全力追趕生長階段。對于嚴重小于胎齡兒,其3 歲時也未達到正常身高,則屬于病理性矮小癥[13]。
2.病理性身材矮小
2.1 營養不良
兒童矮小癥的主要原因是營養不良,因營養攝入不足、吸收不良引起[14]。營養不良可獨自發生,如:因經濟條件食物供給不足、自我飲食限制、機體潛在因素限制營養攝入或吸收或全身性疾病引起。多數營養不良患兒多因營養攝入不足、長期缺失高蛋白等引起。本病屬于暫時性生長遲緩,若合理調整飲食結構、攝入足夠的營養,其生長速度逐漸恢復并至正常水平。
2.2 生長激素缺乏癥
在病理性身材矮小中占比例最高的是生長激素缺乏癥(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GHD)。生長激素(Growth Hormone,GH),有垂體牽引促生長細胞合成和分泌,能夠調節物質代謝,促進個體身高,進而促進骨骼和生長發育。有研究表明,兒童身高增長的主要原因是長骨骨干與骨骺之間軟骨細胞分裂增殖,進而促進人體生長[15]。生長激素缺乏癥其主要病因包括:生長激素結構異常、受體缺陷以及垂體前葉合成和分泌生長激素部分或完全缺失等,導致患兒出現生長障礙性疾病。生長激素是人體促生長的主要因素,經下丘腦分泌,促使生長激素釋放激素。目前臨床對于生長激素缺乏癥患兒治療,多采用基因重組激素,于體外合成生長激素,以改善生長激素缺乏情況[16]。學者王盼盼[17]等在對生長激素缺乏癥(CHD)患兒的研究中,選擇137例生長激素缺乏癥患兒,收集患兒的身高(Ht)、體重(Wt)、BMI、血清生長因素(GH)、血清IGF-1 等指標。結果為:患兒的BIM 與IGF-1 呈正相關,其IGF-1 水平受到患兒的性別、年齡、BIM 以及青春期狀態等因素影響。其在BMI、SDS <0.30 組中,每增加1 個單位的BMI、SDS,將會減低2%的IGF-1、SDS,差異顯著(P<0.05)。在BMI、SDS ≥0.30 組中,每增加1 個單位的BMI、SDS,將會增加93%BMI、SDS,差異顯著(P<0.05)。調整了混合因素(性別、血小板、肌酐、促黃體生成素、雌二醇、睪酮等)后,青春期前的GHD 患兒每增加1 個單位,將會增加39.3%的IGF-1、SDS,其每增加1 個單位BMI,將會降低98.8%的IGF-1、SDS,差異顯著(P<0.05)。表明:GHD 患兒的性別、BMI 以及青春期狀態等因素影響IGF-1 水平,且適宜的BMI 有利于患兒的生長發育。對于青春期前的生長激素缺乏癥患兒適當增加BMI,并適當控制BMI,有利于維持較高的IGF-1水平,進而有利于患兒的生長發育。
2.3 胃腸道疾病
胃腸道疾病也可引起兒童出現矮小癥,本病對患兒的體質量的影響遠高于對身高的影響。患兒受胃腸道疾病的影響,引起腸道炎癥性疾病進展,患兒攝入食物量減少,導致其生長受到限制,影響其正常發育。此外,患兒受到糖皮質激素治療的影響,導致兒童矮小癥發生[18]。
2.4 性早熟
性早熟是指青春期提前出現(女孩8 歲前,男孩9 歲前),出現第二性征,即為性早熟[19]。性早熟主要分為中樞性和外周性性早熟。中樞性性早熟以提前啟動下丘腦-垂體-性腺軸為標志性特點,表現為:女孩乳房增大或男孩睪丸增大、性激素分泌增加等。外周性性早熟由罕見腫瘤、腎上腺疾病、外源攝入過多性激素引起。兒童出現性早熟,引起骨齡快速增長,明顯提前生理年齡,縮短生長年限。若不及時控制性早熟進展,將會提前閉合骨骺,停止身高增長。雖然這些性早熟患兒年幼時身高較同齡兒高,但成年后身高往往低于平均水平。因此,對于性早熟兒童要對其予以更多的關注。
2.5 遺傳代謝性疾病
2.5.1 Turner 綜合征
Turner 綜合征,又叫:先天性卵巢發育不全,是臨床常見的染色體畸變疾病,具有多樣的染色體核型,是女孩常見的矮小癥病因[20]。當女孩出現矮小癥時,重點考慮Turner 綜合癥,絕大多數Turner 綜合征女孩,都存在身材矮小現象,且與預測平均身高低20cm 左右。同時,多數患兒還會出現青春期發育延遲現象,可能存在盾狀胸、膝外翻、肘外翻等現象[21]。
2.5.2 Noonan 綜合征
Noonan 綜合征屬常染色體顯性遺傳性疾病,主要表現為:心臟病、身材矮小、面部輕微畸形等,部分患兒存在智力障礙、漏斗胸、隱睪、出血、水腫,還可合并神經母細胞瘤、胚胎性橫紋肌肉瘤等嚴重癌癥。學者劉子勤[22]等研究中,以7 例Noonan患兒為例,經過全外顯子聯合Sanger測序完成家系分析和解讀。結果為:7 例Noonan 患兒中,共4 例男孩,3 例女孩,均為生長緩慢就診,其中6 例患兒具有本病特征性面容;6 例患兒存在色素沉著以及頭發卷曲、脊柱側彎以及隱睪等特征;6 例患兒智力發育遲緩;4 例患兒的生長激素激發實驗峰值>10ng/ml,無類胰島素生長異常現象;5 例患兒心臟結構異常;7 例患兒均發現PTPN11 基因錯義突變;6 例患兒為新生突變。表明:Noonan 綜合征,以生長緩慢為主要表現,可出現身材矮小、智力發育落后、特殊面容以及心臟結構改變等。
3.其他原因
3.1 甲狀腺功能低下
作為兒童常見內分泌疾病的先天性甲狀腺功能減低癥(CH),主因患兒先天性甲狀腺缺陷或孕婦在孕期飲食中缺碘引起,以智力和體格發育障礙為主要表現[23]。但因甲狀腺功能低下引起的智力低下具有不可逆性。因此,為保證兒童體格、智力的正常發展,需及時發現并治療。
3.2 21-三體綜合征
21-三體綜合征,又叫Down 綜合征或先天愚型,是人體常見的常染色體疾病,以智力落后、生長遲緩、特殊面容為臨床表現,且伴有多發畸形[24]。以人體第21 號染色體呈三體征為細胞遺傳學特征,患兒在出生后會出現輕度宮內發育遲緩、身高偏矮等癥狀[25]。
4.小結
兒童矮小癥,不僅給患兒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交等帶來沉重影響,還給家庭帶來沉重的心理及經濟負擔。影響兒童患有矮小癥的原因較多,本文綜述了正常生長變異(家族性矮小癥、體質性生長發育延遲、特發性矮小、小于胎齡兒)、病理性身材矮小(營養不良、生長激素缺乏癥、胃腸道疾病、性早熟以及遺傳代謝性疾病)以及其他原因(甲狀腺功能低下、21-三體綜合征)等幾種主要誘發兒童矮小癥的病因。多數矮小癥患兒常表現為:精神、心理障礙、性格內向及社交能力欠缺等癥狀。因此,臨床在對兒童矮小癥進行治療中,除治療矮小癥外,還需協調患兒家屬共同進行心理疏導和引導。筆者建議:(1)全面營養:每天制定詳細的飲食計劃,保證攝入足夠的蛋白質、膳食纖維以及維生素等,保證飲食種類多樣,做到患兒不偏食不挑食。(2)合理鍛煉:制定適合患兒的體育鍛煉計劃,如:跳繩、打籃球、摸高等,增強其體質,促進生長發育,明顯改善身高情況。(3)充足睡眠:充足的睡眠是長高的必備條件,因為生長激素的分泌高峰在深睡眠中,所以身高的增長,必然在晚上進行。(4)愉悅心情:現代心理學家認為,影響長高的因素包括:精神、情緒等。所以家屬必須維持一個平和愉悅的環境,促進兒童健康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