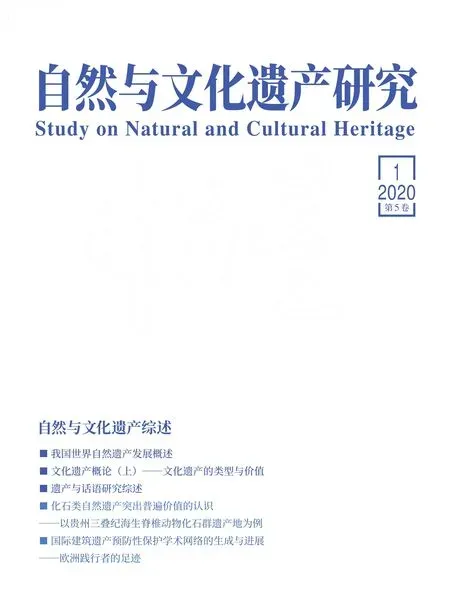以遺產價值為核心的取舍
——關于白鶴梁遺產保護和展示行動的評述
王思渝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北京 100871)
白鶴梁坐落于今重慶市涪陵區,1988年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3年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啟動,白鶴梁被迫整體長久淹沒于水下。為了應對其保護和展示需求,在前期調查、多方驗證和長期討論的基礎上,最終選定所謂的“無壓容器”方案。2003年當地啟動白鶴梁原址水下保護工程,2009年建成白鶴梁水下博物館,2010年對觀眾開放。2012年白鶴梁題刻被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本文目的在于對圍繞著白鶴梁的這一系列以當代遺產觀為導向的保護和展示行動做出整體評述。
對于今日遺產研究工作來說,想要評述一個特定的遺產對象或工程項目,首先需要為評述對象尋找到其自身標尺和依據。此時,國際國內既有的一系列遺產保護文件或政策及其背后的精神,通常構成了大多數學者展開此類討論的骨架。而如若以此作為標尺,尤其是考慮到從《威尼斯憲章》到《奈良真實性文件》當中的“真實性”提法,白鶴梁的遺產保護和展示行動在今天看來確實是存在爭議的。例如,在整體長久淹沒之后,構成白鶴梁的遺產價值要素中重要一環的“石魚出水”景觀不復得見,這也意味著遺產本體所處的基本環境有了明顯的變化,以及由此所引發的節慶習俗式的人文社會活動缺乏了進一步開展的基礎。這些問題都對慣有的遺產話語體系構成了挑戰。
那么,存在著這樣的爭議和挑戰是否便意味著需要全面否定白鶴梁這一系列行動的價值呢?
結合上述研究可以認為,白鶴梁的保護和展示行動是在充分考慮了遺產自身價值要素的基礎上,在現實的政治和技術條件下,對真實性要素做出了取舍。
這種以特定遺產價值為核心來對真實性加以取舍的邏輯,在以《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下文簡稱《操作指南》)為代表的一系列標尺當中也是被承認的,最為基本例證在于《操作指南》自身的書寫邏輯。《操作指南》首先要求判定遺產自身所具備的突出普遍價值,再行討論這種價值基礎之上的真實性與完整性。這種類似的邏輯在世界各國的遺產官方名錄評定中都能看到。因此,這實際上也是在提示相關人員在討論特定的保護和展示行動時,應該將問題的核心聚焦在后天操作是否會影響特定話語體系下被普遍認可的價值之上,而非只要有看似“不真實”的后天操作便對其進行全盤否定。
就白鶴梁來說,其價值核心要素主要圍繞題刻本身所承載的水文科學價值和地方傳統見證之上。由此,這便引申出兩個核心問題,其一是題刻,其二是見證。
對于題刻而言,白鶴梁題刻更接近于通常討論遺產對象時所說的本體。本體在物理實體層面的存續和安全歷來是當代遺產理念和行動所建立起來的基石,這也是白鶴梁現有保護工程(包括后期的監測工作)所完成的第一步。然而以該基石為核心,當代遺產理念和實踐不僅僅滿足于這種存續和安全,從20世紀以來逐漸衍生出評價該基石是否真實的存續和安全的一系列標準,最為典型的便是《奈良真實性文件》當中的12條標準。那么,余下來的問題便在于,在產生了這12條標準之后,是否便意味著所有的保護和展示行動都必須要盡數滿足,不可取舍呢?
在更宏觀的政治經濟背景下,考慮到諸多不可抗因素,白鶴梁只能取舍。而在取舍之時,它的行動實際上展現了兩方面的邏輯。
第一,從這些標尺本身出發,擇其核心進行取舍。《奈良真實性文件》雖然無意對這12條提法做出排序,但是縱觀從《威尼斯憲章》以來的一系列“真實性”提法,位置與環境實際上一直是當代遺產理念當中關于“真實”最為核心的部分。這從遺產理念自身的發展變化歷史當中能夠看出,也以此解釋了為何在遺產研究領域對于重建、異地搬遷等問題歷來敏感。這在史靖塬、史耀華[7]、郭旃[8]、呂舟[9]等人的研究當中均能看到。
第二,從遺產對象本身的價值出發,擇其核心進行取舍。回到白鶴梁本身來說,白鶴梁作為一種遺產,在整個遺產類型體系的角度來說,它最為特殊的一點便在于其作為一種水文觀測的見證,被稱之為“水下遺產”。
因此,這兩方面的邏輯共同解釋了為何圍繞著白鶴梁的一系列行動在做價值取舍時,會反復強調把題刻繼續留在石梁和水環境當中的重要性。
在經歷過這種價值取舍之后仍然得到主流遺產話語體系認可的案例實際上已經不在少數,例如遺產研究者常提的華沙、伊勢神宮等案例。在評定這樣的案例時,其與白鶴梁案例所反映的情況在本質上是類似的,均是在一種當代遺產理念框架下的價值取舍,只不過各自面臨的背景、取和舍的內容有所不同罷了。
所謂“見證”,實際上也意味著一種文化傳統或現象有著不復存在的可能性。從白鶴梁題刻申報“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的文本來看,它想要對應的實際上是突出普遍價值十條標準中的標準iii[10]。而具體到《操作指南》當中,全文是用“bear a unique or at least exceptional testimony to a cultural tradition or to a civilization which is living or which has disappeared”來表述的。換言之,這里已經明文表達了消失(disappear)的合理性。因此,白鶴梁長期永久淹沒之后所消失的記錄水文的科學價值和當地社群繼續圍觀“石魚出水”的社會民俗價值,并不影響其曾經是一種見證。
只不過,在當代遺產理念和實踐當中,會盡量避免是由遺產保護或展示行動而刻意導致這種價值消失。具體到白鶴梁的情況來說,水文科學價值的消失自我國現代水文監測技術進入長江流域之后便已存在,文人登梁賦詩的傳統也隨著現代性下知識分子的結構和慣習的改變而已很難存續。因此,這些均非由當代保護和展示行動所造就。
在這個角度上,最值得爭議的問題反而在于:由保護和展示行動所導致的觀“石魚出水”社會民俗傳統的中斷問題。這也直接影響到遺產地與在地社區之間的關系延續問題,在當下遺產理念中也是愈發被重視的話題。當然,這個問題在白鶴梁的當下實踐中也并非全未被注意。白鶴梁水下博物館的現有展示中已融入該部分的內容。博物館對外開放,并成為涪陵區重要的文化宣傳名片,這都為在地社區保留關于“白鶴時鳴”“石魚出水”的社會記憶提供了重要的輔助,成為塑造地方集體認同的重要一環。也或由于白鶴梁本身常年位于水下,不影響在地社區的日常生活,依靠遺產旅游還能為當地帶來外部性收益,因此白鶴梁所面臨的社區關系相較于諸多大范圍遺產對象而言更好處理。只是在展示的技術手段、對于口述史記憶和檔案材料的進一步發掘與保存、鄉土教育的傳承等方面,白鶴梁尚有待探索更多方式。
總體而言,本文試圖站在遺產話語體系內部去考慮白鶴梁這樣一個傳統認為在經典遺產話語體系內看似有所爭議的案例,從而在盡量對白鶴梁做出準確評述的同時,也以之為窗口,折射出遺產話語體系內所慣有的一系列價值邏輯。實際上,放眼當代遺產保護運動發展的整體歷程,今天的遺產研究已經開始承認,遺產保護本身是一種介入和干涉,只不過這種介入和干涉并不是一個無序或無理的過程,而是順應民族國家、現代性、科學主義式的研究,乃至后期的社會民權式思想所衍生出來了一套自洽的邏輯。這套邏輯自身不一定具備足夠的合理性和正當性,但想要在這套邏輯的基礎上做出進一步的批評和發展,那么理解且不滿足于這套邏輯應當是首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