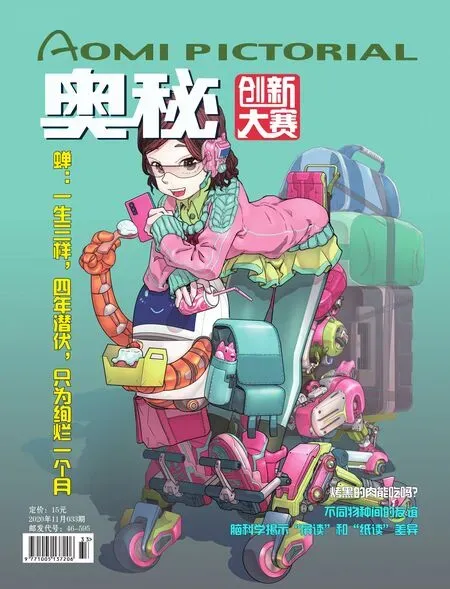腦科學揭示“屏讀”和“紙讀”差異
●夢潔 編 ○景老人 繪

信息化時代,我們的生活在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閱讀方式以及概念也在悄然變化,屏幕閱讀正在逐漸成為日常。那是否就可以讓年幼的孩子們直接拋棄“紙讀”,用“屏讀”來獲取知識呢?本文就從腦科學角度為我們揭示“屏讀”與“紙讀”的差異,幫助我們更加客觀、科學地認識和思考。
數字化時代閱讀,塑造閱讀雙腦
毫無疑問,在數字化時代,閱讀的概念正在發生變化,人們越來越多地通過屏幕,而不是通過紙質文本獲取更多信息和進行閱讀。我們正處于被各種屏幕包圍的世界:電視、電腦、筆記本、手機、電子閱讀器……以屏幕為載體的數字化閱讀方式正在成為人們的選擇。
第17次全民閱讀調查顯示:2019年我國成年國民各媒介綜合閱讀率保持增長勢頭,數字化閱讀方式(網絡在線閱讀、手機閱讀、電子閱讀器閱讀,PAD閱讀等)接觸率為79.3%,較2018年的76.2%上升了3.1個百分點。
這樣的趨勢不僅反映了成年人的閱讀方式,也反映在出生于互聯網時代,在互聯網環境中長大孩子的身上。第一次接觸電屏幕閱讀的年齡不斷提前,這些孩子通常被稱為“互聯網土著”。
屏讀,正在改變我們的閱讀品質
我們是否會冷靜地去思考一些問題:在當前的技術環境下,我們是否正在改變閱讀的含義?閱讀方式的改變是否意味閱讀文化和價值的重塑?閱讀者在屏讀和紙讀時思維方式和閱讀習慣的差異何在?新一代人正在用新的方式連接大腦,培養出對未來媒體環境有益的技能,是有利于還是有損閱讀?
如今,許多神經認知、閱讀和兒童發展等研究領域的專家,正在試圖通過研究來回答這些問題,引導人們正確地認識屏讀這一新生事物。
在《科學美國人》的一篇文章上,研究者賈布聲稱“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發表的大多數研究支持‘紙讀作為閱讀媒介,仍然比屏幕有優勢,’這一說法。”文章還例舉了紙讀優于屏讀的四個原因:數字設備阻止人們有效地瀏覽長文本,這可能會微妙地抑制閱讀理解;與紙讀相比,屏讀需要讀者消耗更多的腦力資源,并使我們在閱讀時更難記住所讀的內容;不管讀者的閱讀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人們在接觸電腦或平板電腦時,他們并沒有像紙讀時那么心定神閑;屏讀無法創造紙上閱讀的某些觸覺體驗,有些讀者在缺乏這些體驗時會感到不安。
這些原因歸根到底,是由于閱讀環境、閱讀媒介和閱讀方式發生變化,而導致閱讀品質流失,或者影響了讀者成為流利、優秀的閱讀者。
古人說讀書學習時應該“俯而學,仰而思”:“俯而學”,就是沉下心去深入學習,潛心鉆研;“仰而思”,就是在學習過程中思考,理論聯系實際。不善于讀思結合,最終是無法達到讀書的真正目的地。
閱讀是需要靜下心來的。讀者在屏讀時,由于屏幕發光的顯示、閃爍的通知、經常會跳出來的廣告以及超鏈接等非閱讀內容的干擾,往往更容易分心。讀者會在多模態的閱讀元素之間來回跳躍,這對于好奇心很強的孩子來說,影響和危害會更大。
很多孩子,包括成年人通常將閱讀誤認為一個單一的 任務:閱讀一篇文章或者拿起一本書閱讀。其實,良好的閱讀包括一系列不同的、經常是相互交織的動作,如一開始就能通過閱讀前的預讀猜測文本;在閱讀和注釋的過程中架構意義;重讀,不僅是一次,而且是多次加深理解和建構意義;批判性地提問促進讀者自我與文本的對話;用更多的注釋、筆記來消除理解困難,用筆將重點劃出來強化記憶,這些都是每一個成功的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厭其煩、樂此不疲做的動作。
屏讀,還會給讀者帶來一種“不可掌控感”和“無力感”。數字文本幾乎沒有紙質文本的觸覺感。在紙讀時,一張張的紙,凝固的文本和可劃寫的紙張,會帶給讀者觸覺。這是紙讀所帶來的一種愉悅體驗,是屏讀所不能企及的。而且,在紙讀時,讀者更能找到他們所讀的內容。讀者為了對文字間建立聯系、做出推論,或者解決疑問,還可以來回輕松地在不同的頁碼上切換,這一點在屏讀時是無法實現的。


還有,為什么在一本紙質書上做顯示和記號對閱讀是必不可少的?阿德勒和范多倫在《如何閱讀一本書》一書中說到:首先,這種方法讓你保持清醒。其次,閱讀,如果它是活躍的,就是思考,而思考傾向于用語言來表達,無論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有記號的書通常是經過思考的書。最后,記號可以幫助你記住你的想法,或者作者表達的想法。這是讀者與文本互動的最佳體現。
屏讀,更多的是一種略讀方式
某種程度上,在線技術是專門為搜索信息,而不是分析復雜的想法而設計的,那么“閱讀”的意義在屏讀時會變成“發現信息”而不是“思考和理解”。
閱讀研究專家曼根通過對網絡讀者行為的描述,認為屏讀主要是略讀或者淺層閱讀:讀者常常是瀏覽和掃描、關鍵詞識別、一次性閱讀、非線性閱讀和選擇性閱讀,深度閱讀的行為甚少,對于長篇幅的文章會避之不及。
略讀或者淺層閱讀,能夠滿足人們在快速時間內獲取信息,或者豐富多感官體驗的愿望,但是長久以往的話,會付出代價。這樣的代價是深層次閱讀行為的缺失:嚴肅地獲取知識、歸納分析、批判性思維、想象力和反思。這樣的閱讀行為本身是閱讀的本質追尋,也一直是解決閱讀問題的關鍵所在。
如果略讀或者淺讀一直主導屏讀的話,那么對于閱讀原本存在的痼疾和問題無疑是雪上加霜,推波助瀾,對大腦進行深度閱讀以獲得復雜理解能力,產生負面的影響。
作為“閱讀大腦的研究者”,塔夫茨大學閱讀與語言中心主任、神經科學家沃爾夫從神經科學、文學和人類發展的角度來記錄兒童和成人沉浸在數字媒體中時大腦發生的變化。她說:當人們快速而短暫地處理信息時,會限制大腦“沉思維度”的發展,而這一沉思維度為人類提供了形成洞察力和移情力的能力。
其實,在這個日益數字化的世界里,我們比以往更需要培養孩子的深度閱讀能力。深度閱讀能力是對閱讀積極熱忱、高度專注、自主控制和深度思考的能力。
人類大腦遠遠沒有適應新的模式
人類的智力水平和認知能力,不僅僅是大腦進化的結果,而是適應環境和社會變化,相互互動的結果。無論是人類群體,還是讀者個體,閱讀的行為和大腦進化并不是天生的,是時光老人的杰作和人類主動發展的結果。人類是經過上萬年漫長歲月沉淀,才形成如今的閱讀模式和行為方式。

譬如,兩足行走、解放雙手、手勢交流與人類語言的進化有著密切的聯系。人們在日常語言中,仍然使用各種重要的身體動作進行交流,如手和手指的運動、面部表情、感嘆、語調,微笑與笑聲。
認知腦神經學家告訴我們,人的大腦并非為閱讀而生,把原生態大腦改造成閱讀腦需要長達十余年、循序漸進的努力,才能完成。這種改造不僅僅是認知層面的改變,更是大腦生理結構的改變。無論是中文閱讀者還是英文閱讀者,只有在長期的閱讀行為鍛造后,才會在左側枕-顳區打造出一小塊專門處理文字信息的腦區,腦神經學家稱之為“文字盒子區”。
人類數字化閱讀的歷史并不長,僅僅數十年而已,但是數字化呈現方式卻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字的物理形式。文字不再與介質相聯系,具有極強的可塑性、可移動性。
在信息技術的幫助下,人們獲取文字的方式和閱讀的方式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類大腦遠遠沒有適應新的模式,不可避免地需要建立與閱讀的新關系、新的智力技巧和新的閱讀方式。我們的大腦具有強大的可塑性,大腦回路正在重新布線,鼓勵大腦呈現出人類正在閱讀的任何媒介的特征,但是這一切需要時間。
培養“雙讀”大腦
歷史總會重演,經常會出現人們擔心新技術會破壞舊技能的例子。公元前5世紀末,當文字傳播正在挑戰口頭傳統時,柏拉圖曾表達過擔憂:“信賴文字會阻止我們記憶。”
其實,這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我們如何從兩者中得到最好的結果。有一點我們必須深信:我們必須改造我們的大腦,適應數字閱讀,鼓勵批判性閱讀和思維的技能,瞄準特別適合數字文本的新技能,并制定教學和評估策略,以幫助孩子培養他們所需的批判性思維,無論他們所讀的是何種類型的文本閱讀。
考夫曼和弗拉納根指出,當閱讀紙質書時,受試者在回答需要推理的抽象問題時表現更好;相比之下,在回答具體問題時,參與者在數字閱讀方面的得分更高。
我們應該教會我們的孩子,根據哪種媒介確定適合閱讀的目的。在閱讀之前,家長要想一想你希望孩子從閱讀中獲得什么。當孩子們只需要掌握和了解主要信息或思想時,屏讀并不比紙讀效果差,而且速度會快很多,在閱讀結束之后,家長通常可以問問孩子主要讀到了什么。但是,如果想要孩子深入理解和綜合觀點,那就讓孩子打印或者購買紙質材料,然后用傳統的方式閱讀。
家長可以合理安排不同比例或者數量的文本類型,并采取相應的閱讀方法,鼓勵孩子在紙質閱讀和屏幕閱讀中切換,培養在各種媒介使用的思維習慣,要幫助孩子建立連接紙質閱讀技能和數字閱讀技能的橋梁。
我們需要培養出一種“雙讀”大腦,即利用每種閱讀風格的最佳技能,讓孩子既可以在線閱讀,也可以在紙質文本上進行深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