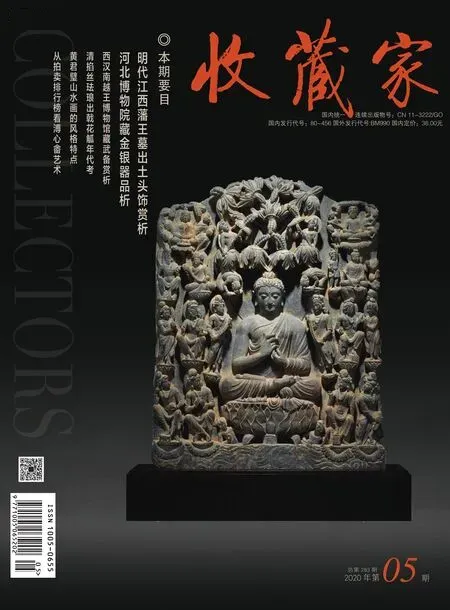審美此間的溫度
□ 明揚
對比時下流行變換著的工業風、極簡風、性冷淡風,我越來越喜歡有著溫暖氣息的懷舊風,那些器物有著歲月包漿的顏色和質感。不知道這是不是與我年歲日長的心態有關。
年輕的時候,我更喜歡有些個性甚或是小眾的東西,并以此沾沾自喜。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總是需要急迫的定義自己,所以也一直在確認自己這些個性表達到底屬于哪一種風格的,哪一個流派的;是不是更高級的,更脫俗的,甚至是更潮流的或更正確的。
后來經歷很多事,經歷了每個人都一樣的那些瑣碎和無法言說的煩惱,雖說這些事似乎都和審美沒有任何關系,然而,回頭看去的時候,他們確實就是這樣悄然的改變了我的品味和目光。審美的偏愛就這樣隨著我們閱歷的增長和內心狀態的改變而有了改變。
美的感知是個性化的
逐漸覺得“審美”也是一種挺個人的事,這里我不想說藝術歷史的發展,也不敢去評論藝術殿堂里那些神壇上的作品,那些毋庸置疑公認的美可能需要被教育、被解讀,才能被公眾認知和欣賞。而我更想陳述的是一個普通人對美和美好的感知,這種感知不需要我們是藝術大師或設計師,甚至不需要懂得任何專業知識,是從心而發的感知力。
在我看來“審美取向”的選擇應該是一個人對自己的理解,我們內在狀態的呈現,我們精神里某種追求的外顯。你審的“美”往往就是最能與你有情緒共鳴的事物。
之于此,所以某個瞬間我也就懂了曾經無法接受的“俗”態,讀懂了春節里那些固執喜慶的紅色,商場里無限循環播放的“財神到”,還有媽媽桃紅艷綠的插花。民俗是生活化的,民俗化的審美其實也未嘗不可。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價值追求,有人追求樸素生活,有人追求花開富貴,有人追求清寂和雅,有人追求哲思,有人追求信仰,但哪有高下之分?所以,只要我們認真有所追求,審美必然也是多元化的,審美也終是個性化的。
顯化的精神力
美是什么呢?我們認同什么,什么就是美。我們眼中的美是我們所認同的理想和情感的具象化表達。當我懷念故人和故鄉時,地面上那一抹照耀此地也照耀遠方的月光就是美的。月光讓濃厚的情感有了顯現,甚至觸手可及。這一份美,它生動有形的展現了我的熱愛。
審美是我們精神世界追求里最凝煉、最極致的表達,是在這一類的價值追求里抽象純粹的高頻能量。也是我們個體人格對精神力量的求索和朝拜,把個體人格推向更崇高、更無限、更整體的境界。所以我也曾認為,美是最靠近自然和神性的。
文化背景下的美
曾經一個畫家朋友做了一次山水畫分享,講到元四家,講山水寫意和留白的孤寂意境。那是對我理解中式審美的啟蒙之作。后來也逐漸發覺在中式審美里大多都是在講究意趣和造境,我們的作品大多都并不寫實,而是通過營造氣氛來表達心中的意。比如中式插花,講究枝條的曲線和形態里的張力;書法里運筆走筆的風骨;戲曲唱腔里婉轉濃郁或蕩氣回腸的情緒。
民族的審美往往就是民族性格的呈現,我們“寫意”是因為我們的性格更為含蓄,然而這含蓄當中蘊含的精神追求卻非常飽滿。這份飽滿的情緒傳達,又要用心體會,須要沉浸當中去才可玩味,從而獲得“意趣”。
無論東方或西方,某一類共性的審美,往往都是基于某一群體共性的精神追求,這就是民族的文化底蘊吧。
美有溫度
有朋友收藏了一個有年代的風箏線軸,線軸古舊,除了歲月風塵外,軸上還落了原主人留下的“穿云、入霧、凌霄、系日”四句題刻。生活中的普通物件因為這個解讀,憑添了更高遠的氣質。朋友說曾經的主人也一定是個有理想有志趣的雅士,原主人的溫度就留在了這個物件上。
還有一個閱讀來的小故事,是老父親招待女兒的客人,
親手做了一盤裹了蜂蜜的小蘿卜,還每顆用心的插了牙簽。女兒嗔怪還不如切盤蘋果,卻沒理解父親別具風味的不俗和雅致。
那些釀造在煙火生活里動人的心機,讓平凡變得充滿美好,沒有一顆審美的心,怎么抵抗這粗礪的歲月。這樣的美低調而高級,隱沒于生活俗事之間,超越形式,渾然不隔,細密的流落在生活起落的際遇里。
美,無一不是與人有關的,人文讓作品有了溫度。
因為有了個性化的選擇,有了切身的體驗,審美就可以成為我們身心的安置。我們與某一事物有了情緒的共鳴,美就產生了。一塊白玉,有人做成項飾,有人當成鎮紙;一條裙子有人穿出婀娜,有人穿出清冷;一塊石頭里的嶙峋或堅定;一株芭蕉里的豐腴或愁緒,同一件事物因為不同人的偏好和解讀而有了不同的美。
這種共鳴使我們內在與外在更為和諧,肯定世界的同時也肯定了自已,這樣的能量加持讓我們動容且愉悅,獲得了心的滋養。審美完成了寄情,寄情正是我們對內心的安置。
美可以在殿堂受人朝拜,美也可以是凡人的救贖,這份身心的妥善安置讓生命豐富美好。萬物自然生滅,沒有人就沒有所謂的美。美是人類的自覺意識,是我們生命力的表達,它一直在歌頌生命本源,生機勃勃的詮釋著生命本身。
即便是悲劇之美,殘缺之美,都是喚起了人們對美、對生、對純粹的珍視和向往。或清簡,或繁華。美是我們對生命哲學的理解,再將這理解重新賦予我們的生活。
此刻,我想坐在一個懷舊的老搖椅上,點上一支煙,放一首入心的曲子,看著窗外落日余霞,和你一起聊聊,這該是多“美”的事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