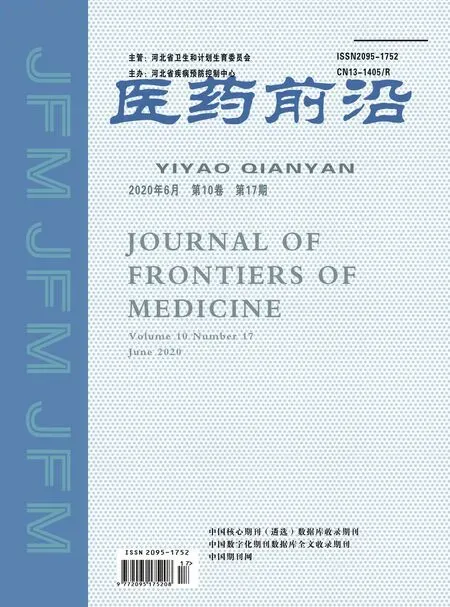小兒血漿D-二聚體檢測對診斷腹型過敏性紫癜的值分析
王春蕾 王遠萍 胡勤芝
(蘭陵縣人民醫院 山東 蘭陵 277700)
小兒腹痛為臨床常見疾病,一般分為慢性與急性腹痛。慢性腹痛造成因素較多,雖由內科疾病所致,但是病理機制較為復雜,并且患兒年齡因素,無法有效表達腹痛位置以及性質,臨床診斷面臨一定困難,極易出現誤診[1]。因此,本文對血漿D-二聚體檢測觀察對診斷小兒腹型過敏性紫癜的價值,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我院2017 年2 月—2019 年2 月前往我院就診的106 例腹痛患兒,男64例,女42例;年齡4~12歲,平均年齡(7.12±1.35)歲。排除標準:急性腹膜炎、消化道穿孔、急性闌尾炎等,血液病、肝病等影響血漿D-二聚體檢測的相關疾病。所有患兒全部進行血漿D-二聚體檢測。
1.2 方法
患兒入院后均接受常規檢查,包括糞便、尿及血、電解質、肝功能、心電圖、腎功能、C 反應蛋白以及腹部B 超檢查,并根據患兒不同的病情,適當選擇內窺鏡、腹部平片或CT 檢查。血漿D-二聚體檢測操作為:確保所有患兒清晨均保持空腹狀態,無菌環境下抽取2mL 外周靜脈血,放置在抗凝管中,1×109mmol/L枸櫞酸鈉比例為1:9,離心15min,3000r/min,然后將血漿分離,通過免疫透射比濁測定法對血漿D-二聚體進行檢測,使用血凝分析儀。血漿D-二聚體標準值為0 ~500μg/L,>500μg/L則證明血漿D-二聚體增高[2]。
1.3 數據統計處理方法
數據采用SPSS21.0統計學軟件分析處理,計數資料采用率(%)表示,行χ2檢驗,P <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 疾病類型
腸系膜淋巴結炎44 例(41.51%),急性胃炎26 例(24.52%),慢性胃炎12 例(11.32%),消化性潰瘍11 例(10.37%),腹型過敏性紫癜6例(5.66%),腸道蛔蟲癥4(3.77),便秘1例(0.94%),未確診2 例(1.88%)。
2.2 血漿D-二聚體檢測結果
106 例患兒在接受血漿D-二聚體檢測中,出現血漿D-二聚體升高有5 例,其他患兒血漿D-二聚體水平檢測結果均正常。5例升高患兒中,4 例為腹型過敏性紫癜患兒,占其比例為80.00%(4/5);1 例為消化性潰瘍患兒,其比例為20.00%(1/5)。
3.討論
慢性腹痛在小兒疾病治療中為常見疾病,其中腹型過敏性紫癜便可造成患兒慢性腹痛。過敏性紫癜分為兩種,一種以腹痛為表現,一種以消化道癥狀為表現。如果患兒腹型過敏性紫癜首發情況以消化道為主,并且皮膚紫癜現象晚于腹部癥狀出現時,臨床極易造成誤診甚至延誤治療,甚至會進行不必要的手術。針對這一情況,對腹型過敏性紫癜患兒進行早期正確的診斷,對臨床治療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醫學界認為腹型過敏性紫癜則是以IgA 為主的免疫復合物,并堆積在機體內血管壁,進而出現的白細胞碎裂性小血管炎。堆積于血管壁的免疫復合物,激活補體,從而導致細胞因子以及中性粒細胞活化,造成血管受到損傷[3]。有關研究表明,如果機體內微血管內皮發生損傷,將組織因子大量的釋放出來,外源性凝血途徑被激活,便會造成過敏性紫癜患兒出現高凝狀態,并通常會伴隨血栓出現、纖溶紊亂、血液凝血等情況的發生,也可視為血栓前的表現狀態。D-二聚體則是機體出現凝血狀態時,凝血酶將會作用在纖維蛋白上,從而轉化為交聯纖維蛋白,并且纖溶系統會隨之激活,從而生產特異性降解物,可用來降解交聯纖維蛋白[4]。因此,D-二聚體為反映患者體內繼發性纖溶亢進和高凝狀態的主要標志物之一。身體健康例的血液中該特異性的產物其水平值較低,機體內如果發生血栓形成的情況,便會激活纖維蛋白溶解系統,對血栓進行溶解,進而形成繼發性纖溶。對機體內血漿D-二聚體的水平進行檢測,如果水平值較正常值升高,則表示機體內出現繼發性纖溶[5]。
本次對血漿D-二聚體檢測診斷腹型過敏性紫癜的價值評價。結果,5 例血漿D-二聚體值升高患兒中,4 例為腹型過敏性紫癜患兒(80.00%);1 例為消化性潰瘍患兒(20.00%)。因此,血漿D-二聚體檢測可推測患兒是否患有腹型過敏性紫癜疾病,臨床可應用。
綜上所述,臨床在針對慢性腹痛患兒的診斷過程中,進行血漿D-二聚體檢測,如果其檢測值高于正常值,臨床可高度懷疑患兒患腹型過敏性紫癜。由于本次腹型過敏性紫癜例數較少,還需收集大量腹型過敏性紫癜患兒,進行血漿D-二聚體檢測,來證實這一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