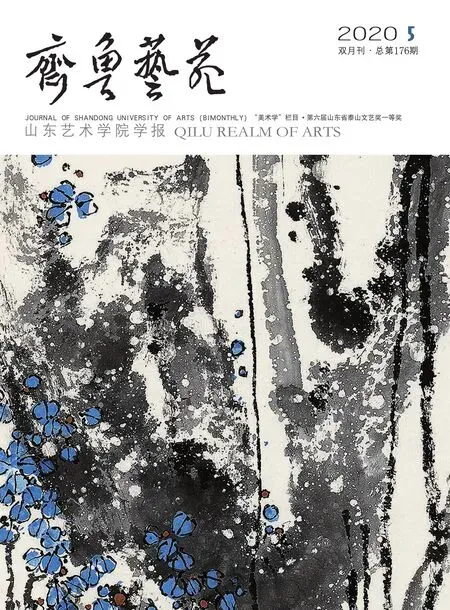五行與五色的符號化、秩序化
王 路,劉德卿
(1.山東藝術設計職業學院應用設計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2.山東藝術學院學報編輯部,山東 濟南 250014)
“與我國民族音樂的五聲音階相似,色彩藝術中的五色說是中華民族色彩美學的基礎。”[1](P24)青、赤、黃、白、黑——中華民族的五色系統是中國先民依據生命本能的色彩本質反應,遵循自然環境中的陰陽五行運化信息,在長期的社會活動中共同生成的情感知覺“太和”與“常性”靈感傳承。五色系統的內在骨架是五行說,即木、火、土、金、水五種元素或類型,作為構成宇宙、自然界萬物及各種自然現象變化的基礎,一切事物、自然現象的性質、類別都被納入這五種元素或類型的范疇,各種運行與變化都可歸為這五類元素的生勝(生克)關系。青、赤、黃、白、黑五色與其對應,即:青-木、赤-火、黃-土、白-金、黑-水,并與方位、季節一一對應即:青-東-春,赤-南-夏,黃-中-仲夏,白-西-秋,黑-北-冬。青、赤、黃、白、黑為五正色,亦有著相生、相勝關系,相勝而得五間色,即:青勝黃得綠,黃勝黑得駵黃(一說流黃,褐黃色),黑勝赤得紫,赤勝白得紅,白勝青得碧。(1)五間色所指說法不一。本文按南朝梁皇侃說。正色不是西方色彩系統中的原色概念,而是指尊貴的顏色,是色彩中的主體。間色是不正、雜色之意,因而間色不止于上述間色,而是除了五正色之外的色相都屬于間色。[2](P216)主色與間色是主與從的關系。這樣的色彩認識絕然不同于西方的科學性認知,也不同于純粹直覺的感受,而是一種象征性的、有著因果律的動態的色彩關系,并且與人的生活、宇宙成為一個息息相關的整體,顯現出人類色彩“原型”的長期存在意義。
五色觀念的淵源與形成頗為復雜,其中與中國社會早期的五行觀念有著較深關聯。關于陰陽五行,梁啟超先生在《陰陽五行說之來歷》中曾說:“陰陽五行說,為二千年來迷信的大本營。直至今日,在社會上猶有莫大勢力。”[3](P343)而顧頡剛在《五德始終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中則說:“五行,是中國人的思想律,是中國人對宇宙系統的信仰;二千余年來,它有極強固的勢力。”[4](P404)時至今日,盡管有了一些新的出土文獻,有了對于它們新的讀解,陰陽五行仍是中國文化中爭論最多,又最莫衷一是的難題。我們僅從色彩與五行的關系,分析隨著五行學說的發展,五色符號化、秩序化的邏輯進展。
一、五方-五色
五行的起源我們無從判定,但是至少在殷商時期即有此觀念顯現(或萌芽)。由上文可知,殷商時期甲骨文之中四方、四方風的存在及其作用。胡厚宜先生曾做對比考證,認為甲骨文中四方名、四方風名整套地保存在先秦古籍《山海經》和《尚書·堯典》中。[5](P61)并在《尚書·堯典》中又出現了新的名稱:暘谷(東方)、明都(南方)、昧谷(西方)、幽都(北方),和明暗有關。[6](P13-21)1945年楊樹達先生對甲骨文四方名做了辨析、解讀,認為四方名皆與草木有關,并與四時相配。[7](P79-81)《堯典》中還出現了:“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于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厥民析,鳥獸孳尾。冬寒無事,并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平秩南訛,敬致。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厥民因,鳥獸希革。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寅餞納日,平秩西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毨。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都,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于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并見,以正冬之三節。厥民隩,鳥獸氄毛。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8](P33-35)這里的“星鳥”(朱雀)、“星火”(青龍)、“星虛”(玄武)、“星昴”(白虎),是四個星座,每個星座各有七顆星組成,四七二十八顆星,又稱二十八宿。四方與相應的天文、季節掛起鉤來,并且與農作物的生長收藏相聯系。春天草木萌生,夏天炎熱似火,秋天草木(作物)蒙上一層白霜,就像作物成熟要用閃著白光的金屬刀刃收割,冬天水凝結成冰深淵無垠。春、夏、秋、冬四時可分別用木、火、金、水自然物象(意象)代表,并且可用各自的色澤:青、赤、白、黑加以辨別、區分。這里白和黑是原始色彩直覺白天和黑夜的具體化(或轉移,但都是光線明與暗的狀態)。
四方概念又不是空洞、抽象的,它是一個空間概念,它必定環衛一個中心,這就是甲骨文中的“商”或“中商”,所以四方又明顯包含了中央一方,這在商代金文中表現為“亞”系圖形文字或圖像(有式和式兩種)。按艾蘭的解釋,兩者均與中央的方形有關,為中央一個方形,東南西北各有一個方形,為一個方形,四個角被分出。[9](P108-109)正如《說文解字》對“十”字做的解釋:“數之具也。—為東西,|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所以,四方概念是于中央之外而言,加上中央才為整體(后世所謂天下、宇宙),即五方。中央(中商)以土地為國家社稷,對農作物最為重要的土理所當然放在木、火、金、水之中央,完整的五方(天下)即可用木、火、土、金、水來表示。《逸周書·作雒解》記錄的是周初周武王歿后周公建造雒(同“洛”)邑的情況:“周公……乃建大社于周中,其壝東責([匯校]責,諸體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10](P570)國家設五色土社稷壇,以其五方各自鮮明的地理顏色為標記,東部是大海青碧幽藍,長江以南廣闊的低山丘陵地帶有著我國分布面積最大的紅壤,西部是青藏高原白雪皚皚,北方大部分地帶是顏色較深、較暗的黑鈣土、栗鈣土、黑壚土,中央地帶則是黃土,五色土象征全國的土地廣博多彩,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最遲在春秋時代已成書的《洪范》通常被認為是記載原始五行說的“正式”文本:“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愛稼墻。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墻作甘。”孔穎達疏“洪范”曰:“洪,大。范,法也。言天地之大法。”[11](P297、307)
至此,由甲骨文、《山海經》,到《堯典》、《洪范》,木、火、土、金、水由五種自然物象(意象)成為構成宇宙萬物的五種基本成分或元素或性質,帶著其顏色、味道等具體的物性因素。
二、四時(五候)-相序
四方風的祭祀中已然明顯包含著四時(季節)的判定。常正光先生曾對甲骨文中的“出日”“入日”之祭進行研究:“卜辭的出入日之祭,就是以測定準確的東西方向線為基礎從而測得南北方向線的辦法……東西線可以判定春分或秋分的到來,據南北線觀測中星及斗柄的指向,又是判定夏至與冬至的一種手段。” 進一步得出度四方是定四時的基礎,四方與四時不可分割的結論。[12](P256)
與殷人崇尚四方相比,周人似乎更加重視四時。《逸周書·周月解》記載:“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13](P577-579)盡管被今人判定為夏時歷法(后人追記)的《夏小正》中存有大量物候觀察記錄,如正月“啟蟄”、二月“來降燕”、三月“鳴鴻”、四月“囿有見杏”、五月“乃瓜”、六月“煮桃”、七月“秀瞿葦”、八月“剝瓜”、九月“巡鴻雁”、十月“黑鳥浴”,但是并無四時記載。
作為儒家十三經之一的《禮記》,是西漢人對秦漢以前禮儀著述加以記錄,編纂而成,其中有一篇是《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星),昏參(星)中,旦尾(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春神,少昊后代),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蔟(十二律中的一律)。其數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天子居青陽左個(2)明堂,是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場所。青陽,古代天子明堂之東向室也。左個,即北頭室。明堂中方外圓,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個。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出玄堂。見呂不韋:《呂氏春秋通詮》,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0年。,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旗,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征,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個,乘朱路,駕赤馬,載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溜,祭先心。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馬,載黃旗,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居總章左個,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個,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14](P400-486)
這里一年中的季節里有不同的星象、尊崇帝王、敬奉之神、五蟲、五聲、律呂、五味、五臭、五祀、五臟等,春夏秋冬四季與天象星宿、天干、青赤黃白玄五色形成一一的固定關系,天子的衣食住行也都有相應不同的規定。所有這一切都因循著一年自然變化的主旋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一秩序運行、展開,天地人皆然。
春秋時期齊人管子著有《幼官》《四時》《五行》等篇。他認為四時關乎國家命脈、天地之運行:“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于時則生福,詭則生禍。”《四時》篇還記載:“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肌膚。”“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他把《易傳》的陰陽思想納入,與五方、四時相配,認為氣生陰陽再生五行,其理論成為一種以氣貫通的理論系統,并且提出警戒要人們循時而行,不可“春行冬政”等等,治國者更要“務時而寄政”。“道生天地,德出賢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圣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于春,長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3)德與刑,用董仲舒的話來解釋:“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見安平秋、張傳璽:《二十四史全譯 漢書》(第二冊),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4年,第1195頁。刑德不失,四時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為久長。不中者死,失理者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四守有所,三政執輔。”[15](P215-223)德與刑成為陰陽之于人道的作為。
在《管子·五行》中,通乎陰陽之氣,黃帝“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后天地之美生”。一年從冬至始,先是屬木,再是屬火,再是屬土,再是屬金,最后屬水,每隔72日,五行五候相序相生,每一條目中,分別敘述其宜行之事和禁忌之事。在《管子》諸篇中,與五行相匹配的項目增加了五時、五政、五氣、五德等內容。《管子》實現了中國古代陰陽思想與五行說的合流。
三、五德終始-歷史
戰國齊人鄒衍,在《史記》中被這樣記載:“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圣》之篇十余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16](P2344)他一方面提出了亙古未有的大九州推想;一方面繼承了陰陽、五行的早期觀念(特別是管子思想),提出“五德終始說”。“德”五德之德即氣運之德,即五行之用。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在《呂氏春秋》(應同篇)中還保存了比較完整的一段:
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于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17](P682-683)
五行秩序不只是相生(木生火、火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關系,更有一種相勝(木勝土、金勝木、火勝金、水勝火)的關系,由注重原來的相生之序而注重逆向的相勝之序,并且由每個歷史時期(朝代)的帝王(黃帝、大禹、商湯、周文王)代言。這里涉及到的因素只有帝王、天、物候、五行、五色。每一歷史時期(朝代)的領導者必須具備上天所要求的一種德(五行之一),不僅擁有與之相關的性質(色),還要遵循、恪守這種相關的性質,才能真正取得天下(興)。以往的歷史已經呈現出這種規律,并昭示著下一步的趨勢。這種應用于社會歷史變遷的五德終始說旋即成為戰國爭霸時代的顯學,也得到后世歷代帝王的異常重視。而五色也成為朝代變遷的征兆,成為特定的代表符號。
在孔子“正樂”“正色”禮教基礎上,漢代董仲舒進一步發揮了鄒衍的陰陽五行說,提出天人感應說。他認為:“天令之謂命,命非圣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18](P1204)天是最高的,是社會政治合理性的本元,也是人的本元和依據,人就像天的影子,但是人的本性(性如禾)還需要道德教化達成其合理性與完善(善如米),道德教化就是道德與倫理教育以及為此而設置的五經六藝和禮儀制度。“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官至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制度禮儀中色彩已經有了區分貴賤尊卑以順應天時的功能。董仲舒的主張在東漢光武帝、明帝、章帝的施政中得以實施,從此天人感應、陽尊陰卑、三綱五常理論成為中國正統官學。陰陽五行說因其成為內在于漢代儒家學派的骨架而實際作用于中國人的政治與生活直至今天,而五色以其符號性、象征性標識出五行的相生與相勝的變化之象。
《禮記》是西漢戴圣記錄、編纂的秦漢之前古代社會的制度禮儀典籍,東漢末年著名學者鄭玄為之作了出色的注解,唐代學者孔穎達作了《禮記正義》,后來這個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說經文的著作逐漸成為經典,宋明清時一直相沿尊為儒家十三經之一,為士者必讀之書。由此書的注疏可以完整看出中國社會對于色彩的觀念:
衣正色,裳間色。謂冕服,玄上纁(淺紅色)下。……○正義曰:玄是天色,故為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為間色。皇氏云(4)“謂”是鄭玄作的注解,“正義曰”是孔穎達作的注疏,“黃氏云”是皇侃的闡釋。皇侃(488~545),一作皇偘,其字不詳,吳郡(郡治在今江蘇蘇州市)人。南朝梁儒家學者、經學家。:“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也,綠、紅、碧、紫、駵(騮)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為木,木色青,木刻土,土黃,并以所刻為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為火,火赤刻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為金,金白刻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色黑,水刻火,火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駵黃是中央間,中央為土,土刻水,水黑,故駵黃之色,黃、黑也。[19](P895-897)
早在秦漢之前,就有了正色、間色概念,漢代鄭玄解釋為帝王禮服玄色在上、纁色在下,南朝梁皇侃明確指認五正色與五間色,唐代孔穎達清晰描繪了五色分別與五方、五行一一對應,五間色來源。
自唐代起,五色系統影響到中國之外亞洲范圍諸多民族的文化與藝術形式。19世紀以后,西方印象派、后印象派及表現主義的代表畫家大膽吸收、引進受到五色影響的東方意象色彩,創造出個性化的繪畫知覺形式,彰顯出五色系統的“常性”生機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