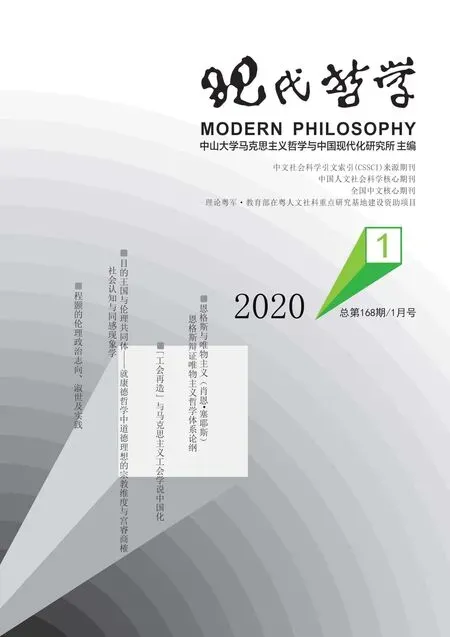道與時間
——以金岳霖《論道》為中心
方 用
“時間”是西方近現代哲學的一個重要主題。20世紀以來,“古今之爭”成為中國思想的核心問題,“進化”“歷史”等“時間”的不同表現形式被思想家廣泛關注,但對“時間”本身的思考則相對滯后。將“時間”概念主題化,是金岳霖《論道》的重要特征,也是其對20世紀中國哲學的一個貢獻。時間是主體的先天感性形式,還是天地人物的展開方式?是意志的表象,還是一去不復返的洪流?是神的創造,還是人的幻像?在人類思想史上,對時間的領悟充滿分歧,也表現出高明的理論旨趣。金岳霖從“道”出發理解與規定“時間”,既表現出深遠的現代視野,也展示著古老而深沉的中國智慧。
一、道:時間的根基
《論道》開篇直陳:“道是式-能。”(《論道》一·一)(1)本文所引用的《論道》相關引文,出自金岳霖:《金岳霖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以下均只標明《論道》相關章節,不再詳述具體頁碼。將“道”視作整個體系的邏輯起點,是金岳霖的精心設計。他認為,“時間”有本有源,是道演過程中所產生的現象。時間有形式,有內容。從根本上說,時間的形式與內容可歸結為“式”與“能”,二者最終可歸之為“道”。“式”與“能”在金岳霖哲學中有獨特含義。所謂“式”是“析取地無所不包的可能”(《論道》一·五),就是包舉無遺的所有的“可能”。所謂“可能”“是可以有而不必有‘能’的‘架子’或‘樣式’”(《論道》一·四)。“能”是象“氣”“質”一樣的純粹質料,其最大特征是“活”“動”。金岳霖以“能有出入”(《論道》一·一六)命題來表達“能”之活、動的含義,而將不斷“出入”視為“能”的基本特性,并由此展開而有了現實。
由“能”之出入,世界動起來,其動力當然就是“能”本身。因此,“能有出入”是世界川流不息的根據,也是川流不息的世界的基本原則。“能”本身不能生滅,它一直在“式”中。“能”無生滅、無增減,“式”也無生滅、無增減。式、能、道無終始,無所謂存在,都沒有時間問題。由此,金岳霖重新定義了“存在”概念:“‘存在’兩字限于具體的個體的東西底存在。”(《論道》一·一〇)就此而言,“存在”只是一“可能”,它包含在“式”中;可以有“能”,而“能”不等于“可能”。個體的東西“存在”,存在的標準之一就是占時間,它有終始,有時間,進言之,“存在”的世界也有終始。“存在”即通常說的“物”,也就是“東西”或“事體”。“物”占時間,有生死。但“物”不是“道”,“式”“能”無終始,不占時間,“道”也無終始,無時間問題。“道”是時間的本原,反之則不成立。
存在的都是“現實的”。所謂“現實”是“可能之現實”,即“可能”的有“能”。因此,“現實”的“現”不是現在的“現”,而是出現的“現”。“能”出現于一“可能”,則一可能的“可能”不僅是“可能”,而且是“共相”。進一步,“可能成了共相,就表示以那一可能為類,那一類有具體的東西以為表現”(《論道》二·一)。具體的東西表現“共相”,“共相”即為“實”。在金岳霖看來,“可能”為“有”,“共相”為“實”,特殊個體為“存”。可見,他對“有”“實”“存”的界定謹慎而又嚴格。“時間”既然為“可能”,為“共相”,則“時間”不僅為“有”,而且為“實”。“實”即“不虛”“不空”。由此,金岳霖以邏輯的方式肯定了時間的“不空”“不虛”。盡管他說的并非思想史問題,但還是以邏輯的方式回應了中國思想史的重要主題——“虛實之辨”。按照這里對“存”的規定,“時間”雖“不空”“不虛”,但卻不能說時間“存”或“不存”。
“能”是活的、動的,它一直出入于“可能”,一直在“現實”一些“可能”。“能”老有出入,“時間”作為一“可能”,其在“老有出入”過程中隨時“現實”。在此意義上,金岳霖稱時間為“老是現實的可能”(《論道》一·一一)。換言之,“時間”無時不現實。“時間”無時不現實,“終”“始”也都是現實的可能,具體而言,“‘能’入于一可能是那一可能底現實底始,‘能’出于一可能是那一可能底現實底終”(《論道》二·一九)。顯然,金岳霖一直通過“能有出入”“可能”“現實”等來界定“始”與“終”等時間的具體形態。對于“先”與“后”,他也做了類似的規定:“現實的可能底現實先于未現實的可能底現實,而未現實的可能底現實后于現實的可能底現實。”(《論道》二·一五)將“先”與“后”等日常用語精確化,視為“可能”,其內涵由“可能”之“現實”順序規定。此說雖抽象、繁瑣,卻甚是嚴密精準。
二、時間是秩序
按照通常的說法,時間是事物展開的過程。“展開過程”帶有空間意味,它可能會表現為向四方延展,甚至可能來回不定地回旋。因此,嚴格說來“展開過程”并無方向,甚至可以說無條理。金岳霖從“先”“后”視角切入時間問題,將“時間”與“秩序”問題建立關聯,或者說,“時間”由此成為“秩序”的一種表述。
在金岳霖看來,諸多可能的現實都存在先后關系,諸多先后關系由此組成一個連級關系。就其中某一可能的現實說,它在此連級中有一個至當不移的位置,此至當不移的位置就是金岳霖所論的“秩序”。 當然,存在以下狀況:兩可能開始現實時處于同一位置,但打住現實時不占同一位置;或者在開始現實時不占同一位置,而打住現實時占有同一位置。不管哪種情況,兩可能的現實之秩序都是不同的。從可能的現實之歷程看,也會存在位置差異,其先后秩序也是不同的。談秩序才有先后,有秩序之先后,才有根本不根本問題。
從“可能”與“現實”討論的時間屬于“本然世界底時間”,它與“我們現在這樣世界底時間”不同,后者即“從經驗方面著想,是具體物事底變遷歷程中的那有先后關系,所以也有不回頭的方向的秩序。我們要客觀地經驗它,離不了具體的物事;我們要客觀地而又精微地經驗它,離不了度量”(《論道》二·二二)。“我們現在這樣世界底時間”是指具體事物的時間,人們可以經驗它,也可以測量它,它也表達“不回頭的方向”。“本然世界底時間”是“先驗的時間”,它不涉及具體事物,不可以測量,可以說是“理論上的時間”。在金岳霖看來,本然世界有“變”、有“時間”、有“前后”、有“大小”,其它都難說。它可以而不必是“我們現在這樣世界”。“本然世界”的時間不會不現實,不能不現實。不過,它有個前提,即要有經驗。換言之,只要有可以經驗的世界,將來那些現實的世界哪怕不是現在這樣的世界,時間都不會不現實,不能不現實。
“本然世界”與“道的世界”也不同。“道的世界”是必然現實的世界,“必然”是邏輯的品格,無論有沒有對應于它的經驗,它都為真。以往、現在、將來等時間形態不會改變道必然現實的品格。“本然世界”是指:只要有可以經驗的世界,就得承認有此世界。“承認”與“必然”是兩回事,但無論如何,“本然世界”都是現實了的現實。
整個現實的根本問題就是現實的原則:“現實并行不悖”(《論道》三·一),“現實并行不費”(《論道》三·二)。前者是說,在任何時期,同時期的現實彼此不悖,后此時期的現實要不悖于此時期及前此時期的現實。由此,本然世界有其秩序,是能以“理”通,也能以“理”去了解的世界。根據后者,現實不會不具體化,現實的個體化是具體化的分解化、多數化。
所謂“個體”包括“個”“體”兩個概念。此“體”是“具體”之“體”,既有謂詞所能形容或摹狀的情形,也有謂詞所不能盡或不能達的情形。所謂“個”是指這個、那個的“個”,即可以與他者區分開來的“殊相”。個體有性質,也有關系。所謂“性質”即“分別地表現于個體的共相”(《論道》三·一〇),所謂“關系”即“聯合地表現于一個以上的個體的共相”(《論道》三·一一),“關系”是對于兩個或多數個體才能實現的可能。對每個個體來說,不同可能在該個體上輪轉現實與繼續現實即是其“歷史”。不管是輪轉現實,還是繼續現實,對于個體來說都是“變”。在任何時間,一個體會“變”,其它個體也會“變”。個體雖變,其變有常。因為個體雖變,但“可能”不變,“式”不變,“道”也不變。人們據“可能”“式”“道”就可以對個體的變有經驗、有知識。
可見,金岳霖以“秩序”規定“時間”,使“時間”變得容易理解、可以把握,人類的知識因此得以可能。但這個“秩序”只是本然的、必然的邏輯秩序,即通常所說的物理世界的時間秩序,而無涉于社會秩序與精神秩序。忽略了這點,就無法正視人世間的時間問題。
三、時間之實質:個體的變動
“秩序”涉及一個以上的個體之間的關系。然而,對于一個體來說,亦有秩序問題。不僅如此,在金岳霖看來,時間的實質就在個體的變動中。對于“能”來說,時間無空隙;但是對于個體來說,時間有空隙,時間之流就是“能”之出入于一個個的“可能”。他承認存在著無個體而僅有“能”的時間或空間,但是個體所能經驗的時間-空間是個體化的時間-空間,現實的時間是個體化的時間。時空不離,時間的個體化即空間的個體化。個體化的時空秩序以個體為關系者,因此,此時空秩序不是連續的秩序。
在個體化的時空中,任何時間可以漸次縮小,這縮小之極限被金岳霖稱為“時面”(《論道》五·三)。一地方的時間橫切所有的地方,任何地方的任何時間就是那時候的整個空間。在個體化的時空中,任何空間可以漸次縮小,這縮小之極限被金岳霖稱為“空線”(《論道》五·五)。空線是無空間積量的整個的時間。在常識中,個體事物有成有壞,個體事物的形式會毀滅。金岳霖則指出,個體之形式都是“可能”,而“可能”只是靜態的空架子,它們可以在時間的延續中持存。此說法的確迥異于常識。
在金岳霖看來,“時面”有空而無時,“空線”有時而無空。它們的交叉點為“時點-空點”(《論道》五·七),既無時間積量,也無空間積量。在有量時間之內,“時點-空點”是無量的。任何時面據而不居,往而不返。任何空線居而不據,不往不來。任何“時點-空點”既往而不返又居而不據,故任何“時點-空點”在時空秩序中都有至當不移的位置。個體化的時空秩序就以絕對時空秩序為根據,而絕對時空秩序以“時點-空點”為根據。
顯然,以“時點-空點”為根據所推出的絕對時空秩序對于個體具有重要意義:可以精確定位個體,獲得其至當不移的位置。但是,時空與某一個體在此視域中似乎是分離的:前者獨立存在,并可以安排、確定后者。對此個體是這樣,對所有的個體也如此。個體被完全確定,其余的可能也就不復存在。金岳霖似乎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其接下來對“特殊”的討論在一定程度上即針對于此。
以絕對時空秩序為根基,金岳霖開始討論“特殊”問題。首先,“特殊”是一現實了的“可能”,即“現實之往則不返或居則不兼的可能”(《論道》五·一四)。此意義上的“特殊”不是指這一那一特殊的東西,后者不過是現實了“特殊”這一可能的個體之物。不管是前者還是后者,“特殊”之為“特殊”就在于在任何一時間內,所有的個體都占據惟一無二的空間,即“居則不兼”。同時,在任何空間,所有的個體都在時間川流中分別地往而不返。或者說,一時間不能有同地點的兩個體,在同一地點,任何一個體不能與其它個體同往返。
以時空位置的特殊來討論個體的特殊,對于個體來說,這似乎有些外在。金岳霖也試圖從“殊相”來理解特殊的個體:“個體之所以為個體,不僅因為它是具體的,不僅因為它大都有一套特別的性質與關系,也因為它有它底殊相。而它底殊相不是任何其它個體所有的。殊相底殊就是特殊底殊,它是一個體之所獨有,它底現實總是某時某地的事體。”(《論道》五·二四)性質、關系是個體特殊之內在要素,每一個體都有其獨有的性質、關系,這是特殊的重要內涵。不過,他仍然強調殊相之殊與時空位置之殊不可分。
特殊個體的變動是變更其空間上的位置,其動有過去,有現在。“過去”曾經現實,其絕對時間的位置不會改變,已往是怎樣,它就是那樣。“現在”亦然,“現在或現代是已來而未往的現實……現在不是空空洞洞的,它不僅是已來而未往,它也是已來而未往的現實”(《論道》五·二六)。就時間說,“已來而未往”是指個體在時間上的位置是固定的,其所經過的歷程不能重復地再現。一旦現實,它就不會變更其絕對時間之位置。世界之“實在”,時間之“不虛”,皆可由此說。就個體說,它是具體的,因此是現實的。所以,個體都有其“現在”,都相對于一“現在”,止于一“現在”。“將來的個體”僅僅是可能,它可能現實而不必現實。
個體的變動有共相之關聯,有因果,也有殊相之生滅。所謂“因果是個體變動中的共相底關聯;生滅是個體變動中殊相底來往”(《論道》六·二一)。就共相的關聯說,個體的變動可以為人所理解。就殊相之生滅說,生為殊,滅為殊。沒有無殊相的時間,任何時間內總有殊相之生滅。無生滅的既不是個體,也不是特殊,也就無所謂過去、現在、將來等時間形態。所以金岳霖說:“個體即時間底實質。”(《論道》六·二六)“道”沒有現實與否問題,也沒有現在、未來問題。
金岳霖以絕對時間來看待個體,個體被精確定位,由此理解個體成為可能。當他強調個體之“殊”的時候,個體、時間的豐富性被凸顯出來,這又超越了理解的范圍。在這看似矛盾的表述中,金岳霖已然碰觸到了理性理解的限度。
四、個體之時間:運與命
將來的個體僅僅是可能,“能”不斷出入于此可能,一些可能不斷現實。金岳霖將未入而即將入、未出而即將出階段稱為“幾”。當然,“幾”也有不同情況。從“能”之即出即入于“可能”言為“理幾”, 從“能”之即出入于個體的殊相而言為“勢幾”。二者都表達未來而即將要來、未去而即將要去之態。由“幾”看,個體的變動沒有“決定”的意義,將來不是已經決定的將來。整個現實歷程就是“能”之即出即入的歷程,必然、固然、當然的理由都不足以解釋“為什么會這樣”。
“能”之出入歷程中,在某個時間,“能”不僅可以出入,而且“會出會入”。金岳霖將“能之會出會入”稱為“數”。“會”含有“一定”之意,但不是“必定”“必然”。“會入就是未入而不會不入,會出就是未出而不會不出……這‘會’雖不是必然的‘必’,而仍有不能或免底意思。”(《論道》七·七)“不能或免”是說時間上的限制,有決定的意思,其根據是“理”。某個體的變動有其“數”是說,某個體的變動無所逃于“數”。但是,其變動究竟在哪個確定的時間發生則不能確定。
金岳霖還用“運”“命”兩個概念表達“幾”和“數”。“相干于一個體底幾對于該個體為運。”(《論道》七·六)“相干于一個體底數對于該個體為命。”(《論道》七·一一)所有個體的“運”都是“幾”,所有個體的“命”都是“數”。個體的變動莫不出于“運”、入于“運”,最終又無所逃于“命”。“命”無可挽回,無所逃,有決定的意味。
一方面,個體的變動不為“幾”先、不為“幾”后,莫不出于“運”、入于“運”;另一方面,又無所逃于“數”“命”。二者合起來就是現實之如此如彼,也就是金岳霖所說的時間之“時”:“幾與數謂之時……它既是時空的時,也是普通所謂時勢的時,也是以后所要談到得于時或失于時的時。最根本的仍是時間的時。”(《論道》七·一五)相較于對時間靜的看法,即將時間視為空架子以安排事物,金岳霖在此更多強調的是時間的內容,即動態的時間。“一時間之所以為該時間就是那些個體底變動,而那些個體底變動之所以為那些個體底變動也就是該時間。每一特殊的時候總有與它相當的,或相應的個體底變動,而一堆個體底變動也總有與它相當的或相應的時間。”(《論道》七·一五)時間之動就是一時間之內個體的動,時間的實質、內容就是此個體的動,也就是該個體之“幾”與“數”。時間是“幾”與“數”,而“幾”與“數”也總是時間、時勢。“運”即“幾”,“命”即“數”,因此也可以說,一個體的“運”與“命”即是該個體的時間。
人是萬物之一,個人也是個體之一種。對個體及個體變動的論述也適合作為個體的人。此即是說,時間是衡量、安排個人活動的架構,由此可以看人的秩序。同時,個人的變動構成了人的時間之實質。簡要地說,個人的“運”與“命”構成他的時間。然而,金岳霖對人深深失望,也無興趣對人的命、運多置一詞。
以一貫的嚴密精確來規定“幾”“數”“運”“命”等概念,其價值不僅在于“澄清”它們的語義,更在于在現代語境下為這些概念重新賦義。以此為基礎,金岳霖從“命”“運”來理解與規定個體的“時間”,強調的不再限于時間中“質”的成分——“綿延”(近于“幾”“運”),而更多的是時間中的“量”,如“趨向”與“界限”(“數”“命”)等要素。就對時間的理解說,這個觀念無疑更健全。
五、現實的方向:無極而太極
《論道》始于“道”而歸于“道”。“道”是一切的開端與根據,也是一切的終極歸宿。它展開為式-能,可能有能而現實。由現實而個體化,由個體的變動而有時空。由時空而規定特殊個體,個體變動有幾有數,最終方向是情盡性、用歸體。變動之極,勢歸于理,盡順絕逆。金岳霖又稱這個歷程為“無極而太極”。
“無極”是依照既定時間向上推演,推到極限即“無極”。從時間角度看,無極是既往,是在任何時間之前。作為極限之極,無極為未開的混沌,為“無”。此“無”不是絕對的“無”、 “毫無”的“無”、“空無所有”的“無”、邏輯上不可能的“無”,而是能生“有”的“無”。在無極中,老是現實的可能還沒有現實,但無極是現實,是不能沒有的現實,是未開的現實。無極中有共相的關聯即理,但此理未顯;無極中有勢而勢未發。
“無極而太極”的歷程中,“能”出入于“可能”,個體變動而“理”顯發出來。在金岳霖看來,“理”沒有例外。但“理”為多,在某一時間究竟哪一個“理”現實,這是無法確定的。由此可說,“理有固然,勢無必至”(《論道》八·七)。也就是說,特殊的事體如何發展是一個不定的歷程。
就個體說,金岳霖區分了“性”與“情”、“體”與“用”。所謂“個體底共相存于一個體者為性,相對于其它個體者為體,個體底殊相存于一個體者為情,相對于其它個體者為用”(《論道》八·八)。個體的變動,總是“情求盡性,用求得體”(《論道》八·九)。這可以看作是個體變動的方向,也可以看作是“勢”求歸于“理”。在“求”的過程中,有順有逆,但一個體在任何時間都不會盡其所有的“性”,也不會得其“體”。但此趨勢不會打住,變動不會打住,也就是說,時間沒有最后,世界沒有末日。變動的極限是各性皆盡,各體皆得,勢歸于理。此無終的極限金岳霖稱為“太極”。“太極”是現實歷程的目的、宗旨與歸宿,它秩序井然且對人有價值,即“至真、至善、至美、至如”(《論道》八·一六)。“太極”是所有可能都現實,因此是無所不包的現實。其中的將來也都現實,因此它無變動、無時間。
“無極”現實,“太極”現實,“無極而太極”的歷程也現實。在金岳霖看來,“無極而太極”之“而”表達現實之歷程,它包括曾經現實、老是現實、正在現實以及將來現實,這個歷程比現實大,比天演大。“無極而太極”就是“道”。由此,作為世界開端與根據的“道”經歷種種現實歷程,達到價值目標,最終又復歸到道一之“道”,合起來說的“道”。作為開端與根據的“道”無終始、無時間,作為無極而太極的“道”也無終始、無時間。時間只是道演過程中暫時出現的現象,或者說,只是在“道”的根基上涌現出來的特定現象,隨著道演過程的展開,時間亦會最終消失。盡管金岳霖沒有用人格神字眼,但這與某些宗教所說的神創造時間等說法一樣神秘而玄虛。當他最后把真善美如等價值加入“太極”(先撇開此價值從何而來問題),實際上已經再次把時間與價值剝離,道演過程遂成為冰冷的、無生機的無人之境。這樣的體系究竟能給予人多少安身立命的養分?“道”又如何能夠“動心”“養性”“怡情”呢?
六、時間與“意味”
在《知識論》中,金岳霖不再思考時間的根基、形式、內容等形而上的問題,而更注重作為人們理解架構的時間。從知識論來說,有“時空意念”問題。康德把時空作為先天感性形式,并利用時空來整理感性材料,以供給知性范疇,二者結合,形成知識。金岳霖認為,“時間意念”不是先天的,但它們卻是積極接受所與的模型。具體而言,時間意念抽象地摹狀時間,就是在川流中找到架子。比如,以日、月作為時間的架子,形成時間意念,并用這樣的架子來呈現時間。有了時間架子(單位),也就有了秩序。由此,人們可以以時間意念架子還治時間以及所有的變動。時間、變動經過時間意念架子的收容、整理,有了秩序,就可以被理解。可以看出,盡管角度與《論道》有差異,但注重時間之秩序義,《知識論》與《論道》乃是一貫的。
從知識論立場出發,金岳霖區分了“本然的時間”與“自然的時間”,其差異在于后者相對于“官覺類”(如人、貓)。無論有無官覺類,本然界之無極而太極的道演歷程不變。道演歷程可謂“本然的洪流”,有洪流就有時間,或者說,洪流本身就是時間。相對于官覺類的時間是“自然的時間”。相對于官覺類,自然的時間又可以分為“主觀感覺中的時間”與“客觀的、個體的時間”,前者比如“度日如年”的時間,后者可以用個體去表示的時間,也就是用地點或特殊事物去表示的時間。“自然的時間”在所與中呈現出來,呈現中的時間就是變更的先后與快慢秩序,所與呈現變更的先后與快慢秩序同時也是時間。“自然的時間”川流不停,去而不回頭。它有內容(即“幾”與“數”),同時又是架子。前者動,似乎不可捉摸;后者靜,可以用來捉摸川流的時間。可以發現,《論道》中未曾出場的官覺類已經在“自然”中出現。有了官覺類,就在“客觀的時間”之外增添了“主觀的時間”。也因為有了官覺類,就不能不考慮時間對人的“意味”,比如“愁人知夜長”。注入了“意味”(2)在金岳霖看來,“意味”與“意像”“特殊”“想像”相關,也與人們使用字詞的習慣相關,比如人們常常在字詞中寄托情感。關于金岳霖對“意味”的論述,參見貢華南:《徘徊于意義與意味之間——金岳霖哲學的張力與境界》,《學術月刊》2007年第8期。,“時間”也逐漸有了一絲暖意與人情味。
總之,金岳霖將“道”視作“時間”的根基與歸宿,視“時間”為道演過程中特定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特定現象,注重“時間”之“秩序”義,以個體的變動作為“時間”的實質,并以“運”與“命”作為個體“時間”的具體表現形態,表現出《論道》對“時間”問題思考的豐富面相。《知識論》由承認“官覺類”“自然”而思考“時間”與“意味”關系,推進了對“時間”問題的探討。與胡適等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為基礎喚醒人的個體時間意識不同,盡管金岳霖以個體的變動為時間的實質,但奠基于“道”的時間呈現出明顯的客觀性特征。較之朱謙之從“情感”出發領會“時間”,梁漱溟將“意欲”視為“時間”的根基等觀點,金岳霖的時間觀念具有鮮明的理性主義特征。金岳霖對時間的理解與規定既充滿邏輯精密辨析,又兼具中國情懷,豐富、深化了20世紀對“時間”問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