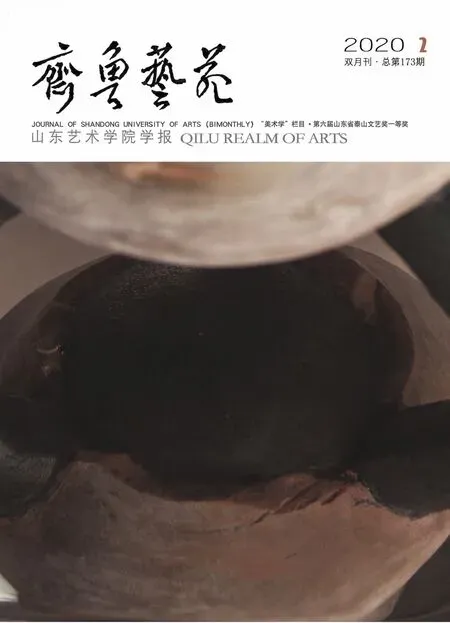設計史方法論研究中的兩種維度
李傳文
(福州外語外貿學院藝術與設計學院,福建 福州 350202)
一
設計史即設計史學,是設計學科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設計學研究中的重要一環。盡管作為一門學科的設計學的誕生不過才半個世紀,但與設計學研究相關的方法論的探討卻早在19世紀就出現了。最早論及設計方法的學者當屬德國近代機械學家、工程學家、機構運動學的創始人勒洛·若洛克斯(F.Franz Reuleaux,1829—1905)。在1875年出版的《理論運動學》一書中,勒洛不僅對機械元件的運動過程進行了系統的分析,使此書成為機械與工程學方面的一部名著,而且還從理論上第一次提出所謂“進程規劃”的模型論,對機械設計、技術方法與工程設計中一些本質性的原理加以歸納和總結,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套綜合性的機械設計的方法論。因此,勒洛闡述機械設計理論與方法的《理論運動學》被視為設計學方法論研究上的發軔之作。
雖然勒洛所論的設計僅限于機械設計領域,與我們今天所談的設計學、設計史研究方法論并非完全相同——今天的設計學與設計史研究方法論遠不限于此,乃是集機械設計、技術設計與藝術性設計方法于一體、融文史與理工等多學科屬性特征的綜合性的方法論。但是,從設計方法論研究上看,勒洛的機械設計方法論還是開啟了設計學方法論研究的先河。
設計史是設計學研究中的一門子學科。屈指數來,這門學科的出現尚不足30年的時光。因此,就目前而言,設計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尚處于借鑒相鄰與相遠學科的探索階段,遠未成體系。設計史研究方法論的成熟必須依賴設計學整體研究及其子學科——設計史學理論體系的建構,也要依賴這些學科理論與方法的互動創新。然而,在近30年的設計史方法論探討中,設計史的研究受制于傳統史學的理論、思想與方法論而裹足不前,與此同時,在吸收引入西方各類相關社會學科較為成熟的方法論體系上又存在消化不良之弊。因此,設計史研究方法論的視野必須不斷拓展,以豐富、增益設計史學方法論研究的路徑。
本文從闡釋經濟社會學理論與文化系統整體觀這兩種理論與方法入手,將其視為設計史研究中的兩個重要視角與維度,探討這兩種理論與方法介入設計史學研究的可能性、必然性及具體思路與方法。
二
經濟社會學是經濟學與社會學的交叉學科。經濟社會學采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經濟現象,其理論形態可概括為經濟行動論、社會經濟結構論、社會經濟變遷論、社會經濟戰略論等。經濟社會學認為,經濟行動是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作用的結果,它的主體是社會人而非經濟人,行動所追求的目標并非獲得最大利潤,而是滿足多層次、多消費群體的需求;經濟系統是社會系統的一個子系統,社會系統的各個子系統具有不同的社會功能,彼此間提供各種功能上的需求,由此而使社會階級、階層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經濟社會學重點研究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經濟社會變遷的個體與社會心理發展、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與發展中的協調與失調等問題。
經濟社會學有關社會經濟結構及其變遷理論、經濟指標體系與經濟發展中的協調與失調等觀點均為我們研究設計史提供了新的有益的借鑒,通過有意識地借鑒這些相關理論與方法,可以大大豐富設計史研究的具體方法,豐富設計史研究的方法論體系。
設計史是歷史。設計史研究的對象并非單一和同質的事物,即設計史不是單純針對古代設計產品的結構、形態、功能、技術與審美的研究,亦非專注于古代工藝設計家的設計風格與設計觀念的研究,而是將設計史的內在發展特征與設計史發展的外在動因相互結合起來加以系統性和整體性的研究,這樣的設計史是將再現描述的敘述方式與闡釋論述的具體方法融為一體并貫穿始終的。
因而,針對古代設計史的研究也并非就事論事,不能僅僅著力于古代設計中風格演進以至趣味轉化的歷史軌跡,而應該將古代不同時期的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結構嬗遞及其對設計的綜合性影響相互結合起來加以研究,這樣的研究并非將經濟社會結構與功能視為設計史發展的時代背景,而是將經濟社會與設計發展融為一體,把二者看作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有機結合體。在經濟社會中,設計風格發展與審美趣味轉化實際上是一個整體性的文化動力系統循環運行的結果。這個文化動力系統包括社會物質文化、精神文化與制度文化等三部分。社會經濟結構廣泛地存在于這個文化整體系統之中(如物質文化與制度文化之中),而作為這個文化體系的重要內容之一,設計、設計史及其觀念的發展、演進無不受到經濟結構、經濟動力與經濟社會變遷的深刻影響。事實上,社會結構、體制機構等均為維系經濟社會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經濟結構、經濟行為與社會結構、體制機構等經濟基礎發生變革時,在此基礎上的各類上層建筑如設計及其歷史發展便不能不同時發生轉化。這樣,設計的歷史發展在時代性、地域性與民族性諸方面均會出現重大轉折與改變。與此同時,具有一定經濟地位、體現不同社會階級(階層)意志的審美主張與旨趣亦隨之出現,并通過不同的設計風格、特征具體展現出來。因此,設計的風格演進與趣味轉化總是與經濟社會變革息息相關的,設計、生產、流通、消費與風格、趣味之間是相伴共生的,這種共生恰恰是通過經濟社會的結構、機制及其發展、改革與重組得以實現的。
20世紀下半葉,美國設計理論家維克多·巴巴納克(Victor Papanek)出版了一部引起極大爭議的著作《為真實世界而設計》(DesignfortheRealWorld,1971,1984)。在書中,巴巴納克認為,設計的最大作用并不是單純創造其商業價值,也非在產品包裝及設計風格方面與同類產品展開殊死競爭,恰恰相反,設計是一種“適當的社會變革過程中的元素”。[1]這一說法深刻地揭示出設計和經濟社會結構與政治體制發展、變革之間的復雜關聯性。從中外設計發展史看,各種設計種類與成果,如建筑、交通工具、家具、服裝、廣告、日用品、環境與室內設計等無不融入各個時代的經濟結構、改革與社會發展變遷之中,設計無時無刻不烙上時代經濟發展、社會變革的深刻印記。可以說,設計是經濟社會的構成要素之一,設計服務于經濟社會,服務于具有不同經濟基礎、經濟利益的消費階級(階層)的現實需要,而作為上層建筑的經濟結構與經濟體制往往通過其利益的代表者(設計產品的消費者)對不同時代、地域與民族的設計施以深刻長遠的影響。
上文已述,在設計史研究中,我們不能僅僅將經濟社會結構及其運作視為設計發展的時代背景,而應將二者互動融合,視為彼此相關相通的要素。運用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視角與研究方法,可以深入探討不同經濟社會結構及其轉型與設計的歷史風格、趣味轉化之間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密切聯系,可以幫助我們深入理解設計風格與審美趣味形成、發展與變革的外部誘因。
在古代漫長的手工藝設計階段,設計的社會性、經濟性屬性與特征往往對設計風格與趣味的轉化產生突出的影響。古代傳統手工藝的設計、生產、分配、流通與消費是與歷代政權的要求、經濟社會的發達程度不可分割的;作為經濟管理體制的一部分,工匠管理體制和勞動力分工決定了手工藝設計的規模、層次與水平。在經濟社會影響下,手工藝產品的生產、分配、消費與市場趨于繁榮,手工藝產品的消費、市場開始被細分和層次化;在代表不同經濟利益集團的消費階級(階層)的主導下,消費需求日益分化,審美趣味時常轉化。例如,在經濟十分發達的明清時代,漆器手工藝的設計、生產與消費就呈現出細分與層次化的明顯傾向,漆器產品因應于社會不同階級、階層的不同需求,在不同的水平上體現出設計的不同風格、品位與趣味;與此同時,消費群體、市場導向諸方面亦出現不同程度的細分化傾向。這些都與明清時代經濟形態、經濟結構的調整、更迭、變遷與重組密切相關,它們從外部為漆器設計的風格演進、趣味觀念與消費市場的形成創造了一種強大的影響力、促動力,這些外部誘因最終經由漆器設計自身的性質轉化而深刻影響了與漆器設計相關的生產、流通、消費與風格、趣味的形成和轉化。因此,我們可將漆器設計自身風格的歷史演進視為“自變量”,將來自于漆器設計外部的經濟社會的嬗遞視為促進漆器設計風格與趣味轉化的“因變量”,自變量的發展與轉化并非僅僅源于自身,它還得益于因變量這一外部要因對其不斷施加的各種影響力。
將經濟社會的嬗遞、變遷與設計風格、趣味的轉化視為相互聯系、相互促動的整體關系,這既是設計社會學理論在設計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亦是設計史研究中“內心觀”與“外向觀”理論的直接體現。所謂設計史的“內心觀”,一方面是指對設計本體事物——設計產品、設計家、設計思潮、設計風格、設計流派等加以分門別類的研究,另一方面還包括對設計、生產、流通、消費、市場諸事象進行關系研究,這是對設計本體多元發展的自變量的研究;所謂設計史的“外向觀”,指的是對誘發設計諸事象的外在要素——經濟結構、經濟行為、經濟變遷和消費群體及其利益主張等詳加考辨,將這些外因視為通過自變量促使設計本體發生本質改變的因變量,這是從設計本體之外對設計史的性質改變與現實轉化發生影響的諸誘因加以深刻的闡釋。
在古代,代表著不同經濟集團的政治力量具有各不相同的審美需求,他們從政治權利、經濟要求、思想觀念與審美功能諸方面對設計提出了各種具體要求,反映出政治意識形態與思想觀念對設計的主導性與控制力;與此同時,經濟社會發展為手工藝設計確立了正常發展的保障體制、規章和其他保護性措施,從而使得以上各種內因與外因的互動聯系變得愈益緊密。因此,在古代經濟社會里,由于經濟社會的推動,設計與市場、消費的聯系變得更加密切,由此推進設計創新和消費發展,促使不同時期的設計風格發生演進,審美趣味發生轉化。另一方面,經濟社會及其結構的穩定化和持續發展又使得設計傳播、接受、使用與反饋變得更加頻繁,經濟結構、經濟行為及其歷史變遷與設計風格的歷史演進、審美趣味的轉化之間不斷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三
從經濟社會學的視域,為我們洞悉經濟結構、社會體制與設計風格、趣味轉化之間深刻內在的關系打開了一扇明窗,加深了我們對設計史發展與變革的全面認識。不過,在這一方法論之外,我們還需要另一個描述、闡釋與評價設計史的理論視角,這個角度便是從文化體系整體觀的視角來辯證地看待造物設計的歷史發展與風格演進。這個視角要求我們從設計與文化的關系以及設計文化自身的本質、內涵等比較研究的視角來看待設計史,分析設計在文化中的地位,闡釋設計史的文化功用與價值,研究設計史內含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與制度文化價值。
文化是什么?數十年來,國際間諸多學者為“文化”所下的定義不下一百多種,從不同的角度為文化一詞作出了精要的概括。以下不妨舉出三種較有代表性的文化定義:
①法國后現代解構主義哲學家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指出:“文化存在于一個民族與世界和與它自身的所有關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為有意義的東西被接受的存在。”[2](P104)這是從哲學的高度闡釋“文化”的內涵。
②被譽為“文化科學奠基人”的英國近代人類學家愛德華·伯內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aylor,1832—1917)在《原始文化》(PrimitiveCulture,1871)一書中對“文化”一詞下了這樣一個內涵豐富而影響深遠的定義:“從最為廣泛的民族志的意義上看,文化或文明是一個綜合性體系。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學到的其他能力和習慣。”[3](P9-10)泰勒的文化定義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影響亦最大。這個定義不僅使我們明白了文化的內涵是寬泛的,而且還是目前學界將文化界定為物質文化、精神文化與制度文化這三大形態的基本依據。
③美國當代人類學家懷特(Leslie Alvin White, 1900—1975)立足于進化理論,將文化視為一個整體全面的動態系統。他認為,文化體系是由技術體系、社會體系與觀念體系三部分構成的。其中,技術體系決定社會體系,也決定觀念體系,由藝術、哲學等構成的觀念體系則以社會體系為媒介。[4](P76)在懷特看來,處于文化表層的技術體系、處于文化中間的社會體系和處于文化深層的觀念體系是構成文化整體系統密不可分的三大有機組成部分。懷特的定義與泰勒有相同之處,但是,在這里,懷特極為重視技術體系在整個文化體系中的決定性作用,他認為文化進化的程度與人類獲取生存、發展所需要的能源的技術水平(程度)密切相關,技術體系的發達與豐富決定了文化整體的發達與豐富。
以上三種關于文化的定義,從不同而又近似的視角為我們剖析了人類文化的整體性、多樣性特質,為我們深入闡述“設計”這一獨特的文化形態即設計文化形態確立了指針,帶來了新的啟發。
設計是文化系統中的一種獨特形態、一個種類;同時,文化具有層次性。設計亦是如此,設計是由設計的物質文化層(或稱器物文化層)、觀念文化層(或稱精神文化層)與制度文化層等三個有機部分組成的,這些不同的文化層在設計中居于不同的地位和水平,因此,在設計的風格發展與趣味轉化中也起著各不相同的作用,具有不同的社會地位與影響。在設計史發展中,觀念文化層往往居于核心地位,它首先來自于設計家的設計思想以及社會思潮的影響,亦來自于不同經濟社會中占據不同地位的社會意識主體的觀念思想,如社會各階級、階層的不同設計思想、審美趣味,并對設計施以不同的壓力,造成各種不同的影響。附著于設計內核的觀念文化層是“禮藏于器”的,是無形的,它是一種隱于設計文化深層的思想意識形態,但卻是一種最終要顯現于設計實體的觀念性的存在。
設計的物質文化層即器物文化層,它以造物的物質媒介為基礎。設計產品必須要以物質實體的形式服務于經濟社會的實用性需求,設計產品的物質形態——產品的造型、結構、色彩、肌理等設計都是產品物化的必然結果,也是對物質材料進行直接或間接選擇的結果。經濟社會的物質需求首先要求以物化的設計實物為載體,這是設計精神表達的基本前提。在人類漫長的設計長河中出現過無數獨特的物質形態創造,這些獨具特色的產品設計蘊含著各種特殊的精神象征內涵和深刻寓意,成為處于不同經濟地位的消費階層尋求精神慰藉的物質依托和情感力量。因此,在設計史中,隨處可見集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于一體的設計創造。
最后,在這種集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于一體的設計創造中,制度保障不可或缺。設計的物質與精神文化創造要得以順利進行,保障設計順利展開的制度文化就顯得十分重要。對于設計史而言,其制度文化層包含歷代社會中由統治者制定的造物規章、條文(這往往具有切實的法律效應),以及設計、生產、流通、銷售與使用過程中應依憑的行業規則、制度(這往往是手工藝者自覺遵循的)等。若按照美國當代人類學家懷特的觀點,這種制度文化層應屬于他所謂的“技術體系”,它主宰著設計中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創造。因此,我們不可忽視制度文化層在設計文化總體創造中的獨特地位及重要影響。
在設計史的研究中,不僅應將設計視為一種文化層次性的存在,還應將設計的物質文化層、精神文化層與制度文化層相互融合,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的有機整體,從整體觀上將三者看作相互融合、相互影響和相互推進的有機組成部分,這體現出設計文化體系的一種整體觀念。在文化體系整體觀的指導下,將設計的風格發展與審美趣味的轉化視為一種文化史的發展,一種文化體系整體觀影響下的產物,這樣,我們才能更為清晰地理清和闡明在經濟社會結構與體制運行的條件下,作為文化整體的一部分,設計風格、趣味轉化是如何不斷發展與逐漸演進的。
設計是文化的一種物化形態與精神表達,是精神文化、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合力
創造的產物,是文化的有機綜合體;設計展現出文化的多元性、復雜性,具有極大的包容性,這是設計創造的不竭源泉。將設計視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的文化系統,有助于我們準確認識與理解設計發展史的內在機制、原理、動因與規律,在經濟社會學理論之外又拓寬了設計史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四
設計史研究不僅在于對設計史實的客觀描述,還在于對設計史實的主觀闡釋與科學評價,設計的歷史研究是集具體描述、客觀闡釋與科學評價于一體的研究。經濟社會學理論與文化整體觀視野是我們進行設計史研究的兩個重要維度。從經濟社會學與設計史的融合研究中,我們可探尋到經濟結構、經濟行為與社會變遷在設計歷史發展中的深刻印記;從文化整體觀中,我們增進了對設計文化創造的多樣性、復雜性的深刻認識。無論是經濟社會學理論,還是文化整體觀都是我們洞悉設計風格演進和審美趣味轉化的明鏡,從而加深我們對設計史發展的深刻理解與全面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