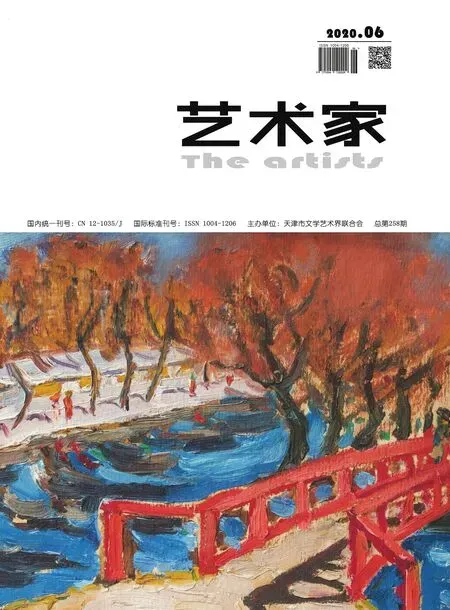淺析竹子作為文人畫題材背后的一些品味
□祝雨欣 南京師范大學
文人畫總有著濃郁的超現實意味和理想的深意,文人們通常用詩意的眼光,取材于梅蘭竹菊、山水樹石等,加之以獨特的筆墨技法及構造,附之以飽含文人精神的情感,形成了中國文化獨有的繪畫審美趣味。古往今來,竹子作為文人畫題材之一,在藝術發展的進程中始終熠熠生輝,其經久不衰的原因還在于竹子背后的中國文化意象和內在精神。
一、“竹”本物
竹子本身屬于中國常見的喬本科植物之一,卻有著區別于其他常見樹木的外表,它的主干筆直挺立,枝細葉密,綠意盎然,從葉常常具有多種形態,適合表現富有變化的筆墨形式。自古以來,它還常常作為樂器、書寫材料等各種風雅之物的原料,竹子的歷史與藝術息息相關。
除表象之外,中國哲學兩千多年的發展賦予了竹子內在精神,深深影響著文人對竹子情有獨鐘,也表明著中華古典傳統的一些品味。范景中先生花了七年時間嘔心瀝血地寫了《中華竹韻》,足以體現中國的竹文化,這些竹文化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舉個例子,將“一花一世界,一樹一菩提”的“花”和“樹”翻譯成“flower”和“tree”,都是司空見慣的花和樹,卻是西方主要的分析哲學思維影響下西方人所無法理解的禪機和妙趣。“bamboo”也是常見的竹,而這個單詞是源于竹竿燃燒的聲音,但中國的“竹”字就不一樣了,《說文解字》解釋為:“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這部解析形字釋義字典同時也收有一百五十多竹部的單字,引導著人們從多方面發散思維來研究竹子。
二、“竹”比德
陶淵明愛菊、周敦頤愛蓮、白居易愛竹……古之達人,皆有所嗜,嗜好的東西雖不同,卻都有相似之處,而唯有竹子,具有最豐富的文化意象和內在精神。竹子能提高一個人的尊嚴,能如神藥一般醫治“俗”這個惡病,所以愛竹者,通常都是志氣高潔、品德中正之士。白居易的《養竹記》和劉巖夫《植竹記》一直一文,異曲同工,雙雙證實了竹子“比德”的觀念。《養竹記》的起始部分提到“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不拔者……”竹子原木剛勁挺拔,即使是大風大雪也堅固不催,這種“固”即比喻君子的“剛”。然而竹子也是剛柔相濟的,它的枝葉是細密的,如《植竹記》所言:“綠葉凄凄,翠筠浮浮,柔也。”竹性直,君子見竹思立身。竹子的心又是空的,空體現了道,體現了虛懷若谷的高尚情操。竹子一節一節的,好比君子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克服重重的困難,砥礪前行,不斷上升自己的高度。竹子又四時一貫,榮衰不殊,就像擁有著永恒的價值一樣。簡言之,竹子比德,比在剛、柔、衷、義、謙、恒、樂賢和進德。
三、“竹”的永恒價值
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提出“自然者為上品之上”的繪畫品評等級,追求自然的藝術無疑在崇高的意境之中,唐代的張璪也提出“外師造化”的造化即要模范自然。因此,自然中的竹子造就與粘幀、礬絹、位置、描墨、承染、設色、龍套等項目有關的討論,是繪畫史所謂的:但即使在表演藝術史上,形象作為一種風格因素對形象的影響,也遠比直接從自然觀察中得到的影響重要得多(Aber auch in der geschichte der darstellenden Kunt ist die Wirkung von Bild auf Bild als Stilfaktor viel wichtiger als das,was unmittelbar aus der Naturbeobachtung kommt),也就是范景中先生翻譯成的:繪畫得益于繪畫的,比它得益于觀察自然的還多。
當代一些人認為“君子于竹比得德”之類的套語是陳詞濫調,這種想法是極為欠妥的。自然下的竹子題材不僅寓意著精神品質,還從繪畫的技法上對繪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斷地推進繪畫藝術的發展。在準備畫竹時,不知多少文人為此操練上幾十年的筆墨技法,潛心鉆研畫竹理論,不慕名利、又耐得住寂寞。多少個漆黑的夜晚,在風吹颯颯的竹林和寂靜清透的竹屋下,挑燈暢讀,唯有古畫典籍、筆墨紙硯相伴。這些歷史積淀下的珍寶,更需要我們銘記在心,它們是中國古典文化精華的璇璣碎錦,隨時都會大放光彩。
總之,就像尼采思索寫實主義時所說,畫家對景作畫,除非大自然可以融入所學詞匯中去,否則任何東西都成不了創作的題材。文人畫取材于竹,用竹子比喻美德,并不是從竹子中看出竹子的優美,而是把竹子之美強加給竹子,把大自然變成生活藝術的宗教,是神圣的。然而,我們必須深知文人畫題材背后的文化意象和內在精神,不能孤芳自賞,我們必須在世界文化差異大背景下站在更高的藝術頂峰去看待文人畫,去實現中國畫藝術在現實世界中的偉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