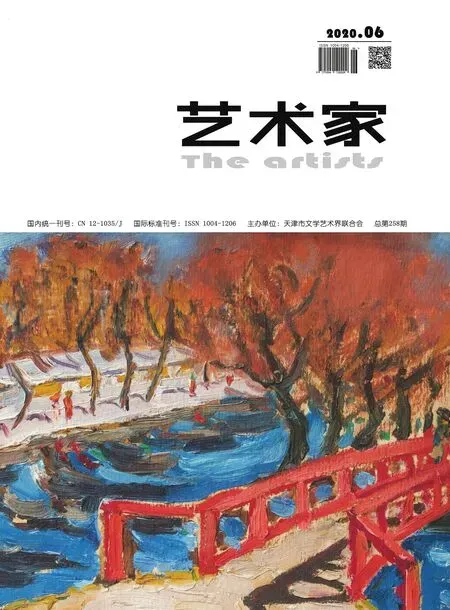創作與沉思
——我的藝術觀
□陳禹丞 魯迅美術學院
本文將以筆者的藝術視角,分三個部分來解讀與闡述藝術創作給筆者帶來的感悟及筆者對藝術觀的理解。第一部分大致為筆者從走上藝術工作道路至今的7年時間里,對藝術的理解與思考。第二部分是通過影視作品中的藝術語言形式來分享一些筆者的感悟。第三部分是通過筆者的藝術作品,來梳理筆者的藝術創作與藝術觀成長的過程。
一、筆者的藝術觀概述
筆者出生在一個飛速發展與變革的時代,筆者所經歷的、看到的,也都在這樣的大環境中,這或許推動了筆者對新事物的接受速度與觀念不斷隨著時代演變而發展。盡管筆者身在學院,但不得不正視當代藝術的劇烈變化,在當代語境下的創作與思考中,筆者的藝術觀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筆者不認為這是一種絕對成熟的征兆,恰恰相反,筆者始終覺得藝術家在不斷地自我否定與觀念改革中成長,這件事本身就是藝術。面對紛繁復雜的藝術現象,應該具有什么樣的藝術觀,筆者現有的藝術觀是否可以在此語境下扎根發芽,是否可以通過普遍規律尋找到一種屬于筆者的符號,是筆者這幾年來不斷思考的問題。在當代大環境下,藝術形式繁雜無章,每個人都在用自己感興趣的或者嚴格意義上是“合適的”形式來體現自身思考,我們也許很難去絕對否定哪一件藝術品或者藝術家是“錯的”抑或是“不好的”。這件事同樣也是之前困惑筆者許久的。但通過這幾年不斷地去實踐,去辯證,去思考,筆者具備了一種自我評判的能力。筆者認為,這種東西與其說是藝術觀,不如說是能力更為恰當。因為它就好像筆者的世界觀一樣注入筆者的身體中。它是筆者的力量,這種力量絕不是瞬間形成的。同樣地,它也可以被改變,但改變后的殘留物也同樣存在,并與改變后的觀念相混淆,形成一股新的力量。這種循環對于藝術來說大概是再美好不過的事情了吧。筆者喜歡這種觀念的變化與形式的否定后萌生出的新芽。在這個過程中筆者不斷地進行著思考與蛻變。
二、從電影中引發的對藝術觀的思考
與筆者喜好有關的是,影視作品在筆者不斷變化的藝術觀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筆者喜歡感受每一部電影、影像帶給自己的沖擊與質疑。而說到藝術觀,就不得不提及《絕美之城》這部電影。它本身的手法就是“非常規的”“現代的”、由多個依托主人公聯系起來的小故事組合而成。換言之,盡管電影中有諸多像塔利亞概念派和光怪陸離的藝術家聚會這種對于現代藝術極其厭惡的元素,我們也不能單單將這部電影所流露出來的藝術觀點簡單地歸納為傳統的或者保守的。其中包含的藝術觀是非常值得人們去思考的。筆者認為,這類電影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在于其中所涵蓋的藝術觀中有許多因素與人們普遍的藝術觀相似,卻又能在這之上為人們帶來新的靈感。這樣的魅力是難以抵擋的。與《絕美之城》不同,電影中的另一種“塑造新世界”的手段不得不提。當代有許多藝術家在完成獨立且深入的思考后會試圖主動構建一個由自己創造出來的新世界,并注入符合其環境的玩法與觀念,如青年藝術家陸揚構建的“腦髓天國”一樣,電影《狗鎮》的新世界則更基于生活且偏向于討論人性,片中導演大膽地將一個靠山的小鎮這樣一個真實的場景抽象為一個舞臺劇劇場般的拍攝地。甚至連每家每戶的房屋都是用地上的白線來簡單表示,這大概就是導演拉斯·馮·提爾的藝術觀。他的這種簡化恰恰為他想訴說的人性提供了更直接的舞臺,在當代藝術中這像一種形式,更像一種觀念。
三、筆者的藝術創作
筆者的藝術創作在短短幾年內經歷了從平面到空間,從靜態到動態,從繪畫到新媒體的轉變,當然這些都是形式上發生的變化。隨著時代的發展,環境的過快變化導致筆者的觀念不斷轉變,隨之而來的還有材料與語言的轉變,這種過快的轉變與多樣性的實驗對筆者的影響注定是多面的。
本科畢業后,“去人性化”思維在筆者的腦海中漸漸產生。經濟學和社會學都建構過理性人,主要是一種理性的、符合模型預期的行為方式。當然,建模和現實是兩碼事。不過,技術和社會制度的前進方式,是為這種理性化行為提供便利的。理性的行為方式,是否等同于自我約束?自我約束,是否對人類本能抱有敵意?如果是這樣,人類是否在向“去人類化”“去生物性”的方向演進?再后來,筆者追求采用更加直接、簡化的形式去表達。筆者嘗試組織了多次行為藝術表演并用影像照片的形式進行記錄,每一次行為表演結束之后作為表演者的筆者都可以感受到“行動”的魅力,并對物質動作背后意義進行更深入的思考。
隨著時代的發展,筆者也對創作進行著新的嘗試,還用新媒體工具創作了多個媒體交互作品與項目計劃,并結合著空間、時間,與體驗者自身,來尋找更多的話題,從一個點出發創造更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