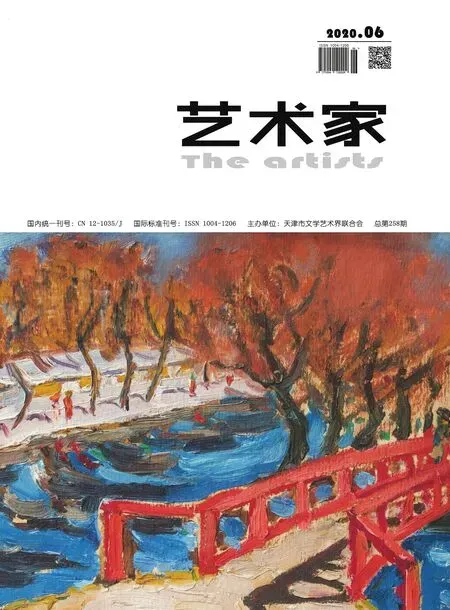淺談趙孟頫書法與書法觀
□于嘉敏 云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元代書法發展離不開集藝術之大成者趙孟頫在書壇的領袖人物。趙孟頫少年喪父,宋朝遺逸,出仕元朝,歷宋元之變,仕隱兩兼,元受重用。人格書法飽受士大夫“失節”爭議。趙孟頫兼攻六體,極力推崇魏晉古法,是元代書壇托古改制、借古開今的領袖。
一、書法
(一)生平簡介
趙孟頫生于南宋寶祐二年,是宋太祖趙匡胤第十一世孫,卒于元英宗至治二年,享年六十八歲。他雖是皇族王孫,但生不逢時。趙孟頫十二歲喪父,二十三歲宋朝滅亡,后隱于故里,苦研學問,沉于詩文書畫中。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受元世祖忽必烈派遣“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趙孟頫未像四年前拒絕出仕,而是邁出北上大都晉見元帝的重要一步。元世祖大加贊賞其才貌,一再升遷,元二十七年其任從四品集賢直學士。元二十九年出任濟南路總管府事。在濟南路總管任上,元貞元年因元世祖去世,成宗需修《世祖實錄》,趙孟頫被召回京城。但此時元廷內部矛盾重重,有自知之明的趙孟頫便借病乞歸。至大三年,趙孟頫的命運發生了變化。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非常器重他。延祐三年,趙孟頫官居一品,名滿天下。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別署水精宮道人、鷗泊。浙江吳興人,又稱趙吳興。歷官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學士,封榮祿大夫,又稱趙學士、趙承旨、趙集賢、趙榮祿。卒后受追封魏國公,謚文敏,又稱趙魏國、趙文敏。
(二)歷史評價
趙孟頫是元代書畫研究的中心人物,其主導新一代書風,是元書壇的領袖。就書畫論,趙孟頫對當時及后世影響可謂無有出其右者,其藝術成就包括書法、繪畫、篆刻、詩歌文學、書畫文物鑒定及音樂各個方面。然而,趙孟頫以宋室身份仕元,觸犯綱常倫理大忌。在藝術評判與封建倫理雙重標準下,趙孟頫招致眾多非議。縱觀歷史,人們對其褒貶不一,評判眾多,現舉例如下:
(1)元仁宗:“帝王苗裔,一也;狀貌昳麗,二也;博學多聞知,三也;操履純正,四也;文詞高古,五也;書畫絕倫,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詣玄微,七也。”
(2)項穆:“孟頫之書,溫潤閑雅,似接右軍正脈之傳。妍媚纖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之祿也。”
(3)傅山:“予極不喜趙子昂,薄其人遂惡其書。” “潤秀圓轉,尚屬正脈,蓋自《蘭亭》內稍變而至此。”
不難看出,歷史上對趙孟頫的評價爭議頗多,尤其是對于人品與書品。趙孟頫的品性是頗具大家風度的,為人持重知謙退,不染“文人相輕”舊習,也頗有不藏人善的胸懷。其失節之疵,生前少有人提及,身后則不然。不僅人格遭鄙視,更連累其書法藝術。但是,歷史功過自有歷史評判,書法藝術的優劣應有其獨立客觀標準,隨著時代的進步,以非藝術因素作為品評書法家藝術成就高低的方式是不科學的。
(三)書法藝術
趙孟頫推崇魏晉古法,用二王法寫真、行、草書,兼工篆、隸、章草這類古體,尤善楷書與行草,是歷史上少見的全能藝人。其書法繼承傳統,用筆清晰,易懂易循,風格典雅和美。在楷書用筆中摻入行書筆法,點畫華滋遒勁,結體寬綽圓潤,橫直相安,布白方正謹嚴。趙孟頫初學遍涉諸體,后王羲之、趙構、智永、李邕對其的影響巨大。趙孟頫最大的功績是使魏晉典雅書風在元朝全面復興并成為典范。中庸和美的趙體對文徵明、董其昌等明清后世書法的影響頗為深遠。
二、書法觀
趙孟頫不僅是元代書壇托古改制、借古開今的領袖,從其出山開始更扭轉了南宋一百多年書法的頹勢。如虞集所指:“自吳興趙公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所以,趙孟頫書法觀的重要內容即對魏晉古法的推崇,使元代書法重新確立以王羲之為偶像的書法傳統。其書學思想主要反映在其眾多書法題跋中。最重要者當屬《蘭亭十三跋》第七跋云:“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趙孟頫雖力推王羲之,但也有其個人心得,他認為筆法要守古,結字則可質可妍、亦晉亦唐變化。“用筆”是千古不能失去的基本規律,是核心。結字也當以古來標準為基準,可“因時相傳”,但以“古”為“傳”。筆法為體,結字為用,古法將其統一于一個審美理想概念,士大夫文人中的復古思潮。
趙孟頫在書史與文化史的功績是書法與歷史發展綜合條件的成果,其在當時書風下找到了個人最適宜的表達方式。“筆墨當隨時代”,今人對古法的認知與元代對古法的推崇也早已不同,肯定成就與取法選擇并非畫等號,今人學書面對浩瀚書史更要保持清醒與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