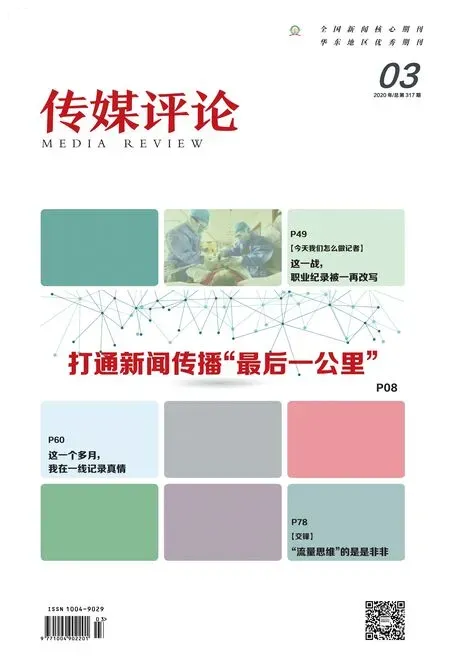社會化媒體時代輿論博弈的技術邏輯
文_岳 璐 羅郵息
當前,社會輿論場內各種話語的激烈博弈已然成為新常態。各種網絡輿論以原生態、多元化分權主流話語,主流話語的輿論引導已難以維持一呼百應的傳統優勢;更為復雜的是,利益格局重新調整,社會結構劇烈分化亦導致民間輿論內部的分裂與對立。輿論博弈實質上反映了多元利益主體的權力角力與思想交鋒,而社會化媒體憑借其強大的交流與互動優勢,“絕不僅僅是一種傳播手段,它還是我們討論、辯論、形成共識”[1]的平臺,不僅為個體狂歡提供了盡情宣泄的舞臺,更重要的是作為輿論博弈的一種無法回避且威力巨大的全新技術邏輯,深刻影響著輿論博弈的具體過程與整體狀況。
作為輿論博弈空間的信息化場景
社會化媒體的蓬勃發展帶來了全新的場景概念,互聯網徹底拋棄了場景是具體的物質地點、空間位置的觀念,取而代之的是完全不同以往的信息場景。新的場景產生了新行為,新行為產生新意義,新意義又成為新社會秩序的積淀,這是一個動態循環豐富前進的過程[2]。在這之中,社會輿論的形成、傳播、沖突與交融也隨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一方面,社會化媒體所構筑的信息場景使得交流的物理屏障消失了,觀點與意見的自由市場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形成。在這個公共空間中,公眾輿論的形成和傳播、辯論和沖突找到了棲身之所。當下,大數據、移動設備、社交媒體、傳感器、定位系統這五種被稱為“場景五力”的技術在現實生活中逐步實現,漸漸抹去了人們信息交流的物理屏障從而建立起一個全新的信息化場景,這個場景中每一個人都可以是內容的生產者和交換者,而社會化媒體就是這個生產和交換的平臺。當成千上萬的公共議題的評論、觀點和意見在各類社會化媒體平臺上匯聚,一定數量的集體性意見形成了網絡輿論,不同意見的網絡輿論亦在此呼應、交鋒,這一信息化場景就成為了公眾聚會的場所,即一定意義上的公共領域,為輿論的形成與博弈提供了空間。
另一方面,信息場景中雖然交流的物理屏障消失了,可取而代之的是信息的隔離墻。當下社會輿論的博弈方大部分處于非合作的狀態,這與社會化媒體的技術特性衍生的交流的無奈不無關系。
社會化媒體的一大特征就是用戶的參與性。社會化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以是內容的發布者,用戶也可以隨意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內容。而且在大數據算法推薦等因素的影響下,平臺可以了解用戶偏好,過濾異質信息,使用戶置身于一個自己興趣偏好的“信息繭房”之中,造成一種信息隔離狀態。因此,社會化媒體能使用戶獲得更多的信息但并不能保證用戶會增加參與公共討論的意愿。同時,在成千上萬的用戶分享中,網絡輿論像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但每一位用戶的知識水平、文化背景參差不齊。這意味著,一旦導致輿論形成的信息是失實的,在沒有有效辟謠的情況下,網絡輿論很有可能偏離軌道,走向失序,特別是在公共事件中,輿論博弈難以達成合作狀態。
互動性也是社會化媒體的顯著特征之一。但社會輿論場中博弈參與者尤其是官方與網民的互動效果仍然有待提升。輿論的博弈有相當一部分情況都是官方首先觸發,不當的舉措導致了輿論博弈的非合作狀態,堵塞了雙方之間溝通的橋梁,建立起了信息的隔離墻。
此外,社會化媒體通過信息流激發公眾的情感,同時也極易將宣泄的情緒迅速傳往每個角落。公共事件進入網絡傳播領域后,網民可以隨意表達自己的情感訴求,憤怒、戲謔、不滿等負面情緒更是有極大的感染力,充斥著整個輿論空間。
作為輿論博弈資源的社會網絡結構
在社會化媒體中,傳播不再和傳統的大眾傳媒一般自上而下、由點到面,而是每一個個體都成為一個小的節點,互相交織、連結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社會網絡。作為社會化媒體的傳播結構,社會網絡對于信息的傳播、意見的自由流通產生著重大的影響,是社會輿論博弈天平中的重要砝碼。
首先,無數的個體節點匯聚編織成了這張巨大的社會網絡,為輿論博弈提供了大量的人群資源。目前,中國擁有將近9億網民,每一位網民都在建構著自己的社會網絡。在個體節點的社會網絡里,用戶可以與自身建立關聯的對象進行溝通、交流與互動,這些網絡互相交織形成了蔓延到社會每個角落的一張大網。網絡輿論博弈是在社會化媒體為主構成的網絡輿論場中各種話語之間的博弈,而社會網絡結構正為博弈中決策的主體提供了資源。在一些大型的突發公共事件中,社會網絡迅速動員大量人員的優勢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湖北省紅十字會在處理捐贈物品時出現疑云,且無及時的正面回應,引發強烈不滿,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賬號“俠客島”隨即發微博要求相關方出面回應,這條微博短時間內就得到20多萬的轉發量、近50萬的點贊。公眾通過點贊、轉發、評論公開表達自己的態度與觀點,成為了輿論博弈中的重要一方。
其次,社會網絡結構在信息資源的傳播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社會網絡結構中,每時每刻都有個體節點在生產信息,公開、自由地發表觀點與意見,這些節點之間交流、互動又會產生新的信息內容,沿著人際網絡路徑不斷擴散,填充著社會網絡中的信息資源。而且,社會化媒體平臺會為用戶進行排序與整理熱門信息。例如微博的熱搜榜,是根據用戶的關注熱度進行排行的實時熱點,每分鐘更新一次。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社會化媒體為輿論博弈提供了豐富的信息資源,但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成為輿論博弈的資源。從總體情況來看,娛樂類信息在信息資源中占比較大,公共信息的篇幅還是較少。這與網民的自身素質、個人偏好、利益相關度等因素有關,也是因為在各節點之間的連接中,一些輕松、娛樂性的話題更容易拉近與其他成員之間的距離。另外,由社會結構轉型引發的社會焦慮,使人們在社會網絡之中想要逃避現實,一部分網民往往“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甚至即使是關涉自身利益,也想采用“搭便車”的博弈策略,不愿發表自身觀點。
再者就是社會網絡中的關鍵傳播節點——意見領袖。借助于移動互聯網技術,傳統的意見領袖的功能更加突出,常常被稱為社會網絡的話語權力中心,處于話語權力的頂層,直接影響信息的流向和輿論的走向。在社會網絡結構中,意見領袖更像是一個過濾器和調節閥,在輿論博弈資源的篩選上起著一個網絡信息把關人的作用。當然,意見領袖對于網絡信息傳播的影響并不總是正面的,在輿論博弈中,由于邏輯知識和結構層面的欠缺,網民很有可能就被某些意見領袖帶入情緒的陷阱,從而走向非理性的輿論博弈,致使輿論博弈偏離了實現合作、統一認知的初衷。與此同時,意見領袖所發布的內容有可能是虛假信息,在網絡環境的助推下,這些信息由中心向四面八方輻射,則會使輿論博弈陷入一種失序的狀態。
作為輿論博弈機會的自組織機制
事物從無序走向有序或從較低級有序到較高級有序的進化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不受外界干預,控制參量變化,通過子系統間的合作實現有序化,這種方式稱作“自組織”;另一種方式則是“被組織”或“他組織”,即在外界指令下被動地從無序走向有序[3]。社會化媒體平臺的大多數傳播行為起源于公眾無意識的行為,但是隨著信息的流動人群會逐漸聚集,傳播活動逐漸顯現出有序的趨勢。而社會輿論也正是通過自組織機制使個體意見從混沌走向分類、集中,為輿論博弈做好了鋪墊與準備。不過,自組織機制也并非在所有時候都能發揮有效作用,自組織機制最后是產生“群體智慧”還是“群體迷失”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無論如何,社會化媒體中的自組織機制為輿論博弈準備了各種“機會”是毋庸置疑的。
一是自組織強大的聚合性為輿論博弈提供機會。當一個有價值的公共話題出現,自組織內能迅速集結內部力量,將其聚合起來,使輿論的形成與博弈成為可能。當自組織內部開始集聚時,會過濾掉一些干擾信息,突出焦點內容,產生正反饋效應,這也使得輿論博弈更加具有針對性。事實上,一些聚合之后的自組織話語權力不斷凝聚、增強,在整個輿論格局中所占比重也越來越大。
二是自組織內部的分工與合作,推動內部的自我修正與自我完善,有可能構建有序的輿情生態。一般而言,不管是常態性的自組織,還是突發性的自組織,成員之間會依據各自特點、角色分化等自然形成某種分工,包括信息與知識組、意見組、行動組等,各系統之間協作運行,從而實現傳播活動的有序化。一旦自組織內部的子系統按照某種規則合作,對于輿論的形成和助推是非常有效的,同時一旦輿論博弈開始,自組織也能更快地采取相應策略,從而占據博弈的先機。
然而,在包容開放的網絡環境中,自組織機制也有產生“群體迷失”的可能。在自組織機制作用下,網絡群體匯聚,在群體心理的作用下,個體理性可能會削弱,集體性盲從可能由此產生,非理性的輿論博弈往往來源于此。
結語
從技術邏輯角度入手對社會化媒體時代的輿論博弈進行探析與研究,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在社會化媒體的推動下輿論博弈產生新情況與新變化的原因,在社會化媒體輿情的多元互動演變中對輿論博弈有一個更加全面、深刻的把握。當越來越多的個體在微博、微信、知乎、B站等社會化媒體平臺上發出聲音、表達意見、發起動員、形成輿論,當熱點事件中網絡輿論與其他話語之間的互動與沖突越來越頻繁,就會極大地影響事件的進程。顯然,不僅僅只是技術的交流手段的社會化媒體在輿論形成、博弈的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基于工具特性的社會化媒體,對于輿論博弈的影響究竟如何,還需要長時間、多方面審慎的探討,畢竟在輿論博弈之中,影響因素從來都不是單一的。
注釋
[1]保羅·萊文森.數字麥克盧漢——信息化新紀元指南[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104.
[2]麻小影.互聯網時代地域的“存在”與“消失”——從梅羅維茨的媒介情境理論出發[J].新媒體研究,2018(4):115.
[3]楊貴華.自組織與社區共同體的自組織機制[J].東南學術,2007(0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