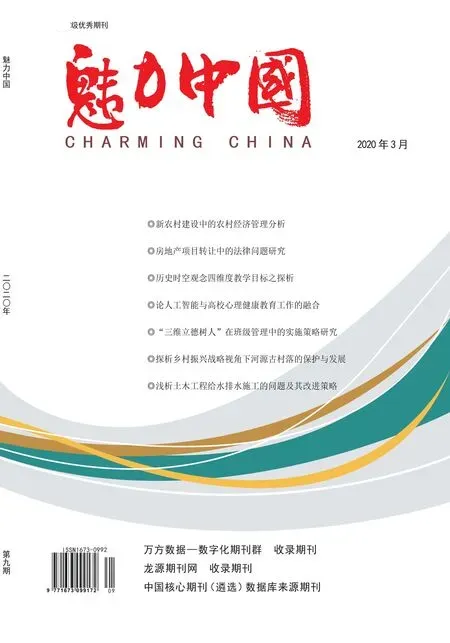醫療懲罰性賠償制度研究
李慧晶
(中國政法大學,北京 100000)
從本質上來講,醫療行為屬于醫療服務,帶有消費特點。但在服務獲取的過程中,相較于醫院和醫生,患者處于弱勢地位,容易受到利益侵害。在醫患糾紛頻發的時代,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對惡意侵權行為進行抑制,確保患者得到充分補償,則有助于維持社會和諧發展。
一、醫療懲罰性賠償制度建立意義
醫療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建立,是基于侵權責任法理論,能夠對醫療侵權行為發揮預防、懲戒作用,確保由此引發的損害能夠得到有效填補。在輕微醫療侵權行為發生后,通過民事性賠償就能保證受害人得到完全救濟。但一旦發生嚴重醫療侵權損害,按照現行規定也只是根據地區工作收入等情況確定傷殘或死亡賠償金額,忽略了受害人實際在經濟、精神等方面受到的各種損害。實際在醫患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等的問題,導致弱勢一方難以通過合法途徑獲得應得賠償。實施懲罰性賠償,要求對受害人受到的損害進行有效消彌,不僅能夠提高醫護人員責任意識,也能展現立法的人文關懷。通過經濟懲罰,使侵權關系中的責任義務得到平衡,也能使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得到有效維護,繼而完成和諧醫療環境的營造,減少醫患糾紛的產生。
二、醫療懲罰性賠償制度建立方法
(一)明確制度適用范圍
結合制度建立目標可知,實施懲罰性賠償是為了對惡性醫療侵權行為進行預防、懲戒,同時彌補受害人損失。在制度適用方面,應主要包含三種情況。第一,醫療機構或人員事前明確知曉服務行為有可能給患者帶來嚴重傷害;第二,醫療機構或人員違背履行積極救治和審慎治療的義務,導致患者承受嚴重損害;第三,醫療機構或人員因疏忽造成重大過失,造成患者發生嚴重損害[1]。對上述情況展開分析可以發現,患者在就醫后之所以會承受巨大損失,與醫療機構或人員主觀上存在惡意、故意或存在重大過失有因果關。如為節省開支使用資質不合格廠家藥品和器械、人員在患者救治中相互推諉、人員行醫時違反操作規范等情況的發生,都與主觀問題有關。醫療工作開展對人員和機構提出了較高責任要求,忽略這一要求意味著其蔑視患者獲取救助的權利,因此發生重大過失等同于主觀惡意,需要得到嚴懲。此外,發生上述狀況會直接造成患者承擔嚴重損害后果,將成為事實懲罰性賠償的事實基礎。
(二)合理確定賠償金額
事實懲罰性賠償,需要解決賠償金額多少的問題。賠償需要發揮預防惡性侵權行為的作用,同時應保證受害人合法權益得到維護,所以還應從侵權方義務、主觀惡意性、受損不可恢復三方面進行考量。如果一味提高賠償金額,反而會引起醫護人員恐懼過失發生,不利于醫護人員采取積極措施預防損害發生,因此金額設定應保證可能發生侵權一方積極履行義務。與此同時,主觀故意和重大過失應區分開來,體現法律公正性。從受損利益恢復角度來看,通常輕傷需要與重傷殘疾或死亡區分成相對不可恢復和絕對不可恢復兩種,應執行不同額定賠償。總體來看,賠償金額確定問題較為復雜,但還應根據實際損失、主觀惡意程度進行確認。在損失確定上,需要將直接證據與合理推斷結合在一起,確定患者將承受的直接和間接損失,并根據醫療機構和人員支付能力適當提高賠償金額,確保制度得到有效執行。從主觀惡意程度分析角度來看,程度越高賠償數額越大,以便使制度能夠發揮懲治作用。結合國外司法實踐可知,賠償金額達到巨額程度,將導致懲罰性賠償制度建立引發醫療行業擔憂,不利于醫療服務的穩定提供,同時也容易引發患者漫天要價的問題,不利于訴訟活動的開展。因此還應設定賠償最高額和最低額,以鼓勵民眾通過合法途徑解決醫療糾紛。
(三)加強配套制度建設
醫療懲罰性賠償制度建立后,只有保證制度能夠落實才能彌補受害人受到的損失。從這一角度來看,還要加強配套制度的建設。考慮到醫療行業具有高風險特點,無可避免的將發生醫療事故。為保證醫療機構和人員有能力支付賠償,還應加強保險制度建設,要求繳納強制性醫療責任保險,起到分擔責任風險的作用。在醫療事故發生后,患者也能通過保險公司獲得應有賠償,從而使醫患糾紛得到緩解。就目前來看,國內缺乏健全醫療保險體系,還應確立責任保險制度進行完善,通過立法促使醫療機構建立責任保險基金,用于支付懲罰性賠償金額[2]。為避免醫院惡意騙保,保險行業也將加入到監管行列中,督促醫療機構加強人員教育培訓,提高人員責任意識。此外,在醫療事故已經發生的情況下,并非全部家庭有能力通過訴訟獲得懲罰性賠償。為解決問題,還應建立非訴訟糾紛仲裁制度,由專門仲裁機構負責協調醫療糾紛,督促醫療機構和人員履行賠償責任。采取該種措施能夠避免啟動繁瑣的法律程序,減輕法院訴訟審理壓力的同時,加速醫患糾紛調解。在醫患雙方能夠達成一致意見的情況下,能夠使侵權方迅速完成賠償行為,保證受害人迅速獲得經濟支持,繼而為患者康復提供保障。
結論:綜上所述,想要使懲罰性賠償制度建立意義得到充分體現,還要對制度的適用范圍進行確認,確保在抑制惡性醫療侵權行為的同時,避免損傷醫護人員的消極處置。在賠償金額確定上,還要根據行為惡意程度保證患者身心損傷得到有效彌補,并完成配套制度建立,保證賠償能夠落實,繼而有效減少由惡意侵權行為引發的醫患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