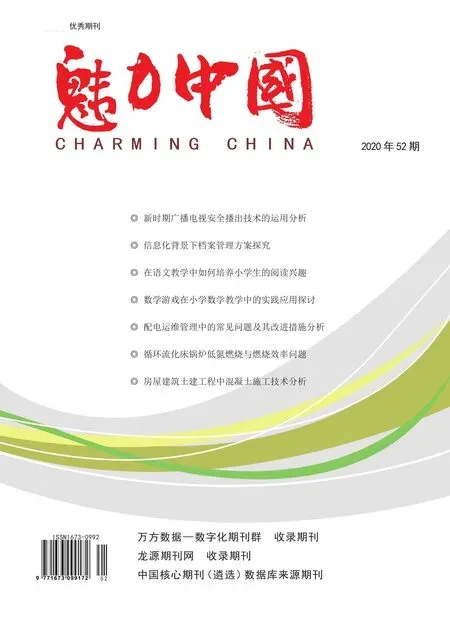“零工經濟”下任務化用工的勞動法規制
(江蘇眾勛律師事務所,江蘇 蘇州 215000)
前言:隨著互聯網經濟的快速發展,為我國勞動市場創造了很多新的發展機遇和就業崗位。學術界中將其稱之為“零工經濟”或“分享經濟”。這樣的經濟模式模糊了從屬性勞動關系和獨立性勞動關系之間的界限,導致兩者之間所存在的灰色地帶逐漸擴大。因此,如何基于勞動法規制的基礎上來化解“零工經濟”對勞動市場所帶來的困境與挑戰成為了當前的一項重要研究課題。
一、“零工經濟”的概念
其實“零工”并不是全新的就業形式,國際勞動組織認為:“零工經濟”的工作形式分為兩種:一方面是眾包工作,也就是可以借助網絡平臺來完成相應的工作,并且這一網絡平臺可以接入不同的組織或者個人,促使全球范圍內的客戶都能夠通過平臺建立聯系;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軟件來展開待命式工作,也就是所有工作的提供及分配都可以通過軟件來完成[1]。由此可知,“零工經濟”是基于互聯網平臺及網絡信息技術的基礎上實現勞動力的臨時按需分配的一種經濟模式。
二、“零工經濟”下任務化用工法律困境
(一)任務化用工削弱了用工關系的繼續性
基于“零工經濟”模式下,平臺企業可以同勞動者之間建立“合作”的合同關系,而平臺企業所承擔的角色就是督促工作完成工作任務的一個信息中介,而勞務提供方則不需要承擔平臺企業的一些訂單義務,同時平臺企業也不需要為勞務提供者的任務數量提供保障。而勞動提供者只需要在有需求的時候向平臺企業提供按需勞務即可,促使雙方之間形成一種不確定的勞務關系。這樣相對自由的用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兩方在用工關系中的相互義務,也因此而削減了勞動關系之間的繼續性特點。
(二)任務化用工降低了用工關系組織從屬性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具備專業技能的獨立勞動者數量越來越多,而用工關系中的組織從屬性開始逐漸從人身從屬性中脫離開來,慢慢成為了判斷從屬性的一個重要標準。我國所頒布的《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中明確提出:組織從屬性是判斷勞動關系的一項必要條件,也就是勞務提供者所付出的勞動應該歸屬于用人單位。勞動給付的組織從屬性需要通過雇傭關系的長期性或者連續性所體現出來,這也是證明勞動給付關系是企業經營重要環節的關鍵[2]。但是任務化用工方式的出現打破了原有的現狀,并致使勞務給付行為變得越發松散,而組織從屬性也逐漸變得難以證明。
(三)任務化用工降低了用工關系經濟從屬性
經濟從屬性可以說是傳統勞務關系中尤為重要的一項特征。因為基于傳統的從屬性理論角度而言,勞動關系的所具備的從屬性一般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雇員始終處于經濟的弱勢的地位上,其需要向雇主提供一定的勞動才能夠獲取相應的工作實現生存的目標;另一方面,雇員的所有生產資料都需要雇主為其提供,并且雇員不需要承擔任何的經營風險。由此可以發現,任務化用工所具備的一系列特征都降低了用工關系之間的經濟從屬性。
三、我國勞動法規制建議
(一)靈活化考量勞動關系的判斷標準
我國所現行的《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中明確了勞動關系的判斷原則,并不斷強調勞動關系需要具備組織從屬性與經濟從屬性等。但是當司法機關基于傳統視角下對“零工經濟”用工關系展開分析,則無法很好地處理隱蔽的勞動關系。因此,司法機關應該與平臺企業的實際運營情況相結合,從而靈活地去考量勞動關系。第一,加強對人身從屬性的認識與理解。第二,對組織從屬性的重視。第三,強化在經營獨立性方面的考察。
(二)勞動法中增設中間保護地帶
我國所頒布的《勞動法》中二元化調整特點是無法有效適應多元化勞動力市場的,因此,勞動關系模式需要由單一調整轉變為綜合調整,并以分類調整的方式來展開區別對待。就立法方面而言非常有必要將中間地帶增設至權利劃分的界限中,為司法機關提供多元化的選擇。首先,勞動法應該將保護范圍進行擴大,并進一步將調整對象由“勞動關系”轉變為“工作關系”。其次,對于經濟依賴型的勞務提供者而言,其權利保障的重點應該放在解決目前職業風險以及收入不穩定等方面。
(三)勞動關系推定排除:設置工作時間門檻
“零工經濟”模式下的勞務提供者是多種多樣的,既包括全職,也包括兼職。因此,可以考慮將不具備實質性就業目的或者僅是偶爾通過勞務提供獲取少量收入的勞務提供者排除在外。在司法實踐過程中,工作的收入標準以及時間一般作為推定排除的門檻,例如:在比利時,如果工人每周的工作時間沒有超過12 個小時,那么就會被認為其從事的工作是邊緣工作或者輔助工作。其實這些標準只是推定的一項重要條件,法院方面會基于事情的本質而考慮雇傭關系。
四、結論
總之,互聯網技術的突飛猛進在很大程度上為“零工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空間和機遇。但是由于“零工經濟”下任務化用工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著很多困境。因此,立法者需要在考慮從屬性問題的基礎上來確定中間主體制度,通過靈活化考量勞動關系的判斷標準、勞動法中增設中間保護地帶、勞動關系推定排除:設置工作時間門檻等方面的完善將勞動法規制的作用及價值充分地發揮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