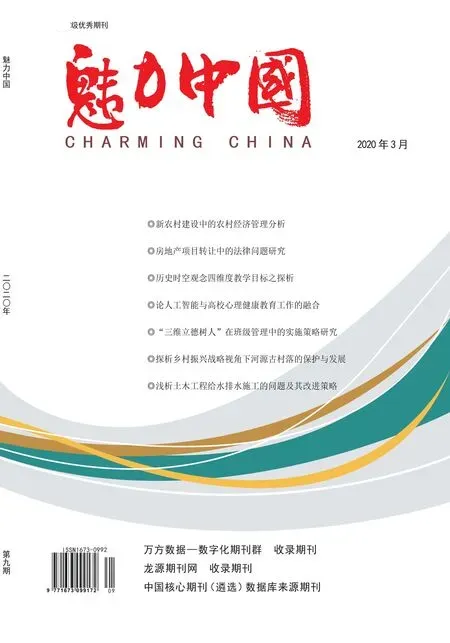論“筆墨當隨現代”說
靳依人
(河南師范大學,河南 新鄉 453003)
石濤《苦瓜和尚語錄》中寫道:“墨之賤筆也以靈,筆之運墨也以神。”石濤更是在筆墨章中確立了“筆墨當隨現代”這一主張,提出了“借古以開今”,拒絕“泥古不化”。宗炳在《畫山水序》中提出了“山水以形媚道”、“澄懷味象”等哲學思想,直接推動了筆墨的發展,使筆墨的內涵有了質的提高。
一、中國畫的變與不變
繼往開來,包羅萬象,時代在變化,中國畫要變嗎?黃賓虹先生說:“變易人間閱滄海,不變民族特殊性。”吾以為,中國畫的不變是中國一脈相承下來的優秀民族文化,是中國畫的根基。那在變與不變,不變中變亦是中國畫特色發展的核心,亦是傳承民族文化需要的新力量,中國畫在變與不變中譜寫時代新風。
支持不變論者認為,在西方的沖擊下,中國畫對自身做出了錯誤判斷,有關文化的不自信,盲目追求西方的東西。在沒有把本國文化消化完,還只流于表面的浮毛,不應講求變。應重摹古為先,不應失了本國特色。但不變維系了中國化發展的血脈和基因,而變卻增添了中國畫無數豐富的內容。我們應當有文化自信,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不變是中華民族之骨肉,變乃中華民族之血液,血液在骨肉中不斷更新流淌。
支持變者認為,一味摹古是停滯不前,是泥古不化,新時代應有新時代的風貌。吾以為,一味地變化只能讓中國的文化流于大眾化、符號化、扁平化,缺乏獨特性與人文關懷。筆墨當隨時代,是要展現時代特色,并非一味地變化。當代是與政治聯系在一起的,我們應堅持做好美育工作,為國家培根鑄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精品奉獻人民。
二、中國繪畫的和而不同
瑞士藝術家海恩瑞希烏爾富林在《藝術史原理》中寫道:“不存在某種能適合于一切時代的藝術形態與風格,藝術作品及其風格,形式特點的形成,不僅同藝術家的個性有關,而且同他浸染接續的時代精神相關。”除了反映當下之外,時代的變化也促進了藝術的發展。筆墨當隨時代而變化,不斷延伸中國畫,豐富它的羽翼,人們才能看到賦予真實感的藝術作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不斷挖掘加入新的東西,以開闊的眼光看世界。孔夫子言:“君子和而不同。”舉例張大千的“潑彩山水”,林風眠的中西融合之路,徐悲鴻的西法引進,都為中國畫探索出新的東西。在他們的繪畫中體現了和而不同。既有中國傳統的筆墨語言,又有新的技法出現,最終在筆墨法度中成就新的精神氣象。不變守的是中國傳統繪畫中的精神、文化氣象。它獨特的魅力、審美訴求、精神意氣不能變。
這種“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融會創新,和而不同,從高的視野看世界,取其美融會貫通,為我所用。而又如何筆墨隨當代、和當代呢?人民是歷史的締造者,是創作的源頭治水,難道不應該扎根人民嗎?我國著名藝術家劉文西先生,深深植根于人民,創作出了展現時代風貌的優秀作品。從藝術本質上來說,藝術創作是現實社會的反映,市人民精神生活的濃縮與提煉,他展現了當代的社會風貌。亦如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真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藝術作品的價值與意義不就是反映現實,展現歷史,為人民發聲嗎?從事文藝事業的工作者任重而道遠。
三、中國畫的破陳出新
有一種說法:“西洋畫是科學,中國畫是哲學。”愛因斯坦說:“哲學可以被認為是全部科學之母。”而中國哲學自古以來就有破陳出新一說。
先破后立的例子數不勝數,生活中酒的制作過程,相當漫長,時間越長就越醇香,一開始它并非酒,而是另一種物質,經過一系列工序,它變成了酒。再如醋的制作過程,臭豆腐的臭變,以死為生,破繭成蝶。最大的不變就是變,變才是永恒的,只有順應變化才能和諧共生。再例如剪紙與篆刻,必先將其破,而后才能立。黃賓虹曾說:“未講創造。則新境界從何而來?”
吾以為,落腳于時代,在本時代變革中國畫創作,反映這一期的時代特色和人文思想。藝術審美的價值并非新就是優,舊就是劣,而是文化品位與藝術水平的高低。石濤說:“我之為我,自有我在。古之須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代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腸。我自收我之肺腑,揭我之須眉。”我們不應該生搬硬套古人的東西,而應在繼承的基礎上推陳出新,若不加思索的臨摹,那就會變成一杯茶,水越沖越無味,若不及時更新茶葉,就是一杯死水。那又如何立足于時代?推陳出新?
在我國,有很多民族過著質樸無華的生活,很多藝術工作者深入其中,融入生活,取材,描繪真實的時代印記,找其特色,反映在新時代下他們的風貌。而都市也有可取的題材,我們可以表現都市人的生活狀態,看看用何種方法來表現他們的強壓,這正是需要我們創新的點。如果描寫現時代。又如何繼承呢?若古代他們用色、配色用到現代的衣物上面呢,是否會顯得更加具有藝術性,更加高雅一些呢?那若我們要破陳出新,連技法也要創新,將表現手法用之于現代,那又會是什么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