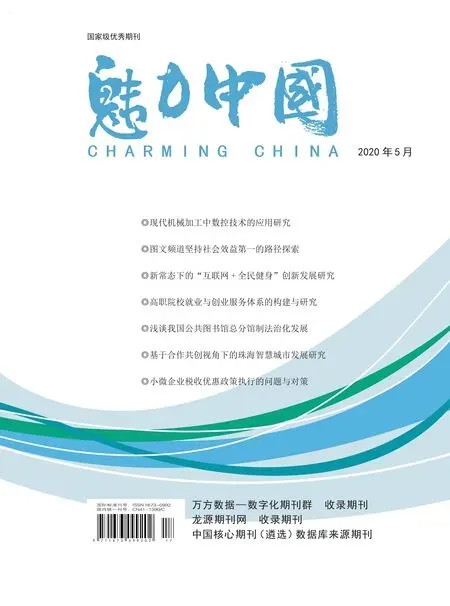淺析花鳥畫中筆墨觀念的演變
(首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北京 100048)
一、氣韻生動與花鳥畫的形成
中國畫作為我國的本土藝術已經發展了數千年,對于中國畫的品評與論述早在魏晉時期就已經十分完善,甚至影響了之后歷朝歷代直至今日。在那個玄學與人物品藻風氣盛行的時代產生了眾多美學命題,如宗炳的“澄懷味象說”、姚最的“心師造化說”,均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以南齊謝赫的《古畫品錄》對后世品評標準影響最大,提出了赫赫有名的六法論。六法第一條法則就是“氣韻生動”,看作品對客體的風度韻致的描繪程度,將氣韻看作畫家的最高品評標準和創作標準,而剩下的五法則都是實現氣韻生動的先題條件,筆法墨法和形象,都是服務于氣韻的傳達。然而,不足的是六法論只論及藝術性方面問題,并無論及思想內容方面的問題,這也為后世畫家們的發展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遺憾的是魏晉時期并未出現花鳥畫家,此時花鳥畫還處于形成時期,包含于山水畫和人物畫之中,上述理論均為針對人物畫和山水畫所總結得出,直到唐代才出現專門的花鳥畫家,就此花鳥畫發展為獨立的畫科并且逐漸發展走向成熟。初唐的西域畫家尉遲乙僧、康薩陀,盛唐的薛稷、邊鸞皆為花鳥畫名家,奠定了花鳥畫藝術形式的基礎。他們的作品雖然沒有流傳下來,但從畫論的描述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此時作品多為線描暈染,鮮艷而生動。筆墨在這一時期并未成為畫中重點,畫面整體氣韻與韻致依然是重要的品評標準,由此可見“氣韻”一詞逐漸擴大到品評人物畫之外,成為各畫科共同的最高目標。
二、以筆墨傳氣韻
晚唐至宋元是花鳥畫大繁榮大發展的時期,涌現出大批杰出的畫家。南齊謝赫于其《古畫品錄》所開創的“氣韻生動”的命題以來,“氣韻”作為繪畫品評的最高標準被歷代畫家所沿用。“氣韻”的實際傳達也是由“筆墨”表現來實現的。二者關系若產生變化則說明時代審美要求產生了變革。五代時期花鳥畫主要由兩種風格,即皇家富貴徐熙野逸,二者雖描繪形象和畫法上不盡相同,但作品都生動傳神,二者筆墨表現都十分干煉,沒有過分表現筆墨本身,而是用線與墨色來表現客觀物象,盡力追求整體氣息與韻致還原所繪形象。
兩宋繪畫繼唐五代之后逐漸老成,文人畫與院體畫相立互存,繪畫美學也進一步發展,在涉及范圍和理論深度上都有很大的突破。宋代花鳥畫也有很高的藝術性,總體上可分為院體畫與文人畫,院體畫主要作品有《果熟來禽圖》、《出水芙蓉圖》等,最楚楚動人的是這些作品中傳達的生動氣息,雖然尺幅不大但仍能虛實相生動靜有序,一花一葉都充滿了自然的靈氣。這些畫院畫家所描繪的花鳥草蟲,栩栩如生楚楚動人。這些作品的筆墨依然只是傳達對象氣韻的工具,用工細的筆墨表現典雅寧靜的氣息,“氣韻生動”依然是這一時期花鳥畫創作的最高標準。另一方面文人畫家則是以蘇軾為代表,較之院體畫家,蘇軾更加強調神似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形理兩全,然后可言曉畫”的理論,蘇軾強調“常理”的重要性,對元代文人畫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這一時期的文人花鳥畫仍沒有擺脫客觀形象的束縛。
元代花鳥畫中所傳達的“逸氣”繼承了宋代的審美情趣,更加傾向于對主觀性情的抒發和表達。漢人政權的覆滅和蒙古社會的嚴峻氛圍中,表達悲憤不得志的世俗情感,抒發漢人士族的高尚人格,“逸氣”隨筆而發,這是“氣韻”在這個時期的特殊體現。這一時期花鳥畫筆法墨法的發展較前代有了較大突破,筆墨技法層面更加的純熟,畫家們逐漸拋棄了五代至宋的勾線填色的工筆畫技法,進一步增強了筆墨在畫中的表現作用,涌現出一大批以王淵、邊魯為例的畫家,他們以墨為色,更加注重筆墨自身的變化,較之宋代審美觀念已有很大不同,但筆墨元素仍為造型表現的工具,并未得到解放。
三、筆墨即氣韻
“筆墨”表現與畫面整體“氣韻”的美學命題在明代中期發生了重大轉變,徐渭開大寫意花卉并將草書融于畫面之中,使筆墨自身審美價值逐漸走向獨立,筆墨形象不僅僅是造型的手段了。筆墨最大限度地擺脫了造型的束縛,筆墨自身也成為了畫家感情的載體,成為了畫家傳情達意的又一形式。這時期的理論界也受到了影響開始形成了“性靈說”和“童心說”等,這些理論共同倡導繪畫應突出精神層面的表達與畫家個人主體性靈的描繪。宋元之時畫家動用筆墨、造型、色彩等眾多因素才可達到“氣韻生動”的傳神行效果,這需要畫面眾多綜合因素的協調參與,“筆墨”只是達到傳神效果的一個基本條件。這時期雖有宋代蘇軾“不求形似”理論的研究;元代“逸筆草草”的社會審美共識和趙孟頫“詩書入畫”理論的發展,但是他們終究在以“似”與“不似”相互討論,無非是神似多一點還是形似多一點的問題。青藤以后,主體性表現現象成為畫壇主流,這就使得“氣韻”的表現極度依賴“筆墨”變化來表現。這反而使花鳥畫離開了外物形體的束縛,傳統的傳神理論得到了發展,畫家主觀情緒更多的出現在了畫面之上。
花鳥畫自明清發生重大變革與發展后,出現了大批理論家,眾多理論家也出現了貶低具象形象,突出筆墨重要性的理論,這時期筆墨成為了品評畫面的最主要的標準,這使得畫家更加注重自身文化修養以及心性品質的修養。清唐岱提出“氣韻由筆墨生”的理論。從他的角度看來筆墨表現即是氣韻,通過效果適當的筆墨效果就能夠達到“氣韻生動”的意境,他的理論與傳統理論背道而馳,將筆墨形式抬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至此為止,花鳥畫以“筆墨”取代“氣韻”成為了重要的畫面品評標準。
總的來看,徐渭開大寫意之先河并引發一系列的思想變革是一道分界線,將畫家對于筆墨的觀念形態分為兩個時期:其一是在徐渭之前,筆墨只是表現“氣韻”的工具,“氣韻”的體現需要筆墨所營造的意境和氣息傳達的綜合效果,筆墨雖然經歷代發展有著多彩的變化,但畫家并沒有解除對形似的傳達,整體上追求形神兼備;另就是青藤出現之后至清代,形似再也不能禁錮畫家的創作,畫家的個人情感融于筆墨之中,筆墨的豐富形成了畫面的“氣韻”,筆墨也成為了花鳥畫品評重要的標準,對后世花鳥畫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