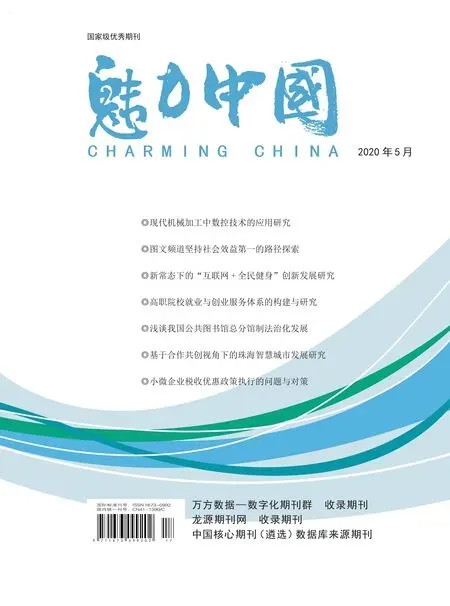澳門區域圖書館評估分析及應用對策
——以何東圖書館為例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廣東 珠海 519088)
一、簡述
公共圖書館面臨著三個趨勢的壓力:數字化社會,形成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社會以及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變化。除了全球趨勢的變化之外,許多國家由于金融危機而削減了公共圖書館的預算。這些挑戰的結果是,公共圖書館被迫向公眾展示其價值,以贏得財政和知識上的支持。
二、文獻綜述
從三個方面介紹相關作品:公共圖書館的感知成果,公共圖書館作為場所以及公共圖書館和社會資本。
(一)公共圖書館的預期結果
為了增強對公共圖書館價值的衡量,建議研究人員在績效衡量的基礎上進一步評估用戶從公共圖書館的經驗中受益的程度,這稱為結果衡量。根據定義,結果或影響代表使用圖書館服務的最終結果。用戶由于與公共圖書館的互動而發生了變化。換句話說,結果測量強調了公共圖書館對個人或一組用戶的影響。
(二)公共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在為人們提供正式或非正式聚會的場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實際上,“圖書館作為一個地方”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奧爾登堡(Oldenburg,1989)。在他的書中,一個很棒的好地方:咖啡館,咖啡店,書店,酒吧,美發沙龍和其他在社區中心的聚會場所,奧爾登堡討論了建立非正式聚會場所的重要性,此后以“第三名”命名。“第一名” 代表家,“第二名”代表工作場所。“第三名”是非正式的公共聚會場所,而不是家庭和工作場所。奧爾登堡觀察到公民參與率的下降,并與缺乏非正式聚會場所有關。當人們僅在家庭和工作場所之間上下班時,與鄰居或社區的互動將減少,并限制了社交網絡。
(三)公共圖書館與社會資本
1961 年,哈尼凡(Hanifan)首次提到了社會資本(Putnam 2000)。他用這個詞來形容團體或家庭中個人之間的善意,團契,相互同情和社交。但是,當時社會資本的研究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布迪厄,科爾曼和普特南發表有關著作之后,對社會資本的研究逐漸增多(Halpern 2004)。根據布迪厄(Bourdieu,1986),社會資本是個人或團體有形和無形資產的積累,可以用來實現個人或團體的目標。在圖書館和信息科學領域,普特南對社會資本的定義已在大多數研究中得到應用。根據普特南(Putnam,1995),社會資本包括社會生活,社會網絡,信任和規范的三個指標,“使參與者能夠更有效地共同行動以追求共同的目標。”
根據社會網絡的力量,社會資本可以進一步分為綁定社會資本和橋接社會資本。束縛社會資本是親戚和朋友之間為向人們提供社會支持而建立的牢固關系,而彌合社會資本是異類人之間為促進人們獲得新資源而所建立的脆弱關系(Halpern 2004;Johnson 2012;Svenden 2013)。從對社會資本的信任的觀點來看,可以將其專門化為人們對認識的人的特定信任,以及表示人們對公眾的信任的廣義信任(Uslaner 2002)。
三、研究目的和問題
近年來,澳門甚至亞洲的公共圖書館設施和服務都在蓬勃發展。輸入和輸出度量是評估該地區公共圖書館價值的主要方法;此外,很少有關于圖書館作為場所及其對培育這些圖書館的社會資本的貢獻的研究。有鑒于此,本文嘗試從何東圖書館的角度調查該地區公共圖書館的感知成果和社會價值。本研究旨在根據上述目標回答以下研究問題:
a)何東圖書館的預期成果是什么?
b)何東圖書館的使用者在多大程度上將圖書館用作場所?c)何東圖書館如何幫助用戶培養社會資本?
d)感知結果,圖書館作為場所,社會資本和圖書館使用之間的相關性是什么?
四、公共圖書館使用率
(一)方法
何東圖書館是澳門一個社區的公共圖書館,人口約 33,000。通過問卷調查收集數據。調查工具包括五個部分。第 1 節收集了有關受訪者的人口統計信息,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居住地,以及從受訪者的家到圖書館的距離,圖書館的使用頻率以及他/她在圖書館的平均停留時間。第 2 節詢問受訪者訪問圖書館的目的和使用的圖書館空間。第三部分是關于根據 Vakkari 和 Serola 的研究(Vakkari 和 Serola,2012 年)得出的公共圖書館的預期成果。第 4 節收集了受訪者關于他們如何使用的意見。圖書館是一個地方(第三名或聚會地點),而第 5 節則涉及新加坡圖書館如何幫助受訪者培育社會資本。三名專家審查了問卷項目的內容有效性。Cronbach 的α 值大于 0.7 時,收集了三十(30)個測試前響應。然后,在 2014 年 5 月至 6 月期間,當用戶訪問何東圖書館時,向他們分發了正式的問卷。收集了 486 份(486)答復,其中 387 份有效。然后通過SPSS 22.0 通過描述性統計,因子分析和邏輯回歸分析來分析有效響應在感知結果,圖書館作為場所和社會資本方面,結構的 Cronbachα 值均大于 0.7。
(二)結果與討論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從人口統計信息和圖書館使用,對新光圖書館的成果,圖書館作為場所以及圖書館之間的社會資本四個方面進行了問卷調查分析。
五、人口統計信息和圖書館使用
何東圖書館的女性用戶(61.8%)比男性(38.2%)多,這與多項公共圖書館研究相似(新南威爾士州立圖書館,2000 年;Leckie 和 Hopkins,2002年;Vakkari 和 Serola,2012 年)。大多數受訪者年齡在 7 至 14 歲之間(38.8%),其次是 25 至 44 歲的組(26.1%)。由于何東圖書館位于社區,因此年齡超過 55 歲的受訪者非常稀少(1.6%)也就不足為奇了。大約57.6%的受訪者是學生,12.4%的教師或公務員,而 9.1%的職業與工業,生產和建筑有關。花王堂區鎮約有四分之三(75.1%)的人口居住在該地區,而73.0%的人可以在 15 分鐘內到達何東圖書館,這意味著何東圖書館對其大多數用戶都是可用的。
在圖書館使用頻率方面,有 26.6%的受訪者每月訪問圖書館 1 至 3 次。22%的人每周訪問圖書館兩次。8.1%是最重的用戶,他們每周訪問圖書館超過 3次。大約是用戶在圖書館的平均停留時間,其中 32.7%的人在 0.5 到 1 個小時內停留在圖書館中,27.8%的人在 1 到 2 個小時內停留,16.7%的 2 到 4 個小時。
用戶訪問何東圖書館的五大目的(多項選擇)是借書和還書(47.8%),自學(33.6%),尋找信息(31.5%),休閑和放松(30.0%)以及閱讀/收聽/觀看圖書館資料(24.8%)。這個發現與萊基和霍普金斯(2002),以及新南威爾士州立圖書館(2000)。
這項研究對新光圖書館的用戶是否獨自訪問過該圖書館感興趣。答復顯示,有 62.2% 的受訪者可能會與其家人和/或親戚一起參觀新光圖書館;可能有37.8%的人光顧圖書館。可能分別有 35.7%和 32.0%的朋友和他們的同學/同事/同事一起去圖書館。這一發現與 Fisher 等人的發現有些不同。(2007),Leckie 和 Hopkins(2002)以及新南威爾士州立圖書館(2000),因為他們的所有研究都表明,大多數用戶只是去圖書館。
六、結論
何東圖書館作為聚會場所,有助于培育橋接社會資本,尤其是在圖書館用作低強度聚會場所時。與家人一起拜訪的用戶之間也有結合的社會資本。本文聲稱圖書館使用頻率,感知結果,圖書館作為聚會場所和圖書館培育社會資本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據我們所知,這是一起討論所有概念的第一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