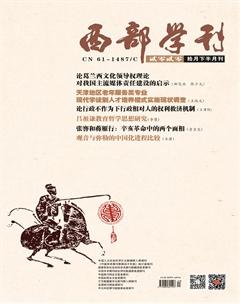淺析晚清婦女守節現象
摘要:清承明制,對節烈婦女進行旌表,并且降低了旌表的標準,擴大旌表的范圍,使清代旌表的貞節烈婦的人數達到歷朝歷代之最。道光年間,出現貞節堂的雛形。貞節堂在晚清出現,是貞節觀念極端化的又一物化象征,它是用來維護封建綱常禮教的,是對婦女的一種束縛和戕害。但是作為一種新的機構制度,貞節堂的社會功能后來逐步由對節婦貞女的恤濟向公共慈善事業嬗變。
關鍵詞:晚清;貞節觀念;守節;婦女
中圖分類號:C913.68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0)20-0120-03
一、緒論
“貞”字最早出現在甲骨文中,最初的含義極少與女子相聯系。通常指堅定、有貞操等含義,在這種釋義當中可以看出此時并不單單只是用于女性。“節”是指氣節、操守之意,常指一個人能夠堅守信念。但隨著封建禮教的發展,“貞節”一詞逐漸演變成專門對于女性提出的要求。學術界通常認為,婦女守節現象是從宋朝開始。在宋以前,有不少寡婦再嫁現象,但是到宋元以后,社會對于婦女的道德約束越發嚴格,此時不僅節婦大量涌現,就連貞女數量也不斷上升。這里便要引入一個概念“貞女”。貞女不同于節婦,也不同于烈女,美國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教授盧葦菁教授在《矢志不渝:明清時期的貞女現象》中寫道:“貞女就是具有深刻道德操守的女性,她把原則看得高于生命,拒絕向恐嚇與威脅低頭。”劉向在《列女傳》中,被稱為“貞”的女性包括夫死不嫁的節婦和拒絕離開身患絕癥或受冷落丈夫的女子。總結前人觀點,貞女即是指為未婚夫守志的女子。相比節婦,此類女子更為人“敬佩”。因為,貞女守志的對象不是丈夫而是未婚夫。在古代傳統社會,婚姻從來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們很有可能連未來丈夫的面都未曾見過,居然能夠為其守節一生更有甚者為其殉節,此舉實在是令人敬佩且詫異。那么,是什么使得這些女子不顧生命去守節呢?
從秦漢到元明的這段時期,雖然對于“貞節”的關注度很高,但婦女的離婚與改嫁卻很少受到限制。可到明清時,這種情況開始發生了逆轉。明清時期封建禮教達到頂峰,對于婦女的束縛更是嚴格。一方面,貞節從一種觀念演變成了在社會上的實踐;另一方面,隨著專制主義達到頂峰狀態,對貞節的要求體現在宗教層面上。明清時期的婦女守節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經過封建統治者的大力支持與女教圣人們的宣揚鼓吹,這種貞節觀念已經失去了理性成份,充斥著迷信色彩,最終走向了宗教化。除此之外,明清統治者對于節婦貞女的大力旌表,也使得明清時期,甚至一直到晚清,社會上對婦女的貞節看得非常重要。
二、貞節觀念的演變
貞節觀念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產生,《禮記》中明確強調,所謂“婦人”,就是“伏于人者”,宣稱“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1]。從這一句話可以看出男尊女卑的觀念由來已久。孔子也曾提過“三從四德”等觀念。婦女的地位在社會上無法與男性地位相對等。到秦漢時期,貞節觀念仍顯寬泛,它更多的是被納入女德范圍而受到提倡。例如秦始皇重視貞節,幾次刻石,都曾提及。泰山刻石有云:男女禮順,慎尊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凈。[2]42漢代是禮教形成的重要時期,兩個女教圣人劉向和班昭都對女子行為提出了規范性的要求。但這些都是在對待男女關系上,強調女子要順從她的丈夫,男尊女卑,夫強婦弱,而并未單獨突出貞節觀念。且秦漢社會婦女改嫁與再嫁的現實狀況也都存在。在后漢書《列女傳》中有幾個再嫁的例子,例如荀爽之女采,“十七嫁陰瑜,十九產一女而瑜死。后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雖然采以不愿嫁而自縊,成其節烈之名,但荀爽不以改嫁其女為非,奕亦不以愿娶再嫁婦為辱”[2]58。這里采雖然自殺以取得節烈之名,但是從其父荀爽以及郭奕的態度上看來,當時對于女子再嫁并未存在道德上的譴責,只不過采可能是深受《女戒》以及其他女子讀物的影響,加之對死去丈夫的情意,所以才不愿意再嫁他人。社會對待婚姻的態度也都是有意則留,無意則去的態度。
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貞節觀念又再度被提倡。在魏晉南北朝這樣離亂的年代,貞節觀念并未因戰爭的混亂而淡化,北齊《羊烈家傳》說道:“一門女不許再醮”[2]48。羊家為了使婦女守節,專門建造了一個尼姑庵,女子失去丈夫后就出家為尼。再看看隋唐時期,貞節觀念逐漸松弛,何以見得?在唐代,公主再嫁者,達二十三人,三嫁者四人[2]118。公主再嫁可以認為是因為位高權重,所以不足為奇。但是如韓愈的女兒曾先嫁給李氏,后又嫁給了樊宗懿,這足以表明再嫁不是位高權重的專利,而是得到整個社會的默許。由于貞節觀念淡薄,唐代婦女的名節不如后世之重,淫泆之事時有發生,也不會受到什么懲罰[1]。從宋元時期開始,隨著理學的形成與興盛,貞節觀念越發受到世人的重視。但宋元終究是貞節觀念的穩定形成和發展時期,期間對于婦女貞節方面的要求還并未非常嚴格。
明清時期的貞節觀念可謂是達到了頂峰。走向宗教化,是明清貞節觀發展的一個特點。到晚清時期,守節現象依然存在。雖然晚清以來受到了各種外來列強的侵略戰爭以及內部農民起義的沖擊,根深蒂固的貞節觀念并未因此而動搖。
三、晚清貞節觀的延續與發展
晚清是個劇烈動蕩的時期,在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甲午戰爭、中法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等一系列戰爭以及各種外來思想的沖擊之下,晚清王朝早已搖搖欲墜。但即便是在這樣的國情和社會環境下,對于貞節觀念,懷有守舊思想的人依然不肯放松。
清承明制,在對待貞節觀念上也不例外。清朝屬于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朝代,滿族早先的貞節觀念比較淡漠,婦女再嫁現象屢見不鮮,沒有特意倡導“守節”。但是,已經結婚的女性在婚姻關系中也被要求忠貞不二,從一而終。但社會上對于未婚女子,并未有守節的強制要求。從歷史文獻記載來看,滿族的習俗常常被描述為“婦貞而女淫”[3]。直到清兵入主中原后,滿族統治者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不得不接受漢族的禮教思想,貞節觀念也由此不斷得到強化。在清朝中后期,滿族婦女在丈夫死后也多為其守節,甚少出現改嫁的情況。此外,清朝的統治者還提倡節烈女,并延續了明朝做法。對節烈婦女進行旌表,并且降低了旌表的標準,擴大旌表的范圍,使清代旌表的貞節烈婦的人數達到歷朝歷代之最。清朝政府的旌表節婦活動順治初年已經開始。一組數據中可以看出清朝對于守節婦女的態度。根據《清實錄》的記載,從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起到十八年(公元1661年)間,共旌表節婦403人,烈婦175人。康熙一朝共61年,旌表節婦總數4822人,再到雍正帝繼位后節婦受旌表的人數達到9995人。乾隆時期受旌表的人數仍然有增無減,總計有32521人。嘉慶25年里,旌表人數達到29179人。道光的30年間(公元1821—1850年),由朝廷表彰的節婦有93668人,咸豐一朝節婦達77025人。到同治年間,旌表的節婦增至到190040人[4]。以上所列舉僅是朝廷所旌表,為世人所公認的節婦。民間一些因不滿足朝廷的要求未被表彰的節婦未列其中。數字如此之龐大,令人驚奇。雖然社會上也存在一些要求婦女再嫁的呼聲,但是女子必須守節、從一而終的呼聲甚囂塵上。
四、晚清的貞節堂制度
晚清女性貞節禮俗的社會功能不斷加強,女性節烈楷模的示范效應的作用被不斷突顯。社會雖未像宋理之學出現后大力推崇倡導貞節觀念,但是通過統治者的大力旌表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使得社會非常看重守節的重要性。隨著社會對于貞節觀念的不斷強調,婦女內心已深深感受到守節對于一個女人的重要程度。她們無需社會給予壓力,自己心甘情愿做一個守節的女子。
從道光年間開始,城市中的頭面人物開始建造公共的寡婦堂來供貧困寡婦居住[4]。這是晚清貞節堂的雛形。貞節堂在晚清出現,是貞節觀念極端化的又一物化象征。但是作為一種新的機構制度,貞節堂的社會功能正逐步由對節婦貞女的恤濟向公共慈善事業的近代化嬗變[4]97。為了使節烈之風發揚光大,清代對婦女經濟上的獎勵和資助發展到晚清時,逐漸演化為一種專門救助寡婦的貞節堂制度[5]97。政府的極力提倡,社會上的強烈呼聲,貞節的宗教化發展以及社會經濟的衰落,使得“節婦”群體日益龐大,她們無依無靠,生活難以為繼,于是貞節堂組織便應運而生。貞節堂的條約明確規定,貞節堂的功用在于收養節婦貞女。婦女在丈夫死后愿意堅志守貞,并且家境貧寒,無所依靠。對于請求入堂的婦女,司事須調查清楚,并且要有人保薦方可入內。婦女一旦進入貞節堂,不僅“男親族無論長幼,概不準入堂見面”,而且連“三尺之童,概不許入”,“節婦所帶幼童大十歲以上者,不得居住內堂”,這完全斷絕了她們與外界的聯系。為了保證堂內寡婦的貞節不受外界的“污染”,堂內的大門除非有特別的事情才會打開,否則終日閉門。堂內設立的轉桶梆門,也是整日封鎖的,寡婦們生活在一個完全與外界隔離的空間中,對外界的變化一無所知。堂內設兩把鐵鎖,司事各掌其一,“開門拆封,須兩人會齊”。對于生活中所用物資的輸送傳遞事宜,例如取水、送水,購買生活必需品等,“梆門內每院設水缸二,每日開門兩次,送水傳遞物件;外有木梆,內有云板”,“服役人等必由司事稽查,不得任意啟閉關”。如果有親眷探望必須先通知司事,然后再安排其在轉桶處相見。只有當節婦貞女患病勢危的時候,親眷來堂看視“方準開門進內”[5]100。堂內規定對于入堂的寡婦的生活所作出種種限制,如不遵守這些規章制度,這些節婦們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貞節堂制度建立的出發點就是要確保這些節婦們能保持自己守節之身,不被外界所“污染”,盡管貞節堂保障節婦們的生計,帶有一種慈善救助的意味,但是它也是一種強化貞節觀念的手段,將節婦的言行控制住,來保證貞節的純潔性。貞節堂“將束縛、禁錮入堂寡婦作為第一要義,它對宗教化的貞節觀念作出了更為豐富的物化闡釋,在封建倫理的踐行推波助瀾以后,成為貞節殺人的幫兇”[6]186。貞節堂與貞節牌坊的作用是一樣的,它是用來維護封建綱常禮教的,是對婦女的一種束縛和戕害。
作為一種制度機構,“貞節堂在同治后數十年大量出現,多少透露出女性貞節制度以及救助制度在近代即將發生變革前的一點信息,那就是,對節婦貞女的恤濟開始向公共慈善事業轉變”[5]100。大量的節婦進入貞節堂,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這些節婦的生命。但是失去丈夫的婦女生活是艱難的,在晚清時期,纏足、三從四德等腐朽的行為思想已經將女性的生命模式固定好了,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是她們固定的生存模式。婦女的思想從未被在意,婦女的聲音從未被聆聽。久而久之,這些婦女們逐漸喪失了自己的人格與獨立性,變成了男人的附庸。
五、對貞節觀的批判
鴉片戰爭之后,大量西學進入中國的大門,各種西方新思想也開始在中國傳播。晚清婦女生活中逐漸加入了新的因素。例如不纏足運動的興起,女學堂、女學報的創辦,婚姻自由觀念的發展。晚清是中國社會的一個轉型期,傳統與現代產生劇烈沖突,婦女的意識開始覺醒。康有為、譚嗣同等為代表的維新派就對強迫寡婦守節的封建道德進行了憤怒的譴責,他們認為,程朱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封建綱常名教,造成了“億萬京垓寡婦,窮巷慘凄,寒餓交迫,幽怨彌天地”的人間悲劇,“以人權平等之義,則不當為男子守苦;以公眾孽生之義,則不當以獨人害公;以人道樂利之宜,則不當令女子怨苦。”所以寡婦守節是“萬不可行”的[7]152。受到維新思想熏陶的女子對于貞節觀也有所認識,她們問道:“男何以不貞節,不責之男而僅責女”[8]。男子可以不忠于妻子,三妻四妾,而女子卻終身只能從一而終,否則將會遭受世俗的譴責與處置。這是自古遺留下的毒瘤,而新思想的傳播,啟發了世代受壓迫的女性,使它們有了更為大膽的想法。除此之外,在清末民初時,貞節觀念也是受到了進一步的批判。有學者指出“守節”是男人壓制婦女之術,使得“為婦人者,一切學問不加研求,亦徒以守節一端為莫大事業矣”,也有人指出婦人守節,不僅不仁道,而且是極不平等的[9]。男子無人守節卻處處逼迫婦女守節余生,這是極其不合理的。
不僅在鴉片戰爭后存在對貞節觀的批判聲音,在此之前也有一些有識之士對此作出了譴責。這可以追溯到明代思想家李贄,他以“童心說”為標準,對儒家思想的許多觀點進行了批判。他主張男女平等,反對歧視婦女。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唐甄從人之天賦人格平等出發,主張夫婦、男女關系都應該是平等的,“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傳統的‘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等封建綱常倫理”[10]263。清代著名學者俞正燮對“男尊女卑”婦女觀批判的力度是最大的。在他的《癸巳類稿》和《癸巳存稿》中與女性相關的篇章當中,大力批判了封建禮教對人性的摧殘。“俞正燮對于貞節觀的批判更加有力,《節婦說》主張男女在婚姻道德上的標準應一致,‘古言終身不改,身則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理儀無涘,而深文以罔婦人,是無恥之論也![10]264”一些開明的學者對于守節觀的認識以及對于封建禮教的抨擊,說明了在清代,雖然婦女貞節觀走向了極致,但也面臨著的走向其反面的局面。婦女借助新思想的傳播,逐漸沖破牢籠的束縛,走向一個新的美好生活。
結語
幾千年來,婦女所承受的壓迫是難以用言語來形容的,封建禮教的條條框框使得婦女淪落為男性的玩物。隨著社會的發展,風氣逐漸開化,女性的地位開始慢慢提升。貞節觀念也逐漸淡出了人們的思維。但是,要把這種根深蒂固的舊思想徹底移除,應該還需要時間的消磨。晚清距今已有一百多年,期間經歷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新中國成立以及改革開放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但是在一些偏遠的農村地帶,這種貞節觀的殘余仍然存在。男子喪妻再娶與女子喪夫再嫁,在一些人眼中仍然具有不同的性質。所幸的是,社會上已經不存在如封建社會那般對于女性的歧視與壓迫了。女性有了獨立的人格、思想,擺脫了封建禮教束縛,有權力有能力改變自己的命運。
參考文獻:
[1]張娟.明清婦女貞節觀成因淺析[J].中國民族博覽,2017(9).
[2]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3]高松.略論滿族貞節觀念的轉變[J].滿語研究,2017(2).
[4]高邁.我國貞節堂制度的演變[J].東方雜志,1935(2).
[5]張雪蓉.晚清女性貞節禮俗社會教化功能的強化及其變化探微[J].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
[6]章義和,陳春雷.貞節史[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
[7]康有為.大同書[M].北京:中華書局,1956.
[8]王椿林.男女平等論[J].女學報,1898(5).
[9]陳文聯.近代中國思想界對封建“貞操觀”的批判[J].衡陽師范學院學報,2001(5).
[10]羅慧蘭.中國婦女史[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
作者簡介:章慧敏(1996—),女,漢族,安徽宣城人,單位為蘇州科技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管理學院,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社會史。
(責任編輯: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