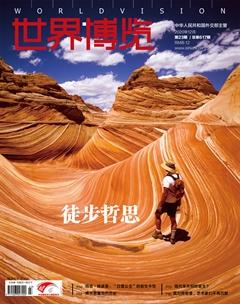佩德羅·阿莫多瓦:用色彩反抗世界
耐吉
佩德羅·阿莫多瓦的電影里有著極具風(fēng)格化的敘事水準(zhǔn)和高飽和度的藝術(shù)把控,在瑰麗的影像風(fēng)格之中透露出的是坦誠(chéng)且具有紀(jì)實(shí)性的鏡頭語(yǔ)言,而他的雙性化人格更賦予了他的電影雙性化的特點(diǎn),從而形成了獨(dú)特的藝術(shù)魅力。
2020年9月,在第77屆威尼斯國(guó)際電影節(jié)上,除了最終榮獲金獅大獎(jiǎng)的趙婷導(dǎo)演的《無(wú)依之地》外,最大牌的一部作品,當(dāng)屬西班牙電影大師佩德羅·阿莫多瓦的新片《人類的呼聲》。
佩德羅·阿莫多瓦是西班牙電影界最具影響力的標(biāo)志性人物,后現(xiàn)代的美學(xué)、夸張戲謔的故事和養(yǎng)眼的題材也讓他的作品備受爭(zhēng)議。阿莫多瓦受波普文化和美國(guó)黑色電影的影響很深,再加上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和極端的表現(xiàn)方式,讓他在行業(yè)中脫穎而出。
“變色龍”背后的憂傷
阿莫多瓦出生在西班牙一個(gè)名叫卡爾澤達(dá)的小鎮(zhèn),那里崇尚男尊女卑的觀念:男人什么都不必做,女人則需負(fù)責(zé)所有大大小小的事,這讓他在小小年紀(jì)時(shí)就對(duì)“萬(wàn)能的女性”充滿了崇敬之心,并對(duì)真實(shí)世界及宗教價(jià)值產(chǎn)生疑惑與失望。
他的沒(méi)有文化的父親以販賣葡萄酒為生,但因經(jīng)營(yíng)不善而屢屢虧本。母親緊衣縮食供阿莫多瓦讀書,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成為牧師,這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貧窮家庭的孩子來(lái)說(shuō)是最好的出路。兒時(shí)的阿莫多瓦在圣方濟(jì)各派的教會(huì)學(xué)校上課,參加合唱團(tuán)。糟糕的教育制度令他苦惱,偽善的神父的侵犯行為更使他徹底喪失了對(duì)宗教的信仰。對(duì)統(tǒng)治階級(jí)和虛偽宗教的嗤之以鼻,以及對(duì)社會(huì)邊緣貧窮人群的關(guān)懷,構(gòu)成了他深刻的童年記憶,也為日后創(chuàng)作提供了素材。
阿莫多瓦因特殊的性取向而被小鎮(zhèn)居民投以異樣的眼光。但他并沒(méi)有因此沉淪,那時(shí)的電影給了他最大的安慰。他10歲開始看電影,喜歡道格拉斯·瑟克、比利·懷德和希區(qū)柯克好萊塢式的表達(dá),也鐘愛布努埃爾這樣的歐洲先鋒派導(dǎo)演,銀幕女神瑪麗蓮·夢(mèng)露和娜塔莉·伍德的一顰一笑都牽動(dòng)著他的心。
上世紀(jì)六七十年代,佛朗哥專制政權(quán)走到末路,波普文化和搖滾樂(lè)培育了西班牙濃厚的藝術(shù)氣息。16歲的阿莫多瓦毅然放棄進(jìn)入修道院大學(xué)的機(jī)會(huì),在和父母激烈爭(zhēng)吵后,孤身一人前往馬德里嘗試尋求學(xué)習(xí)拍電影的機(jī)會(huì)。
然而,當(dāng)時(shí)電影學(xué)校都被政府關(guān)閉,他不得不靠在跳蚤市場(chǎng)賣小飾品來(lái)養(yǎng)活自己。緊接著,他在電話公司找到了正式工作,白天是勤奮的職員,夜晚留著長(zhǎng)發(fā)成為地下藝術(shù)活動(dòng)的小頭目。阿莫多瓦攢錢買了臺(tái)超8攝影機(jī),拍了很多有關(guān)中產(chǎn)階級(jí)生活的作品。他從不接受任何晉升,這讓電信公司同事驚訝不已。他靠業(yè)余時(shí)間為刊物創(chuàng)作小說(shuō)漫畫,組織業(yè)余劇團(tuán)表演,讓自學(xué)的書本理論知識(shí)落地發(fā)芽。
隨后,阿莫多瓦這位“新潮派”藝術(shù)的代表人物,帶來(lái)了尺度大膽的《烈女傳》和《激情迷宮》,轟動(dòng)影壇。他戲謔地批判腐朽的道德規(guī)則,贊頌人與人之間的情誼,宣泄了自己壓抑已久的欲望,收獲了非凡的反響。可到了拍攝《欲望法則》時(shí),他卻申請(qǐng)不到銀行貸款,得不到官方機(jī)構(gòu)的支持,劇組人員的巧言令色讓他體會(huì)到了人情冷暖,不得不放下面子向朋友
借錢。
但他并沒(méi)有因此被打垮,而是選擇和弟弟阿古斯丁創(chuàng)辦了名為“欲望無(wú)限”的制片公司,在柏林影展吸引國(guó)際發(fā)行商的關(guān)注,為他打開了美國(guó)市場(chǎng)的大門。精力旺盛的阿莫多瓦迎來(lái)了施展才華大展拳腳的黃金時(shí)代。
阿莫多瓦知道如何將眾多看似狗血的元素融入劇情中,用荒誕的手法折射人性的明暗,演繹人間的低俗悲喜劇。與此同時(shí),鮮明的個(gè)人色彩符號(hào)、夸張的角色情緒和先鋒的室內(nèi)建筑設(shè)計(jì),再加上歌舞、戲劇和西班牙斗牛等元素的搭配,構(gòu)建起他獨(dú)到的美學(xué)風(fēng)格。
1980年代的海洛因幾乎毀了整整一代人,阿莫多瓦沒(méi)有沉溺于癮君子的糜爛,而是將全部精力專注于描摹形形色色的人物。他從周遭環(huán)境中吸收了無(wú)限養(yǎng)分,尤其是對(duì)少數(shù)派人物情感的把控,使他從挑戰(zhàn)社會(huì)價(jià)值觀的小眾藝術(shù)家一路逆襲,成為世界主流的電影導(dǎo)演。
在阿莫多瓦成長(zhǎng)的村莊,女人只能穿黑色的服裝,這導(dǎo)致了他對(duì)色彩的極度渴望。受到安迪·沃霍爾、畢加索、達(dá)利的影響,以及地中海、加勒比、阿拉伯以及西班牙的地域藝術(shù)熏陶,身為完美主義者和控制狂的阿莫多瓦對(duì)美有著敏銳的嗅覺,他還經(jīng)常擔(dān)任自己片子的美術(shù)指導(dǎo)。《胡麗葉塔》中的女主角阿德里亞娜·烏加特曾表示,導(dǎo)演會(huì)親自監(jiān)督并決定所有細(xì)節(jié),甚至一個(gè)只出現(xiàn)兩次沒(méi)人注意的鑰匙扣,他都會(huì)親自挑選。
善惡之間的飲食男女
除去華麗的視聽元素,成長(zhǎng)于社會(huì)大學(xué)的阿莫多瓦塑造人物時(shí)嚴(yán)謹(jǐn)而苛刻。他戲里的角色看似卑微諂媚,卻對(duì)生命抱以最純粹的期許;看似地位高貴,卻無(wú)法舍棄對(duì)舊日時(shí)光的依戀。他們的行為荒唐,但并不邊緣,因?yàn)樵诂F(xiàn)實(shí)生活中,人性始終處于善惡之間,他們的一舉一動(dòng)對(duì)照著觀眾潛意識(shí)里無(wú)法被滿足的深層愿望。
雙性化的思維模式讓阿莫多瓦能精準(zhǔn)把握好男性和女性的特質(zhì)。《對(duì)她說(shuō)》中,男主內(nèi)尼諾對(duì)女性有這樣的描述:“女人的腦袋很神秘,對(duì)她們要有耐性,跟她們講話要細(xì)心點(diǎn),偶爾要撫摩她們,記住她們存在、她們活著。”他的電影中無(wú)處不體現(xiàn)對(duì)女性的關(guān)懷,她們的細(xì)膩敏感在他的描摹下熠熠生輝。
“女性能夠給我提供喜劇素材,而男性只能讓我寫出悲劇。”阿莫多瓦電影里的男性有強(qiáng)大的控制欲,這讓他們更容易身處泥潭而無(wú)法自拔。《對(duì)她說(shuō)》里的內(nèi)尼諾花費(fèi)4年時(shí)間,精心照料昏迷不醒的芭蕾舞者阿麗夏,享受著與沉睡愛人的靈魂對(duì)談;《捆著我,綁著我》中的里奇是被雙親拋棄的孤兒,用綁架的方式向心愛的女星示愛;《吾棲之膚》里的外科醫(yī)生無(wú)法承受女兒的去世,用整容術(shù)再造妻子,換來(lái)的卻是無(wú)愛的背叛。愛使人發(fā)瘋,阿莫多瓦將男性內(nèi)心世界被壓制的狂熱放大,觀眾在獵奇之余不免會(huì)被他們的執(zhí)著觸動(dòng)。
在被阿莫多瓦視為個(gè)人最好劇本的《不良教育》中,初戀男孩與貪婪的敲詐犯、高潔的神父與猥瑣的入室者、年輕有為的導(dǎo)演與權(quán)力的掌控者,看似相反的人物形象都能在同一角色身上得以中和。毀滅性的沖突背后,包容著人類誕生之初的純潔以及在欲望和名利誘導(dǎo)下的迷失。生活無(wú)常,人亦如此,復(fù)雜的表象中往往蘊(yùn)含著單純的動(dòng)機(jī)。
女人的獨(dú)角戲
《人類的呼聲》是一部女人的獨(dú)角戲,是關(guān)于愛情、欲望和自我救贖的啟示錄。它改編自法國(guó)電影文學(xué)大師讓·谷克多寫于1928年的獨(dú)幕劇《人之聲》。這部時(shí)長(zhǎng)30分鐘的短片,也是阿莫多瓦與“高冷女王”蒂爾達(dá)·斯文頓的首次合作。蒂爾達(dá)·斯文頓在接受媒體采訪時(shí)說(shuō):“我曾經(jīng)請(qǐng)一個(gè)牧師為我祈禱,讓我可以在一部佩德羅·阿莫多瓦的電影中扮演角色。我曾以為這是不可能的,因?yàn)槲也粫?huì)說(shuō)西班牙語(yǔ)。但是電影是一種通過(guò)凝視、理解而形成的全球性通用語(yǔ)言。”
電影講述的故事是關(guān)于一個(gè)女人和情人之間的最后一次電話,而她的情人正打算娶另一個(gè)女人為妻。阿莫多瓦從這部獨(dú)幕劇中汲取靈感,由此誕生了他創(chuàng)作生涯中難得的英文對(duì)白作品。
極度大膽的色彩運(yùn)用,頗具張力的表演狀態(tài),愛恨分明的角色塑造,向來(lái)是阿莫多瓦電影中明艷的西班牙底色。在《人類的呼聲》中,他再次用極具代入感的鏡頭,剖開了一個(gè)瀕臨崩潰邊緣的女人的迷失、掙扎和浴火重生。
第一個(gè)鏡頭,在灰暗空曠的倉(cāng)庫(kù)里,蒂爾達(dá)·斯文頓身穿一襲華麗紅裙,悵然若失地在一把木椅上坐下。此時(shí)的她,碎發(fā)凌亂,眼神空洞。畫面一轉(zhuǎn),她又換成一身黑袍,呼吸沉重。整整2分鐘,沒(méi)有一句臺(tái)詞。唯有聚光燈打在蒂爾達(dá)削瘦蒼白的臉上,戲劇感呼之欲出。
隨后故事正式展開。身穿明亮藍(lán)色西服的蒂爾達(dá)·斯文頓面無(wú)表情地牽著家養(yǎng)的邊牧犬,到商店買了一把斧子。蒂爾達(dá)回到家,獨(dú)自在沙發(fā)上喃喃自語(yǔ):“4年了,你一直都說(shuō)會(huì)回來(lái),直到3天前。”她失落的眼神里,滿是對(duì)愛人不辭而別的絕望和尚存的一絲不甘心。
換上鮮紅色毛衣的蒂爾達(dá),舉著香檳在夜里徘徊,就像一團(tuán)凝結(jié)的火。某一瞬間,她突然爆發(fā),砸碎酒杯,拿起斧子,歇斯底里地向鋪在床上的黑色西裝瘋狂砍去。那一刻,高舉的斧子與墻上古典油畫中的裸體形成了鮮明對(duì)比。等到蒂爾達(dá)終于冷靜下來(lái),她便吃完藥片蜷縮在床上,獨(dú)自承受眼前的情感困境。
綠色床單、紅色毛衣以及破碎的黑色西服,阿莫多瓦用極具視覺沖擊力的色彩向銀幕前的觀眾展示了女人破碎而扭曲的情感狀態(tài)。
清醒過(guò)后,蒂爾達(dá)補(bǔ)完妝,終于在焦灼中等到了來(lái)自情人的電話。一段長(zhǎng)達(dá)15分鐘的精彩獨(dú)角戲由此開場(chǎng),我們從頭到尾都聽不到電話那頭的聲音,卻能夠通過(guò)蒂爾達(dá)極富張力的表演狀態(tài),時(shí)刻感受到情感的起伏跌宕。
最開始,蒂爾達(dá)強(qiáng)忍著情緒假裝鎮(zhèn)定,試圖用輕松的語(yǔ)氣挽回愛人。她告訴他,自己一切都好,他的狗一直在等他回來(lái);她告訴他,可憐的小狗一直不明白為什么他會(huì)突然消失。然而,情人并不為所動(dòng),依然冷血地決定要離開。蒂爾達(dá)的情緒便逐漸失控,開始抱怨、質(zhì)問(wèn),進(jìn)而怒吼:“為什么就這樣離開一個(gè)愛了4年的女人?其實(shí)我過(guò)得很不好,狀態(tài)非常糟糕,藥品幾乎成了我唯一的朋友,但我還是化了妝等你回來(lái),因?yàn)槲蚁虢o你看到我最好的樣子。”她的聲音忽然低落。
蒂爾達(dá)·斯文頓將一個(gè)失戀女人的脆弱、敏感、搖搖欲墜的狀態(tài)演繹得淋漓盡致,而她自身氣質(zhì)里獨(dú)有的冷傲和鋒利,更是讓觀眾們隨著角色情緒的打開而屏住了呼吸。直到電話突然切斷,蒂爾達(dá)決絕地走向衣櫥,換上一件黑色皮衣。繼而,她拎起紅色水桶沖出門,就像一切早已準(zhǔn)備好的那樣,將汽油澆滿了陽(yáng)臺(tái)和倉(cāng)庫(kù)。昏暗的倉(cāng)庫(kù)里,熊熊火焰燃盡了她4年的回憶。她帶著狗平靜而篤定地走了出去,門外是一片非常刺眼的光明。
阿莫多瓦在影片中用了鮮明的色彩表現(xiàn)人物的狀態(tài),那些大面積高飽和度的服飾便象征著角色情緒的多次改變。藍(lán)色西服代表了暴風(fēng)雨前的平靜,紅色毛衣預(yù)示著情緒的第一次爆發(fā),黑紅色睡袍是內(nèi)心的矛盾與掙扎,而最后的黑色皮衣則是女人走向新生的鎧甲。
蒂爾達(dá)·斯文頓用抓人的表演帶我們經(jīng)歷了一場(chǎng)痛苦的自我救贖。阿莫多瓦說(shuō),這部影片就像是一節(jié)關(guān)于欲望的道德課,而那些愛情的迷失與掙扎,同樣也在這場(chǎng)獨(dú)白中無(wú)處不在。? ? ? ? ? ? ? ? ? ? ? ? ? ? ? (責(zé)編:馬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