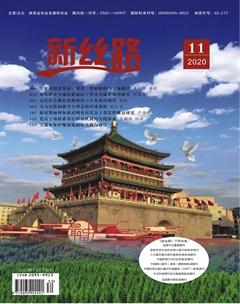儒學在當代中國及世界的現(xiàn)實與可能
呂文璐
摘 要:談起儒學,大多數(shù)人包括西方學者認為,儒家學說豐富的思想內(nèi)涵無不滲透并體現(xiàn)在中國人的生活中。盡管在歷史長河中,它經(jīng)歷過被邊緣化、受到過其他文化的沖擊以及政治家或思想家的批判,但并不能由此就忽視它經(jīng)過不斷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后給我們的現(xiàn)實社會帶來的指導意義。尤其在當今世界,儒學的再度興起使我們不得不再次將注意力投射到這一精神文明上。
關(guān)鍵詞:儒學;歷史發(fā)展;基本內(nèi)容;現(xiàn)實意義
在開篇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針對“儒家”、“儒學”、“儒教”做以區(qū)別和說明。其中,“儒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之一,其創(chuàng)始人是孔子,代表的是一種階層,通俗地說,是有著共同思想觀念的一個群體,如:道家、法家、墨家、陰陽家……本篇所要討論的對象——“儒學”則是儒家學派的主要思想觀點凝練而成的一種學說體系。而“儒教”則是從西方所謂的“宗教”角度來理解儒家思想。許多人習慣性地認為,儒、道、佛是中國的三大宗教。儒學作為一種精神文明,不僅關(guān)乎社會,也植根于人們的日常生活,是中國人的人生哲學。由此,上至先秦時期的初創(chuàng),經(jīng)過歷代的變革、創(chuàng)新、沖擊,乃至在當代的再度興起,它或多或少地始終出現(xiàn)在人們的觀照視野中。就目前學術(shù)界現(xiàn)有的文獻資料來看,對儒家學說或文化的研究大體集中在以下幾方面:儒學在市場經(jīng)濟環(huán)境中的體現(xiàn)及應用,如:景觀建筑的設計、旅游業(yè)、企業(yè)管理、學校內(nèi)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及德育教育等。分析文學或藝術(shù)作品中儒家思想元素及其內(nèi)涵如:《孔子》、《白鹿原》等。研究儒家思想在海外傳播的概況,如: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等國,以及分析在當代中國興起的原因及影響。
整體來看,對于儒學的關(guān)注,不論是討論其所起的現(xiàn)實意義還是對其內(nèi)涵的深層挖掘,研究成果已相當豐富。但專門針對該思想的發(fā)展線索進行系統(tǒng)的梳理,乃至結(jié)合其核心內(nèi)容分析對當代中國及世界的啟示意義,這方面的論文成果卻稍顯不足。因此,本文試圖從儒學產(chǎn)生的背景入手、結(jié)合自身理解對其基本內(nèi)容及社會功用做一闡釋,嘗試著預示該思想文化在當代中國及世界的啟示意義及可能。
一、歷史淵源及發(fā)展
《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游文于六經(jīng)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敘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為最高。”從劉歆對儒家來源的陳述中,我們可以得知,儒家學派以孔子為先師,他創(chuàng)私學、講“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強調(diào)仁義倫理。其實,早在孔子之前,“六經(jīng)”便已經(jīng)存在了,據(jù)文獻考證,“六經(jīng)”正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結(jié)晶(“六經(jīng)”又稱“六藝”)。[2]當初它們只是作為教育皇族子弟的教材,但隨著周王朝統(tǒng)治的沒落,這些典籍經(jīng)書便在像孔子這樣的人手中被闡釋和傳授,這些人以教授經(jīng)書為生,并對這些經(jīng)典著述注入自己的見解認識,如:孔子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論語·陽貨》來解釋當時的禮制規(guī)定,即父母去世后,兒子要為父母守喪三年。又如,《十三經(jīng)注疏》便是歷代教授經(jīng)書的人形成的各自的注解或解釋成果。由此,這些人被稱為“儒”。也即一批熟諳六經(jīng)的專家被稱為“儒家”。
1.“諸子百家”時期
與此同時,由于政治局面混亂,針對“人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社會”這一問題,代表不同階層利益的諸子百家紛紛提出了各自的主張,當時活躍在思想界的“百家”被史學家司馬談主要分為六家: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其他幾派的批判,如:墨子在《非儒》篇里說:“累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shù)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眾。”除此之外,儒家堅持以“禮”和道德治理國家,而法家則主張靠獎懲來統(tǒng)治一切人,“儒家一向指責法家卑鄙、粗野,而法家則總是指責儒家書生氣、不切實際。”[1]109等等,我們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在最初產(chǎn)生的環(huán)境中便經(jīng)歷著質(zhì)疑和斗爭。
2.秦漢時期
孔子、孟子、荀子不斷豐富儒家思想并對其注入新的內(nèi)容。漢武帝時期,中央集權(quán)國家的建立亟需統(tǒng)一的政治思想,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便從制度上保證了儒家思想的統(tǒng)治地位。為了維持社會秩序,董仲舒從儒家的五種倫常關(guān)系(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中選出君臣、父子、夫婦三項,稱為“三綱”,用“五常”來表述儒家崇奉的五種德行:仁、義、禮、智、信。在舊時的中國,“三綱五常”便成了個人品德、社會倫理的規(guī)范。此時的儒家在發(fā)展過程中其實已經(jīng)吸收了不少其他各家的思想,又由于政府的支持,相比其他學派,在政治上占據(jù)了更為有利的地位。
3.六朝、隋唐時期
而在六朝先后,及至中央集權(quán)擴大化了的隋、唐時期,儒家經(jīng)典成為開科取士的主要標準,儒家思想一時成為得到國家政權(quán)認可的官學,并通行于全國。公元628年,唐太宗下令在太廟中修建孔廟。但此時的儒家思想并不如孔孟、董時期那般充滿活力,在不同程度地受到玄學和佛學的挑戰(zhàn)下,人們對形而上學的問題,即人的本性和命運產(chǎn)生了更大的興趣,如:向秀和郭象在《莊子注》中倡導“棄彼任我”的生活方式,即不再依循別人的意旨生活,而是可以率性自由地過自己的生活。佛教的傳入,使國人開始相信“因果報應”、“前世今生”,“一切眾生,莫不是佛,亦皆涅槃。”也即人一旦覺悟之后,便可以從生死輪回之苦中解脫出來。《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以及《易經(jīng)》中所談到的對這類問題的觀點也被更新。韓愈的“道統(tǒng)說”便是證明,他們研究“道”、即關(guān)于“真理”的學問,而并非“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原道》。
4.宋、明時期
繼而在北宋到公元11世紀下半葉,被更新了的儒學分為兩個不同的派別,一派是以程頤、朱熹為代表人物,史稱“程朱學派”或“程朱理學”。他們從《易傳》出發(fā)所講的“道”是宇宙萬物內(nèi)涵的原理,由此而發(fā)展出“理”,萬物各自有“理”,“總?cè)f物之理,便是太極。”(《朱子語類》卷九十四)而“氣”又是按“理”而凝聚的,“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氣,則理便在其中。”(《朱子語類》卷一)由此可見,“理”、“氣”構(gòu)成萬物,從而有“天地之性”、“氣質(zhì)之性”。另一派是由程頤的哥哥程顥創(chuàng)立,陸象山、王守仁來完成,被稱為“陸王學派”或“陸王心學”。在他們看來,“宇宙是一個完整的精神實體”[1]201,我們的世界是心的、經(jīng)驗的。因此,我們需要“致知”、“格物”,而“致知在格物”。《大學》
上自唐代的韓愈直到宋、明時代,這種被更新了的儒學實際上是“儒學、佛學和道家思想、道教思想的融合”[1]208但它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同時的知識界的批評和抵制:“朱子道,陸子禪”,認為更新后的儒學其實其實曲解了孔子的原意。我們認為一種哲學思想如果能順應時勢,果斷吸收或融合其他思想,以滿足不同時代人們的需求,這種思想便是具有持久生命力的,而不是一種消亡,也不一定非被看作是思想史上的“災難”。
至于現(xiàn)、當代時期儒家思想的流變和發(fā)展,考慮到文本內(nèi)容的安排,我們將放在第三部分來闡述。
鑒于儒學知性、修身的人生哲學,仁愛、和諧的社會倫理,天人合一的人文主義內(nèi)容,這種具備人、地、天三者的統(tǒng)一,自我完善的精神體系不論在舊時中國還是現(xiàn)當代世界,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意義。
二、對現(xiàn)、當代社會的啟示意義及發(fā)展可能
儒家傳統(tǒng)這多元而豐富的精神內(nèi)涵,不論是對人生的啟示,還是對宇宙、社會的認識,放在現(xiàn)、當代世界都有其一定的現(xiàn)實意義和價值。因為它“總在不斷地回應‘時義(時宜)《周易·彖傳》,并因此而歷久彌新。”[3]回顧整個發(fā)展過程,孟子對墨子的批評做出首次回應,面對“吾愛吾身,勝于愛吾親。”《墨子》孟子則“善推其所為”《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宋、明時期對佛學、道學做出了很好的回應,并吸納而發(fā)展出遵從事理、本心的“理學”、“心學”。
盡管在五四時期,新興的文化啟蒙和西方船堅利炮的軍事、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的沖擊,使得思想界出現(xiàn)了“全盤反傳統(tǒng)”、“全盤西化”的偏激傾向。在“中國向何處去”的歷史問題上,他們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儒學傳統(tǒng)。然而,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能愈加積極地反省自身的傳統(tǒng)文化,反省我們的社會究竟需要什么樣的價值理念,什么樣的精神思想是我們需要揚棄的。即使進入到21世紀,儒家文化是否能在這個日益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中生存、甚至獲得新的發(fā)展的契機?我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
1.身心合一
儒家傳統(tǒng)注重心身修養(yǎng)。強調(diào)“適當其時”又“恰如其分”地行事和處理各種感情和欲望。如果一個人懂得對自己的感情和欲望進行適度地調(diào)節(jié),并使其得到合理的滿足,達到一種平衡,而不至于“過分”或“不及”,這對于保持精神的健康是必需的。另外,我們將對個人身心和外界所領(lǐng)會的付諸實踐,從而真正懂得其內(nèi)在的意義,我們才能夠稱得上做到了真正的完美。在完善個人的身心修養(yǎng)的同時,也需要關(guān)注他人的完善,這就到了社會的層面。
2.社會和諧
儒家提倡以“仁愛”、“忠恕”之心對待他人。通過修身,人心“像同心圓一樣一圈一圈地向外擴展,從自身出發(fā)到家庭,到可以直接對話的社群,再到國家,最后直到全人類”。[4]206
中國是以“家”這種社會結(jié)構(gòu)組織起來的一個個族群,孔子認為“仁愛”不應該只停留在愛自己的親人上,還要將愛推廣到他人、整個社會。這樣,“個人自掃門前雪”變成了“天下一家”的和諧局面。每個人應擔負起應循的社會義務,社會不就和諧起來了?同樣,把這種“仁義”施行到其他民族、其他國家,也將有利于和諧世界的建設。當前,世界政治和文化格局發(fā)生著復雜深刻的變化,各個國家的經(jīng)濟、政治、環(huán)境、安全等都面臨著不同程度的挑戰(zhàn),“和平與發(fā)展”成為各個國家和民族追求的基本目標。而在實現(xiàn)各個國家共同利益的同時,我們也應關(guān)注它們之間的矛盾和差異。根據(jù)孔子“和而不同”的理念,我們倡導在尊重各個國家主權(quán)和特點的基礎上,達到一種和諧的狀態(tài)。
3.天人共生
《地球憲章》中寫到:“地球,我們的家園,是生機勃勃的生命共同體。”儒家經(jīng)典《中庸》中有一段也描述著大自然的富饒與生命力。面對全球性的環(huán)境污染和生態(tài)平衡破壞問題。儒家傳統(tǒng)認為只有我們充分發(fā)展了“不忍之心”,不僅可以知天,還能夠與天合一。朱熹說:“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可見,“天人合一”觀告訴人們:要以“知天”“畏天”之心對待大自然的創(chuàng)造,同時要合理利用大自然的資源,并對其加以正確保護,這也是“對全球共同體發(fā)出的道德命令。”[4]201
三、結(jié)語
綜上所述,儒家傳統(tǒng)上自初創(chuàng)的先秦時期,直到當今世界,它帶著一種“會通”精神[5],并糅合著中國乃至世界的訴求,一步步地自我革新。其知性、修身的人生哲學,仁愛、和諧的社會倫理,天人合一的人文主義無不是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人情倫理的需求應時而變,即“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周易·系辭傳下》。我們不可否認這種溝通天、地、人三者統(tǒng)一的思想觀念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當代和諧中國以及“地球村”的構(gòu)建的。因而,我們認為,儒家傳統(tǒng)是可以走向世界的。
參考文獻:
[1]馮友蘭.馮友蘭文集(第六卷)[M].趙復三譯.長春:長春出版社,2008:4.109、201、208
[2]湯一介.儒學與經(jīng)典詮釋[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47(4):5-12
[3]黃玉順.儒學與中國之命運——記念五四運動90周年[J].學術(shù)界,2009.3(136):37-46
[4][美]杜維明.對話與創(chuàng)新[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206、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