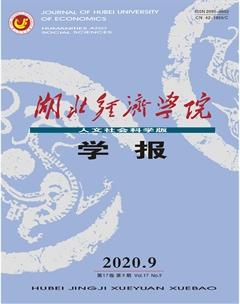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形成與發(fā)展
郭婷婷
摘要:董必武與李漢俊在思想轉變中,經歷了從儒家思想轉向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最后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歷程。在探索方式上,李漢俊側重理論,董必武從教育切入,他們都為中國共產黨的籌建做出了突出貢獻。作為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典型代表,他們的形成發(fā)展具有普遍性,是時代影響與個體實踐交互作用的結果。
關鍵詞:董必武;李漢俊;思想轉變;探索方式
從一大到十九大的九十多年,既是中國共產黨道路選擇的歷程,也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積極探索的歷程。考察中國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顯然對于實現(xiàn)“中國夢”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董必武與李漢俊是中國早期的先進知識分子,他們在探索中成為了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典型代表。本文將分析二人在馬克思主義探索中的異同,考察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形成與發(fā)展。
一、思想轉變:儒家思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馬克思主義
從思想轉變歷程看,董必武與李漢俊都經歷了從儒家思想到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再到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二者均出生于清朝末年,在其成長發(fā)展過程中正值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時期,其思想轉變符合新思想的傳播邏輯。同時,這也是他們積極汲取新思想,探尋救國救民道路的結果。
董必武與李漢俊都出生于傳統(tǒng)知識分子家庭,他們的父親均為秀才出身的塾師,另外,在他們最初成長中起到同樣重要影響的親人也是秀才出身。李漢俊的兄長李書城16歲便中了秀才,董必武的四叔是才名遠揚的廩膳生員(秀才中的最高名目),董必武5歲已入學塾讀書,18歲時中了秀才。因此,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必然在早期對二者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董必武從革命探索中走向馬克思主義
董必武早期追隨康梁,辛亥革命爆發(fā)后,在湖北組織同盟會支部。赴東京私立日本大學留學時,他與張國恩謁見了孫中山,得到孫中山的鼓勵,在加人中華革命黨后,積極參加孫中山在日本組織的革命活動。后來,董必武與張國恩受孫中山派遣返鄂策動李愈友起事反袁,兩次被捕后依然繼續(xù)從事革命活動。1917年,董必武再赴日本,期間開始接觸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書籍。1918年春,董必武在成都“得知俄國十月革命消息后,寫信給在日本的友人,探尋情況,索取資料。”后來,董必武應鄂西靖國軍總司令蔡濟民之邀擔任司令部秘書,“共謀反對北洋軍閥的護法斗爭。”口l不久蔡濟民遭到另一將領方化南的殺害,董必武等來到上海向孫中山申述蔡案,然而此時已孑然無助的孫中山先生除了表示同情和惋惜外,無能為力。
在追隨孫中山的革命過程中,董必武逐漸認識到“孫的路子不對頭,總是靠軍閥。革命發(fā)展了,孫中山把握不住,結果叫別人搞去了。”迷惘與困惑中的董必武開始探尋新的救國道路,可是“當時社會上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日本的合作運動等等,各種主義在頭腦里打仗。”年五四運動時,董必武從鄂西到上海。此時,李漢俊從日本畢業(yè)回來,住在董必武對面,在經常的談論中,董必武“從李漢俊那里知道許多俄國的消息”,開始“看《資本論入門》和考茨基的書。”此后,董必武“就想法了解俄國革命的情況和馬克思主義的書”,并且“開始研究俄國的方式”。
(二)李漢俊從理論探索中走向馬克思主義
1904年,12歲的李漢俊在兄長李書城之友吳祿貞的資助下東渡扶桑,李書城當時在日本已經“拜訪了孫中山,結交了黃興,開始投身革命,他和友人組織湖北同鄉(xiāng)會,創(chuàng)辦了《湖北學生界》(后易名《漢聲》),宣傳反清、愛國的民族思想。”正處于少年時期的李漢俊與李書城同住一處,在耳濡目染中受到了民族資產階級思想的熏陶。在與另外兩位好友的交往中,李漢俊也受到了民主思想的沖擊,一位是深受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影響并且后來成為孫中山追隨者的戴季陶,另一位是與中國同盟會接觸頻繁的沈玄廬。
李漢俊在日本留學的后期正值日本社會激烈動蕩的大正時期,隨著社會主義風起云涌,社會主義在日本得到了迅速傳播。當時,李漢俊結識了堺利彥、高滓正道和宮崎滔天等日本社會主義者以及其他的進步人士,尤其與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交往甚密,結下了師生之誼。最終,李漢俊放棄了摯愛的數(shù)學,轉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并成為了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探索者。
從革命探索中走向馬克思主義的董必武與從理論探索中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李漢俊代表了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兩種典型形成路徑,他們在時代背景的影響下,又顯示出思想轉變歷程的同質性,即“儒家思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演變邏輯。
二、殊途同歸:理論宣傳與教育救國
經過曲折的探尋,最終找到馬克思主義這一救國之路后,董必武與李漢俊等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都清醒地認識到“新思想是經濟變革底反照,而這經濟的變革又是社會全體進步底表現(xiàn)的緣故。所以新思想是人類進步的重要要素,又是物質的生產力底變化所依以傳到社會組織唯一媒介”。因此,當務之急是“把主張、思想告訴人家”,通過“能喚醒群眾、接近群眾的方法”傳播馬克思主義。
1919年8月,董必武與張國恩等在“商談中得出一個結論,他們一致認為目前能夠作的是辦報紙和辦學校兩件事。”舊“董、張于秋末回武漢著手籌備報社”,擬定報名為《江漢日報》,后因籌款困難,這一計劃最終擱淺。“報未辦成,他們提議辦學校的事卻有人共鳴”。他們先后聯(lián)絡了幾位響應者,學校的開辦經費由創(chuàng)辦人共同募集,無奈之下的董必武甚至將身上的皮袍當了才湊夠了份額。在共同的努力下,他們逐步解決了經費、教員、立案等一系列問題。1920年3月,位于湖北省教育會舊址西北角幾問房子里的私立武漢中學正式開學。開學后,為了更好地在學生中傳播馬克思主義,董必武和陳潭秋編寫了《政治問答》,并組織了具有參與校務領導權利的學生會,指導學生會創(chuàng)辦了《武漢中學周刊》,鼓勵學生發(fā)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另一方面,在他們的倡議下,武漢中學開設了宣傳革命思想的社會主義課程,他們還通過各種途徑獲得先進書刊,作為向師生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的教材。此外,董必武先后邀請李漢俊、惲代英、劉子通、黃復生等先進知識分子到武漢中學講課。武漢中學不僅發(fā)展成為湖北教育改革的先驅,還逐步發(fā)展“成為武漢地區(qū)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進行革命活動的基地之一”。
為了進一步推動教育救國,促進群眾覺醒,董必武將教育對象擴展到工農,將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到了工農中間。董必武與張國恩、陳潭秋等創(chuàng)辦了新教育社,發(fā)起組織了湖北職業(yè)教育研究社和湖北平民教育促進會,并出版了具有新教育思想的刊物《新教育》。董必武一方面積極在《新教育》上發(fā)表具有影響力的文章,一方面利用那些組織推進平民教育,他積極發(fā)動武漢中學及其他學校具有先進思想的師生,創(chuàng)辦了勞工學校、武昌女子學校補習學校、識字班、平民學校,同時還號召學生利用寒暑假返鄉(xiāng)的機會,在家鄉(xiāng)創(chuàng)辦農民夜校或平民學校。這些教育活動深受工人與農民的歡迎,在提高無產階級知識水平的同時,促進了無產階級的思想解放,也為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
五四運動后,《新青年》、《星期評論》、《民國日報》、《覺悟》副刊、《建設》,以及后來的《勞動界》和《共產黨》月刊等先后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陣地,李漢俊或者是刊物的主編,或者是主要撰稿人,與這些先進報刊雜志都有著密切的關系。
李立三后來曾指出,在五四時期反抗帝國主義、反抗封建勢力的刊物中間,“最占勢力的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評論社”。《星期評論》創(chuàng)刊時還是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隨著李漢俊逐漸成為其“思想領導中心”,該刊物最終成為了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陣地,其銷量從最初的1000多份一度上升到十幾萬份。《星期評論》團結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在其周圍,并且推動了很多人的思想演變,像惲代英、俞秀松、施存統(tǒng)、楊之華等革命者在其文章、回憶錄、書信中都忠實地記錄著。1946年夏,周恩來在接受美國記者李勃曼的采訪(見《嘹望》周刊,1984年第2期)時也曾談到,《星期評論》、《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等進步刊物對他的思想都有深刻影響。此外,該社曾接待過諸多日本社會主義者以及朝鮮早期共產主義者,發(fā)展成為了國內與國外馬克思主義者溝通的重要渠道。
《星期評論》從創(chuàng)刊到被迫停刊的短短一年時間內,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就有50多篇,而李漢俊發(fā)表的關于新思想的文章就有將近40篇。他在《新青年》、《共產黨》等先進刊物上發(fā)表的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文章或譯文也有60多篇。李漢俊通曉日、英、法、德四國語言,翻譯了《馬格斯資本論入門》、《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主要內容、第一國際宣言、第二國際布魯塞爾大會決議、第三國際籌備宣言、蕭伯納贊美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與勞動黨》的演講等大量重要馬克思主義著作,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關鍵人物。
三、籌建組織:群英結黨救中華
董必武與李漢俊在實踐與理論的探索中,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增進了對工人階級的了解,馬克思主義通過先進知識分子同工人運動相結合,為共產主義組織的建立作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成立共產主義組織也成為救國救民道路的必然選擇。
1919年5月,李漢俊翻譯了日本著名社會主義研究者山川菊榮的《世界思潮之方向》,他在后記中寫到“我們中國怎么樣?——中國決不在世界外,也不能在世界外。”還談到,“人家叫我做民黨叫革命黨,我應該在這一點有切實的打算”。可見,李漢俊在那時已經有了籌建無產階級政黨的想法。
1920年2月,陳獨秀來到上海,在多次與李漢俊等人的交談中,“越談越覺得有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必要”。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一行來到上海,與李漢俊、陳獨秀等馬克思主義者進行了多次商談,“一些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更加明白了蘇俄和蘇共的情況,得到了一致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在這時候,‘中國共產黨發(fā)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5月,李漢俊作為主要發(fā)起人,參與發(fā)起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舉行了中國積極分子會議。這次會議為未來的中國共產黨奠定了基礎”,李漢俊在會議上表示堅決贊成建立中國共產黨。1920年8月,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成立。上海早期黨組織逐漸發(fā)展成為推動全國建立共產主義組織的中心,當時,李漢俊“在黨內地位僅次于陳獨秀”,主要負責湖北早期黨組織的籌建。同年8月,董必武接到李漢俊的來信,“信中告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情況,并約董必武和張國恩在武漢成立共產主義組織。”董必武復信表示贊同,并應約建黨。“后來,李漢俊又親自來到武漢,找董必武談,要建立共產主義小組。”董必武隨即秘密聯(lián)絡陳潭秋商談建黨的問題。這時,劉伯垂受到陳獨秀的委派來到武漢協(xié)助董必武籌建黨的組織。董必武、張國恩、陳潭秋同劉伯垂就建黨問題取得一致意見后,又發(fā)展了包惠僧、趙子健、鄭凱卿。1920年8月,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在武昌撫院街董必武、張國恩寓所正式宣告成立。
為了團結教育進步青年,李漢俊參與發(fā)起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8月,“第一個青年團建于上海,其原則是準備社會革命。不久,董必武與陳潭秋率先在武漢中學建立起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作為黨組織的預備學校。1920年9月,李漢俊又參與創(chuàng)辦了黨第一所培養(yǎng)干部的學校——外國語學社并擔任法語教員。與此同時,李漢俊為了協(xié)助武漢共產主義小組開展工作,介紹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助手馬邁耶夫夫婦兩次來到武漢,他們住在董必武、張國恩寓所,與董必武、張國恩、陳潭秋等進行廣泛交談,了解武漢黨組織的籌建情況,并介紹俄國革命的情況和經驗。1920年11月,董必武“和張國恩、李書渠等研究,正式成立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團,確定‘團的主要任務就是實現(xiàn)社會主義”一。在成立會議上,董必武發(fā)表了長篇講話,激勵青年“不要把我們看得分文不值”,“要投身到正在醞釀之中的新的運動中去”。1920年冬,董必武“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一方面作為共產主義研究小組的公開活動陣地,另一方面吸收先進的知識分子研究馬克思主義,為發(fā)展黨的成員準備后備軍。”
1920年12月,“陳獨秀應孫中山之邀,去廣東擔任教育廳長,由李漢俊代理書記,并主編《新青年》”。不久,為了推動工人運動的發(fā)展、培訓和選派人員赴俄留學,李漢俊所主持的上海早期黨組織便成立了職工運動委員會和教育委員會。1921年1月,董必武與李書渠等創(chuàng)立《武漢星期評論》,李漢俊是主要作者之一,董必武也發(fā)表了多篇短評。《武漢星期評論》逐漸發(fā)展成為武漢馬克思主義思想陣地之一。1921年初,在維經斯基返俄后,上海早期黨組織與共產國際失去聯(lián)系,隨即因經費短缺而陷入困境。李漢俊經常熬夜撰稿以賣稿籌款,甚至為了籌集經費當?shù)敉銎奘罪棥?921年3月,李漢俊所主持的黨組織在困境中仍推動了上海法商電車工人大罷工,他一方面派黨員團員前去主持工作,一方面撰文支持并稱贊工人的“齊心的團結力”。
1921年6月3日,國際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抵滬,與李漢俊和李達取得聯(lián)系,經過深入考察與了解,馬林認為中國已經具備了建立共產黨的條件,提出盡快召開中共“一大”的建議。李漢俊與李達商議后又致信陳獨秀與李大釗,最終確定了關于召開中共一大的各項事務。隨后,李漢俊與李達便發(fā)函通知各共產主義小組分別派兩名代表抵滬參加黨的成立大會。1921年7月,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李漢俊的寓所召開。董必武與陳潭秋作為武漢代表,李漢俊與李達作為上海代表參加。會上,董必武與李漢俊受大會委托,共同向共產國際起草了一個“中國情形的報告”報告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把這種狀況的調查研究結果建立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所闡發(fā)的理論基礎上,極力主張進行社會革命的必要性。后一部分列舉了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的罪惡”。會議中途遭到巡捕搜查,李漢俊為了掩護同志們,冒著生命危險留下周旋,董必武與其他代表則乘船前往嘉興,繼續(xù)開會。
董必武在“一大”結束后返鄂,與陳潭秋一起進一步發(fā)展黨的組織,并一直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與探索。中國共產黨正式誕生后,由于與中央意見產生分歧,李漢俊于1924年脫離黨組織,但他依然堅信馬克思主義,“以社會主義者自居”,致力于工農和民族解放,“他常對人說:我不能做一個共產黨員,能做一個共產主義者,亦屬心安理得”。
綜上所述,以董必武與李漢俊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早期探索者在思想轉變過程中體現(xiàn)出同質性,在實踐探索中也體現(xiàn)出目標的一致性與方式的多樣性,這是歷史條件影響與個人實踐交互作用的結果,他們都為馬克思主義的早期探索做出了突出貢獻,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發(fā)展,推進了馬克思主義指導我國革命的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