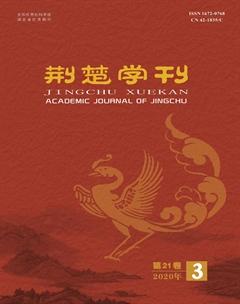高校教師性騷擾的行為類型與法律屬性
楊軍 保琰
摘要:近年來,頻繁曝光的高校教師性騷擾在我國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然而,高校教師性騷擾的類型結構和法律屬性并沒有得到基本的討論。因此,有必要以類型思維為基礎,從當事主體、主體間關系、行為構成等方面厘定高校教師性騷擾的一般類型要素。進而,以受侵害權益和權益受侵害程度為類型區分標準,討論高校教師性騷擾行為的法律屬性。從受侵害權益出發,高校教師性騷擾主要包括侵犯公民個人法益和公共法益兩種類型,前者包括對人格權和受教育權的侵犯,后者包括對教育管理秩序和社會秩序的侵犯;從權益受侵害程度出發,高校教師性騷擾則可能構成民事侵權、行政過錯和刑事犯罪三種類型。
關鍵詞:高校教師性騷擾;類型結構;行為類型;法律屬性
中圖分類號:D92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2-0768(2020)03-0070-07
一、 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高校教師性騷擾事件頻繁曝光,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2018年1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女學生羅某實名舉報教授、博導、長江學者陳某性騷擾羅某等多名女學生;同年4月,時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沈某被舉報曾對學生高某進行性騷擾并導致高某自殺。兩起事件曝光后在社交媒體長期保持較高熱度,《人民日報》就“校園性侵案”發表了專門評論[1]。其后,2019年12月,“上財副教授性騷擾女大學生”事件再次掀起社會波瀾。與此同時,伴隨Metoo運動(1)不斷擴展蔓延,性騷擾作為世界性的普遍問題受到越來越多關注。
然而,無論是發生在高校還是其他場域的性騷擾從來都不是近年的新問題。1974年,凱瑟琳·A·麥金教授便提出了“性騷擾”這一概念,指出“性騷擾是不平等的一方強加給另一方的令人不愉快的性要求,包括性暗示和戲謔等”[2];2005年,《婦女權益保障法》的修正也對性騷擾問題進行了規定:“違反本法規定,對婦女實施性騷擾或者家庭暴力,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受害人可以提請公安機關對違法行為人依法給予行政處罰,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2014年,教育部出臺《關于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明確規定高等學校的教師不得“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系”;2019年11月,教育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師德師風建設的意見》,要求針對高校教師性騷擾學生等開展集中治理;2020年5月,《民法典》頒布,第一千零一十條規定:“違背他人意愿,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騷擾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機關、企業、學校等單位應當采取合理的預防、受理投訴、調查處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職權、從屬關系等實施性騷擾。”
盡管相關規制不少,但性騷擾尤其是高校教師性騷擾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明顯的緩解。處理過程很少有法律授權機關的參與,處理結果更是缺少對行為屬性的法律判斷。在此背后,還存在著更多的高校教師性騷擾長期被忽略、被合理化、被容忍而免于實質性懲處[3]。
高校教師性騷擾與師生關系結構不對等現實問題有關,因此,有學者研究了高等教育中的性別權力關系,認為知識權力和性別權力交互疊加是引發高校教師性騷擾的重要原因[4]。但是,規范視野下,該問題的頻發實則與以道德評價為主而法律判斷缺位的問題有更大的關系。于當事主體而言,法律屬性判斷缺位一方面會導致被害人無法尋求權利救濟,另一方面會導致一旦存在“冤假錯案”雙方當事人無法獲得法律框架內的有效解決。于教育法治而言,該種缺位意味著高校教師性騷擾法律防治機制將難以實踐適用,防范效果可能更遭削弱,教育法治的目標付之闕如。反之,明確的法律屬性判斷將使得相應處理有法可依,防范機制的建構有跡可循。本文將通過高校教師性騷擾的類型建構,進一步厘清其范疇和類型特征,從而以此為基礎討論高校教師性騷擾的法律屬性。
二、高校教師性騷擾的一般類型要素
合理審慎地界定高校教師性騷擾類型是梳理現有制度缺陷、構建防治體系的前提。明確禁止“性騷擾”是2005年修改《婦女權益保障法》最受認可的成就之一,但本次修改及后續的法律法規中并未說明“性騷擾”概念的確切含義。界限劃分模糊也成為相關侵害難以得到救濟的重要原因。相較于一般的“性騷擾”,校園環境較為封閉,學生往往在旁人難以察覺的情況遭遇性騷擾,舉證難度更大[5]。所涉權益與情境的不同使高校教師性騷擾更具其獨特性,在本文看來,高校教師性騷擾包含以下幾方面類型要素:
其一是當事主體。總體而言,高校內的主體包括:(1)管理主體,即黨政管理人員等高校管理者,如校長院長、書記副書記等;(2)教育主體,即高校教職工等承擔教育任務的人員,如一般教師、導師等;(3)科研主體,主要是指專職研究員等高校內專門從事科研工作的人員;(4)學習主體,主要是指學生等高校內的學習人員;(5)服務主體,主要是指后勤等承擔校內服務工作的人員。此外,具體情境下同一人可能同時體現出不同的行為主體身份,不同行為主體的特征也可能共存于同一行為人身上,如教師同時擔任黨政管理職務,學生同時具備管理職責等。從目前曝光的高校性騷擾來看,由于獨占的權力優勢,管理、教育及科研主體是主要的施害主體,居于弱勢地位的學習主體是主要的受害主體。高校教師的性騷擾在高校性騷擾中占比最大。因此,本文將主要關注高校教師性騷擾的問題。而所謂高校教師性騷擾,主要是指實施方即行為主體為高校教師,被騷擾方即受害主體為高校學生的性騷擾行為。
其二是主體間關系。行為主體與受害主體之間存在某種特定的權力關系,這是高校教師性騷擾與其他類型性騷擾之間的主要區別。有學者將此稱為“校園關系”,即“施害人基于擔任學校職務、承擔任務等而與受害人所產生的關聯,并且優勢方能夠通過這類關系給弱勢方施加影響” [5]。基于中國式傳統師徒關系的現代延伸、行為主體在學術層面的知識權威等多種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受害者感知的該類影響可以做適當的擴大理解。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該權力關系還可能是“隱性、軟性的,展示出魅力面向的,而針對此權力的服膺是柔性的、往往是有高度認同性、信仰性的” [6]。可以認為,高校教師性騷擾體現出一種行為主體與受害主體之間強弱不對等的關系,這種關系產生的效果是:(1)行為主體擁有時間和空間上較強的支配能力,從而具備高頻率策略性地運用個人權力對受害主體實施騷擾行為的可能,并能在正常交流與性騷擾之間切換自如;(2)受害主體的防范處于被動局面,難以在時間和空間上徹底擺脫風險;(3)受害主體很可能因代價嚴重而不敢或不能反抗,加之對于導師信任背叛和信念崩潰而產生緊張感[3],從而長期處于痛苦、壓抑的心理狀態。
其三是行為構成。判斷高校教師性騷擾是否成立應該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進行考察。在主觀方面,行為主體應當具備“故意”要件。一方面,行為主體應當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具備性意味;另一方面,行為主體應當有意通過一些行為實現其與性相關的目的,如追求性刺激或宣泄性欲望。在客觀方面,行為主體需要實施了包含性因素或性意味的行為,如向對方發出帶有性含義的挑逗、侮辱、威脅等冒犯性言論,或對受害主體強行進行身體接觸、強吻或擁抱等[7]。同時,該行為應對受害主體產生了侵犯結果。這主要包括兩種可能:(1)騷擾行為“不受歡迎”,使受害主體的權益受到侵害,在此性騷擾語境下的“不受歡迎”并不要求受害人明確表示拒絕,只要違背其真實意愿即可[8];(2)受害主體所處群體的權益或相關秩序受到侵害。毫無疑問,第(1)種情況肯定構成性騷擾。略有爭議的是第(2)種情況。對此,本文認為,對性騷擾危害的評價不應當局限于直接的受害主體,受害主體所處群體權益或相關秩序的受損,也應當歸責于行為主體的性騷擾行為。有美國學者便曾提出,教職員工對學生的性騷擾會對學生的平等受教育權造成極大的傷害,可能會“妨礙和損害學生充分享有教育的福祉、氛圍和機會” [9]。因此,在行為構成的客觀方面,上述兩種可能只要有一項實現便應當認定侵害的成立。
基于上述三個類型要素的分析,本文認為,高校教師性騷擾主要是指高校中具有教師身份的行為主體基于不對等的權力關系對受害主體實施的包含性因素和性意味的傷害行為。在這一行為構成下,以行為人的主客觀方面為標準,一些其他基于權力不對等而對學生做出的不當行為,如某些導師利用權力對學生進行學術壓榨等,便不在此概念范疇之內。
三、部分特殊情形的合類型性分析
法律屬性的判斷本質上是一種合類型性判斷[10]。要判斷某一特定行為類型的法律屬性,首先要判斷該行為類型是否符合相應的法律類型。前文討論了高校教師性騷擾的一般行為類型,但仍有相當一部分行為在是否符合前述類型的問題上存在爭議,主要包括師生戀、高校性交易兩種特殊情形。由此引發的類型性爭議在很多場合也構成了行為主體抗辯性騷擾成立的主要理由。例如,有行為主體指出自己與受害主體乃情侶關系,其行為不構成性騷擾。因此,在辨析高校教師性騷擾的法律屬性前有必要先討論這兩種特殊情形的合類型性。
在一般高校教師性騷擾情形下,受害主體完全被動,不具有引發、利用、接受性騷擾的意愿;而在師生戀與高校性交易中,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預見性騷擾,甚至具有自愿、主動的主觀意圖,這正是其區別于一般高校教師性騷擾的特點。本文認為,導致這種區別的是當事主體間的“情意關系”,此“情意關系”根據引起主體的不同可劃分為行為主體引起型與受害主體引起型。對于前者,就受害主體對該 “情意”的反應可進而區分為接受和拒絕兩種情形。在拒絕情形下,毫無疑問行為主體做出的包含性因素或性意味的行為將構成性騷擾。若其持接受態度,那么其中具備性意味的行為作為成年人之間你情我愿的私人行為,不會構成對一方的傷害,前文所述高校教師性騷擾行為構成要件的成立將會受到質疑。受害主體引起型則更易引起爭議,如果受害主體主動向行為主體發起僅包含性因素的行為邀請,性騷擾自然不會成立。還需要注意的是,此處受害主體對“情意關系”的接受和主動發起應當是基于真實意思表示而做出的。如果是迫于行為主體的權力權威而做出的表面合意,那么行為主體的行為毫無疑問依然是性騷擾。
有必要追問的是,是不是在所有你情我愿的主體間關系下性騷擾都不會成立呢?在本文看來并非如此。既有的研究中,已有學者在分析師生戀時從“自由論”及成年人之間的“情欲自主”出發,提出“傳統觀念中以為正確的倫理關系,實際上是不平等、不正確、充滿壓迫的,只是此種不平等權利關系被倫理的外衣所美化” [11]。我國部分臺灣地區學者進而提出“解放師生戀”,認為只要“當事人自愿,沒有欺騙、毀謗、脅迫、剝削等情況,師生間性行為就應該受到尊重”[11]。但在本文看來,該主張只是浪漫主義情懷的過度泛濫,忽略了前述校園權力關系導致的雙方主體間無可避免的不平等性,更可能成為性騷擾的華麗包裝和開脫借口。例如廈門大學吳某就曾以此辯解其性騷擾:“大家都是成年人,你情我愿各取所需”。另一方面,對于對兩性問題尚缺乏足夠認知的大學生群體而言,在遭遇性騷擾時,可能出現錯誤認識而將其理解為“男女之間的浪漫關系”,甚至有可能以自我歸罪的方式對導師的騷擾行為進行合理化的解釋,乃至逼迫自己愛上導師。這種表面上的“師生戀”實則為性騷擾行為造成的非正常后果。最后,從行為構成來看,即便是你情我愿未對當事主體造成權益侵害的師生戀,也可能因侵害到當事主體所處群體的他人利益或特定秩序而構成性騷擾的危害后果。一旦行為主體與當事主體成為戀人,當事主體之外的其他主體將落入一種權利不對等的境地。由此,“一些國家在教育領域的反性騷擾實踐,都力圖避免具有直接指導關系或教學關系的師生間的浪漫關系,以免產生交換型性騷擾或第三方敵意環境性騷擾的可能性” [12]。因而,除非雙方之間不會存在任何權利義務交叉,行為主體的權力不會帶給受害主體任何的優勢權利(本文將此稱為純愛型師生戀),否則師生戀便帶有性騷擾的嫌疑。
在對第三方權益和特定秩序的侵害可能性上,師生戀問題與高校性交易具有相同之處。相對于以直接傷害或剝奪學生某種權益而獲得性利益而言,利用雙方在社會經驗尤其是性經驗方面的差距,對性騷擾對象進行洗腦或灌輸權色交易觀念并額外提供校園權益進而獲得性利益的現象更多,后者就是所謂高校性交易。相關案例中,騷擾者都會在騷擾前后提出發表論文、資助參加會議、推薦交流和深造等好處,并通過自己的“權力策略”操縱受害主體的“同意”。而這些“好處”往往是行為主體基于學術研究、高等教育和行政管理的公職可以支配的公共資源。因此,高校性交易實則是對公共資源不可交易性的侵犯,校園管理秩序和教育秩序將因此遭受明顯破壞,此類行為與刑法意義上的行賄受賄并不存在本質區別。與此同時,高校性交易將受害主體所處群體中的其他人置于顯著的不平等地位,難以進行公平的競爭,其利益也將受到減損。概言之,高校性交易的情形中,行為主體的騷擾行為將因同樣會構成侵害后果而構成較廣義上的高校教師性騷擾。
前述判斷在性剝削理論的框架中也可以得到印證。在性剝削理論框架中,“性剝削的本質是一種不平等的關系,是剝削者對性對象的工具化利用”,其中包含了兩項核心要素——“利用”及“剝削者獲益”;受剝削者“不受益”并不能作為成立剝削的必備要件,即使受剝削者也獲利,但只要與剝削者獲利不成比例,也成立剝削[13]。當前學界對性剝削理論主要應用于兒童性侵害問題的分析上,并將雙方能力上的不平等總結為相關性行為之所以會具有剝削性的最關鍵因素。事實上,高校教師性騷擾亦存在明顯性剝削關系。盡管高校學生已經具備一定社會經驗的積累,但在教師面前仍存在顯著實力落差。無論是基于學術資源等進行的自愿性交易,還是基于社會經驗、性經驗方面的差距而產生的一般類型師生戀,其實質都是利用青年學生的特性和弱勢所進行的具有剝削性的性活動。
事實上,目前所謂師生戀、性交易與高校教師性騷擾常常相互交織難以區分,許多表面上看來是受害人“自愿的”性交易和情意關系,實則是受害人處于懼怕、擔憂等心理而難以抗拒,行為主體所做行為在本質上是“不受歡迎的”。而這種“不受歡迎”的主觀特征卻常在社會公共輿論對女性道德的貶低之下被“交易”這一表面公平的帷幕所遮蔽[12]。因此,本文認為,除了純愛型師生戀,一般的師生戀和高校性交易都符合高校教師性騷擾的行為類型。
四、高校教師性騷擾的法律屬性
高校教師性騷擾行為沖擊了一般國民的道德情感,目前的話語體系也期望將各類騷擾行為全部納入法律規制之中,實施嚴格的法律管理。但在如何確定行為屬性進而建立法律規制的問題上,目前的實踐和理論分析均認識不足,民事侵權、行政過錯、刑事犯罪的界限不清楚,對高校教師性騷擾進行法律屬性的判斷無從談起。
本文認為,為解決這一問題,根本上要對高校教師性騷擾的法律屬性進行類型判斷。該判斷應當建立在對“受侵害權益的法律屬性”及“權益受侵害的程度”兩個維度的同時評判之上,受侵害權益越重要,權益受侵害的程度越高,則性騷擾行為越嚴重,反之亦然。從我國當前的法律體系來看,一般來說,民事侵權、行政過錯、刑事犯罪依次代表了違法性從低到高、從不嚴重到嚴重的順序(2),構成了高校教師性騷擾法律屬性的三種類型。從高校教師性騷擾侵害的權益類別來看,主要包括人格權、受教育權等個人法益,以及管理秩序、教育秩序等公共法益。下文將主要從高校教師性騷擾侵犯的權益類型出發,對行為的法律屬性進行討論。
(一)侵害個人法益的高校教師性騷擾
一般來說,高校教師性騷擾侵害的個人法益主要包括當事人的人格權和平等受教育權[14]。
1. 侵害人格權的高校教師性騷擾
“人格權是指民事主體專屬享有,以人格利益為客體,為維護民事主體獨立人格所必備的固有權利” [15]。作為最基本的民事權利,人格權具有基礎性,其內容具有法定性。我國1986年《民法通則》第一次在立法上對人格權進行了法定化,列舉了生命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等具體人格權類型;而后《民法總則》第109條規定了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第110條對民事主體的具體人格權進行了概括列舉;《民法典》“第四編人格權”在“第二章 生命權、身體權和健康權”中特別就性騷擾進行了規制。從高校教師性騷擾的行為構成來看,該類行為侵害的主要是受害主體的人格尊嚴和性自主權。
首先,人格尊嚴是“民事主體作為‘人應有的最起碼的社會地位, 和應受到的社會與他人最起碼的尊重” [16]。根據國際上對性騷擾的理論研究成果,性騷擾防范機制本質上是一種性別管治機制。從主體間關系來看,高校教師性騷擾是有權主體對無權主體的權利傾軋,這種傾軋毫無疑問帶有對受害主體人格尊嚴的蔑視以及侮辱,顯然構成了對其人格尊嚴的侵犯。
其次,性騷擾侵害了受害人的性自主權。具體而言,性自主權是“人在遵循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自主表達性意愿和自主決定是否實施性行為和以何種方式實施性行為,滿足性欲望而不受他人強迫和干涉的權利” [17]。在性騷擾實施過程中,騷擾者一方面獲得了一般意義上的性欲望的滿足,同時還通過權力傾軋獲得了某種權益增加感,二者均來自于對受害主體性自主權的侵犯。值得明確,此處所說性自主權“不僅包括性交的內容, 還包括保持自身性器官完整性和安全性的身體上的利益, 和自主的性行為帶來的精神愉悅與滿足等精神上的利益” [16]。在這個意義上,此處的性自主權還應當包括受害主體的性羞恥心,行為主體進行的性因素相關的猥褻、侮辱等對受害主體性羞恥心的侵犯同樣會構成性自主權的侵犯。
從規范內容來看,當前《民法典》“人格權”編中將性騷擾規制直接規定在身體權內容中。有學者認為此處規定存在不妥,具體而言,性騷擾行為除接觸之外,也確實存在大量不需要接觸身體的情形,同時其“目的是非法侵害對方性利益,結果是使受害人的性權利受到損害,而不是僅僅使受害人的身體被非法接觸” [18]。對此,本文傾向贊同當前《民法典》的規制安排。一方面,將性騷擾視為對身體權的侵犯,以身體權保護相關性自主利益,符合比較法中身體權從傳統消極防御到積極利用權能的新型人格權趨勢;另一方面,當前的規制設置方式,也并未排除對于性騷擾所涉人格利益的其他人格權保護方式,當性騷擾侵害精神利益時,仍可適用《民法典》關于一般人格權的規定[19]。
最后,值得說明的是,盡管當前學界尚有爭論,但本文認為,作為性騷擾行為所侵犯法益的人格權不應包含名譽權。所謂名譽權,是“自然人對其名譽享有的不受他人侵害的權利,是一個人得到社會合理評價,人格得到社會其他成員尊重的權利” [19]。根據現行規范,侵害名譽權的方式如侮辱、誹謗等一般具有公開性的特征,而性騷擾的突出特點即行為的隱蔽性,兩者顯然存在沖突。若認為性騷擾侵害了名譽權,則意味著受害者失去了性方面的名譽,那么受害者若是站出來維權,“在法庭上承認自己在性的方面失去名譽恐怕是對人格尊嚴更大的傷害” [12]。若受害主體名譽權的損失來自于行為主體在一般意義上的侮辱,則只會構成其他的侵權行為,而非性騷擾。盡管性騷擾本身一般并不會直接侵害當事人名譽權,但出于對社會聲譽評價和所謂的“不光彩行為”曝光的擔心,絕大部分的受侵害者并不會選擇將騷擾行為告訴執法或司法部門。這一內在心理因素一方面阻礙了救濟渠道的開啟,另一方面也促使性騷擾行為主體實施更加猖獗的騷擾作為。對此,美國以校園裁判為受侵害者提供了一個更為有效的選擇。“校園裁判”即在校園中成立正式的反性騷擾機構,并制定相應防治政策,進而為受害者提供咨詢幫助并就其投訴開展調查。具體而言,校園裁判的內容主要包括:設置專業化專職崗位人員、制定較為激進的校內性侵認定及防治立法、設置準司法程序規則、制定人性化的懲罰和警戒措施以及建立犯罪統計與常態化預防宣傳制度等[20]。
從法益侵害的嚴重程度來看,根據民法典侵權責任編,一旦行為主體構成性騷擾,其行為將構成民事侵權,受害主體可以依據民法典向行為主體請求侵權責任。同時,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42條,性騷擾對個人法益的侵害還可能構成行政過錯。而一旦性騷擾的危害程度過于嚴重,行為人將構成刑事犯罪。例如如果強行與被害人發生性關系,那么行為人將構成強奸罪等罪名(3);如果侵犯了被害人的性羞恥心,行為人將構成強制猥褻、侮辱罪。
在區分性騷擾嚴重程度的問題上,當前存在主觀說、客觀說和以性別差異為基礎的客觀說。其中,主觀說主張完全依據被騷擾者的感受作為判斷標準,客觀說認為應當從一個誠實善意人的角度去判斷是否足以構成性騷擾,而以性別差異為基礎的客觀說則給客觀的誠實善意人賦予了原告的性別特征[8]。本文認為后兩種判斷標準的可采性顯然優于主觀說。一方面,在“性騷擾”現象中,有相當一部分涉及平常相處與人際互動過程中可能會引起“不舒服”感受的行為,對這些行為,應相信并鼓勵人們運用生活智慧應對,而不是納入法律機制硬性禁止的范圍[21];另一方面,在高校教育領域,若采取過于嚴格的界定標準,則很可能導致導師對于招收異性學生以及與異性學生的相處過分警惕,乃至盡可能減少接觸指導,該局面的產生很可能加劇教育中的性別不平等。同時,以性別差異為基礎的客觀說則比一般客觀說更加合理,這種學說使“誠實善意人”擁有了相對具體判斷的標準,使性騷擾嚴重程度的判斷更加可行。
2. 侵害平等受教育權的高校教師性騷擾
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具體而言,“受教育權是公民依法享有的要求國家積極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條件和機會,通過學習來發展其個性、才智和身心能力,以獲得平等的生存和發展機會的權利” [22]。由于“校園權力關系”的存在,高校教師性騷擾還可能侵害被騷擾者及其所處群體他人的平等受教育權。
就被騷擾者而言,平等受教育權的侵害體現在兩個層次上。首先,盡管教授或導師不一定是學校行政權力的絕對擁有者,但對學生而言他們卻擁有指導、評價、推薦甚至錄取學生的重要權力。這種無冕之權將學生置于被動境地[4],也使得行為主體具有性騷擾的實施可能,從而沖破雙方之間正常的教育與被教育關系,侵犯受害主體的平等受教育權。其次,一旦騷擾行為得逞,受害主體將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后續可能不得不通過性利益的交換來獲得其應有的平等受教育權;若未得逞,受害主體很可能將面臨來自行為主體的報復和進一步侵害,平等受教育權同樣得不到保障。最后,眾多受害人由此承受極大的精神壓力,排斥異性、懷疑自我科研能力,甚至精神抑郁,乃至發生割腕自殺等極端行為。如此境地下,正常的學習生活尚難以繼續,更何談平等受教育權的有效保障。對被騷擾者所處群體其他人而言,如前文分析行為構成所說,盡管并非騷擾行為的直接相對人,其平等受教育權同樣會被侵犯。這尤其體現在師生戀和校園性交易的行為類型中,此類型下,行為主體擁有的具有獨占性的教育權、管理權很可能有所傾斜或存在傾斜風險,從而相對剝奪直接相對人所處群體的平等受教育權應有的“平等”屬性。
就法益侵害嚴重程度而言,目前我國憲法和法律對于作為基本權利的平等權與受教育權的保護主要是原則性與宣誓性的,尚未在規制和實踐層面明確自然人是否可能侵害他人的基本權利,也未明確如何對其他自然人承擔相應責任,由此引發的侵害識別及權利救濟實則處于較為尷尬的狀態。
(二)侵害公共法益的高校教師性騷擾
在個人法益之外,高校教師性騷擾還可能侵害公共法益。具體而言,這種行為會構成對高校管理秩序、教育秩序的侵害,極端情況下也可能侵害社會公共秩序。
從當前的規范內容來看,從教育部相關意見到各部門法律,性騷擾都被視為需要禁止的行為類型。在秩序建構的視野下,這意味著正常的教育教學管理秩序和社會秩序在本質上作為一種受到法律保護的公共法益,是不允許高校教師性騷擾行為的存在對此造成破壞的。具體來說,行為主體與受害主體之間本應存在有純潔的管理與被管理、教育與被教育、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而性騷擾的存在將嚴重影響此種純潔關系,導致師生之間無法再按照正常的教學秩序開展教學工作,這無疑是對于法律保障之下公共法益的極大破壞。
最后,從公共法益的侵害程度而言,當前我國民法對此并不予以規范,行為人可能構成行政過錯或刑事犯罪。于前者而言,一旦行為人侵害了正常的教學秩序,行政機關便可以依據行政法規對其進行處罰;于后者而言,一旦行為人對教學秩序、正常社會秩序的破壞已經達到了刑事犯罪的程度,那么便可以對其以尋釁滋事罪、聚眾淫亂罪等罪名進行刑事處罰。
注釋:
(1)Metoo(我也是),是女星艾麗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等人2017年10月針對美國金牌制作人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星丑聞發起的運動,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犯女性挺身而出說出慘痛經歷,并在社交媒體貼文附上標簽,藉此喚起社會關注。
(2)需要聲明的是,這只能代表一般情況。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中,民事侵權所產生的危害后果、構成的刑事違法性并不低于行政過錯或刑事犯罪。
(3)按照當前我國刑法規定,強奸罪只保護女性的性自主權。如果被害人是男性,那么只能以強制猥褻罪進行處罰。
參考文獻:
[1]?校園性侵案:讓每一個青春都能走進春天[EB/OL].(2018-04-05)[2019-03-22].http://k.sina.com.cn/article_2286908003_884f726302000ador.html.
[2]?袁翠清.我國校園性騷擾法律規制探究——以美國相關法律為對比[J].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18,37(6):109-115.
[3]?李佳源,方蘇寧.高校性騷擾:特征、現狀、成因與應對機制——以女研究生為重點的實證分析[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5(8):91-97.
[4]?雙曉愛.當代中國高等教育中的性別權力關系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黨校,2017.
[5]?任海濤,孫冠豪.“校園性騷擾”的概念界定及其立法意義[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8,36(4):150-157,168.
[6]?汪江連.高校“性騷擾”:權力、道德與法律的多元考察[EB/OL].(2018-02-09)[2019-03-23].https://www.wxwenku.com/d/105361653#tuit.
[7]?劉司墨.校園性騷擾的法律規制問題研究[J].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7(4):43-51.
[8]?張新寶,高燕竹.性騷擾法律規制的主要問題[J].法學家,2006(4):65-76.
[9]?李軍.學術性騷擾的共犯性結構:學術權力、組織氛圍與性別歧視——基于國內案例的分析[J].婦女研究論叢,2014(6):44-55.
[10]?張文,杜宇.刑法視域中“類型化”方法的初步考察[J].中外法學,2002(4):421-432 .
[11]?王俊.從道德審判走向法治化:對大學校園學術性騷擾的審思[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5):158-165.
[12]?宋少鵬. 何為性騷擾?:觀念分歧與范式之爭——2014年教師節前后“性學派”對“女權派”的質疑[J].婦女研究論叢,2014(6):56-65.
[13]?杜治晗.兩小無猜非兒戲——一條司法解釋的法教義學解釋[J].清華法學,2020,14(4):53-71.
[14]?李振勇.校園性侵行為的法益分析與預防[J].青少年犯罪問題,2018(3):14-20.
[15]?楊立新.人格權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39.
[16]?薛寧蘭.性騷擾侵害客體的民法分析[J].婦女研究論叢,2006(S1):5-9.
[17]?郭衛華.性自主權研究——兼論對性侵犯之受害人的法律保護[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73.
[18]?楊立新.我國民法典人格權立法的創新發展[J].法商研究,2020(4):18-31.
[19]?張紅.民法典之生命權、身體權與健康權立法論[J].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2020,35(2):70-86.
[20]?胡裕嶺.美國高校性侵防治校園裁判立法的經驗與啟示[J].青少年犯罪問題,2020(1):104-113.
[21]?黃盈盈.“MeToo高校反性騷擾事件”的社會學分析與對策建議[EB/OL].(2018-08-02)[2019-03-29].http://www.sohu.com/a/244238444_232950.
[22]?王勝利,王潔.淺析高校懲戒權與大學生受教育權的沖突與平衡[J].天津法學,2010,26(1):105-108.
[責任編輯:盧紅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