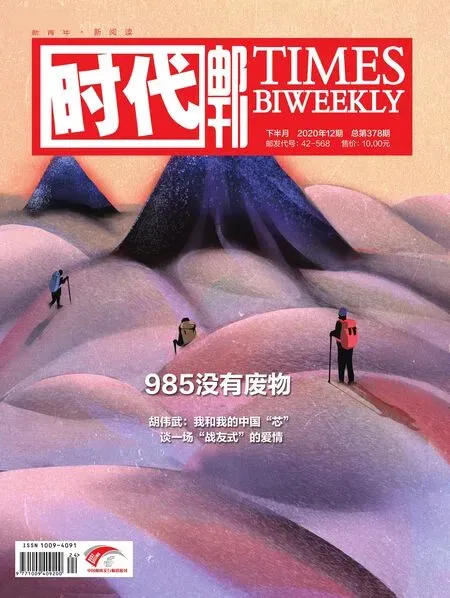月圓之夜,聽我為你唱首歌
那一年,我們都19歲,我是公司的開票員,師諾是銀行的收費員。若說我和他有什么相似之處,那就是,我倆都有些“不懂事”“沒眼色”,都會有意無意地減弱自己在人群中的存在感。
不過和師諾一起工作很開心,比如他會指著辦事大廳里跑得最歡的老丁說:“你看,像不像只大螞蟻……”他不說倒也罷了,他一說,你再看老丁,真的神似一只忙忙碌碌的大黑螞蟻。他還指著主管說:“像不像螳螂?”可不是嗎?你無論什么時候把目光投向主管,他都在指手畫腳,除了指手畫腳,還真想不出他還會別的什么動作。師諾把大廳里的一切瞬間都變成一部默片,讓你忍俊不禁。他把耳機給我戴上一只,示意我,配上音樂更有滋味。
后來,我經常在人群中辨別像師諾這樣的人,他們的一部分知覺仿佛永遠停留在少年的某個階段,有能力發現美和真正有趣的瞬間,當這些有趣被發掘并呈現出來時,平庸和煩瑣的生活瞬間被照亮了。
一起工作了兩周,我知道了師諾的經歷:北漂在地鐵和酒吧里唱了兩年歌,幾乎一天三頓煎餅果子,如今他在銀行工作的目的是攢些錢繼續北漂。父母在縣城,很開明,并不反對他的生活方式,只是有些擔心他的日子太窘迫,托在這個城市的姨媽關照他,姨夫給他找了現在的工作。可只要他敢去他們家,他們就會恨鐵不成鋼地數落他,說他浪費了他們給找的平臺,不會走動、不愛應酬。還有賣唱,簡直丟人現眼!
有一回房東突然漲租金,他措手不及去找姨媽借錢,姨媽罵他沒出息,把錢扔在了地上。我問:“那你撿了沒?”
“撿了。”他眼神黯淡得像蒙了一層霧,他沒說為什么。對于太過復雜的情緒,就像對待令人難堪的現實和生活,他不是看不懂,是干脆轉開臉裝作看不見。
再說,不撿又能怎么樣,不撿錢就有尊嚴了嗎?與音樂相比,在現實里丟失的面子又算得了什么呢?誰能理解音樂帶給他的巨大快樂?說到唱歌,師諾眼睛變得特別亮。他決定給我唱首歌,待到某個月圓之夜。
如今,我們一起看月亮的那棟樓早就不見了。在現實生活面前,那些疑似愛情的、讓心靈感動的細節都太輕盈了,輕得一口氣就吹散了。
多年過去的一個晚上,我加完班在樓下的便利店買咖啡,電視機里忽然傳出一首歌,正是師諾在有月亮的陽臺上給我唱過的那首歌。“愛呀,不必表達,也不必說話……”
震驚之余,我跑出門,抬頭,一輪圓月掛在天上。透過越來越厚的眼淚,月亮,不是一輪,是好幾輪,那一團團光芒,涌出來,滾落在地上。類似的信號就像外星人發來的密碼一樣,以后再也沒有收到過了。
如今,游走在這個早已面目全非的城市,我經常會莫名好奇,師諾變成什么樣了呢?對他來說,用音樂換來了面包,是實現了夢想,還是遠離了夢想?
在我尋思的當兒,十字路口堵成一團的車們正焦躁地狼奔豕突,但愿,開車的某個神情麻木的中年人,不是師諾。